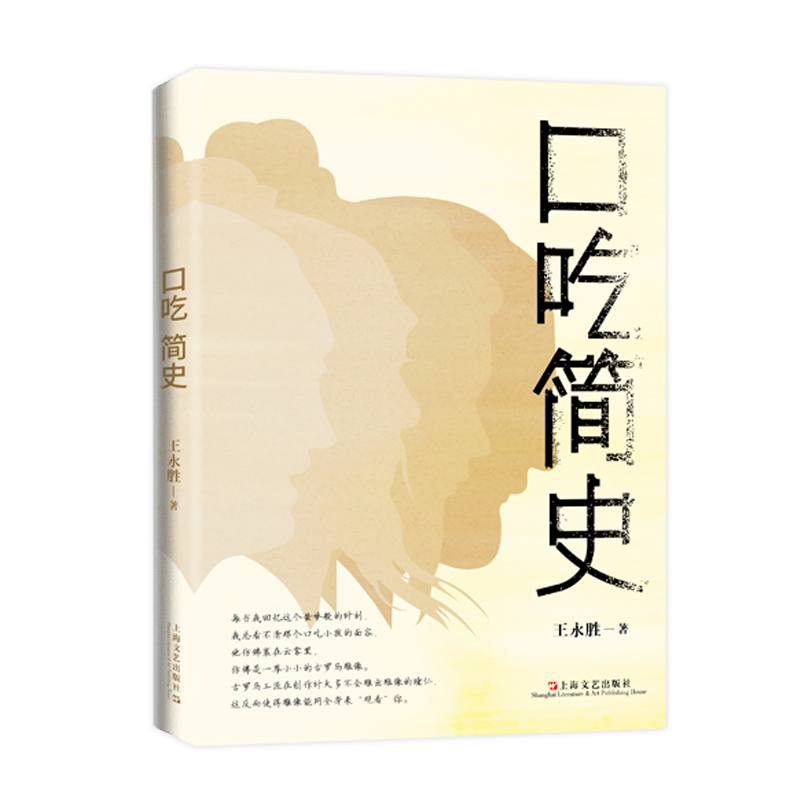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2.30
折扣购买: 口吃简史
ISBN: 9787532183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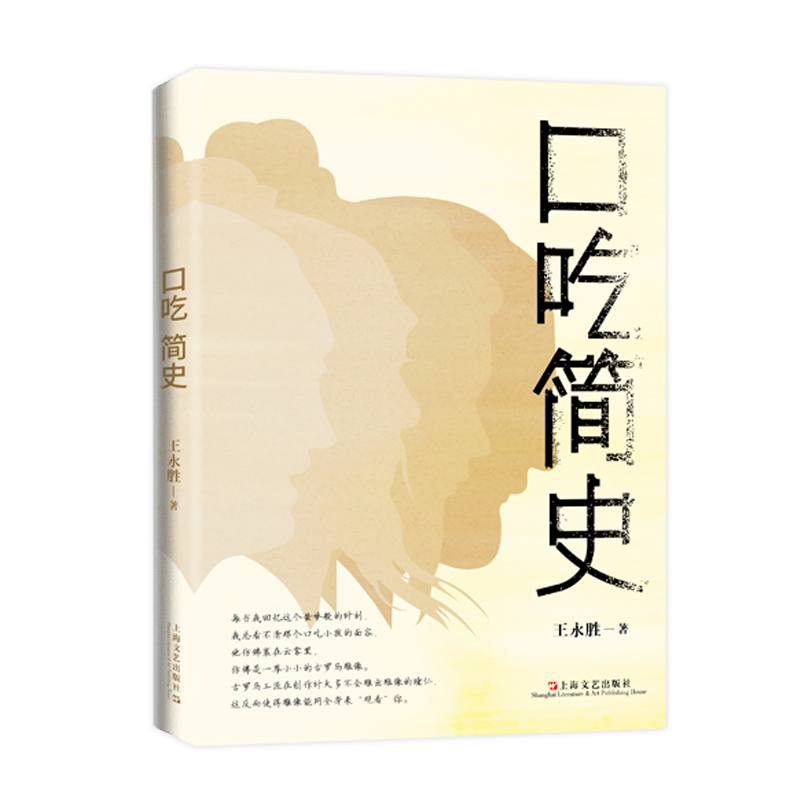
王永胜,浙江温州人,1982年出生,早年口吃,业余习武,文章散见于《读库》《书城》《随笔》《青年文学》,已出版作品《屠龙简史:武林漫游三千年》《云朵背后的云朵》等。
朱见深:帝王的口吃现象(节选) 一 朱见深,年号成化,庙号宪宗,明朝第八位皇帝。在位期间四海升平,虽有几次民变却无损大局,基本无大事可述,气候有点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朱见深实在是一个平平淡淡、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皇帝。 但是,看似平常的表象,细究起来底下又藏着许多非常有趣的东西。 朱见深曾两度为太子,最终还能君临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此独特的经历,都是拜吊诡的命运所赐。 1449年8月,朱见深的父亲,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兵溃土木堡被俘。皇太后孙氏命朱祁镇异母弟朱祁钰监国,立3岁的朱见深为太子。一个月之后,朱祁钰即皇帝位,就是代宗,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1450年,太上皇朱祁镇还京师,居南宫,所谓“居”,其实就是被代宗朱祁钰软禁。皇帝被俘虏之后,还能安全返回,这在中国历史上又是很少见。 1452年,朱祁钰废6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皇太子朱见济死了。 1456年12月,代宗朱祁钰病重。群臣议论复立朱见深为太子。 1457年正月,大臣石亨、徐有贞等认为“皇帝在宫,奚事他求”,复立太子不如拥英宗复位,且功劳无量,是谓“夺门之变”。政变也就是夜间几个时辰之间的事,一转眼,龙椅上换人。英宗时隔7年,两度为皇帝,这在历史上又是绝无仅有的。三月,英宗复立11岁的朱见深为太子。 朱见深18岁时,英宗崩,这一次他才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失去了父亲。英宗崩时,也只有38岁,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年轻的父亲。 朱见深就像顽童手中的玻璃弹珠,首先被放在火上烤,烤完放在冷水里“呲”,之后继续放在火上烤……如此几番折腾。 二 立太子,遵守嫡长子制,所谓“立长不立贤”。“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时,无嫡子,留下三个婴儿皇子,均是庶出。长子朱见深虚岁3岁,真正算起来仅一岁零十个月。在兵荒马乱之中,皇太后孙氏立朱见深为太子。 朱见深在最需要父爱的童年,却“失去”了父亲。他身为太子,龙椅上却坐着叔父。在懵懵懂懂的年龄,他该如何理解如此诡异的事。 有人统计过,权力巨大、荣耀无比的中国皇帝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况最差;非正常死亡比例高;人格异常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如果统计一下太子的命运,也会是同样让人唏嘘。童年的朱见深无疑会慢慢地感受到从四周蔓延而来的,无形的焦灼与压力。 举一个相似的例子。清朝末年,慈禧也是从奕身边夺走他4岁的儿子载湉,即光绪帝。张宏杰在《坐天下》一书中用悲悯的笔调如此形容光绪:“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群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类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简单平凡的亲情。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 上面这段话同样适合朱见深。朱见深也是在相似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在同样的紫禁城,在同样的年纪,也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也用恐惧的眼神偷偷看着自己的亲戚。 三 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为,无助、脆弱的儿童会觉出世界存在潜在威胁的所有负面影响力,因为害怕这种潜在的危险,同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便会形成某种神经质的倾向来对抗着世界。 身在帝王家的儿童同样受到这种负面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他们受到比普通儿童更大的压力。盘点中国历史,口吃的帝王并不少见,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司马氏阴冷的眼神带给他的压力;北齐第二任皇帝高殷,被他父亲文宣帝高洋抽打成口吃;北齐后主高纬,他在军中口吃发作时,就本能地用大笑救场。 如果我们把范围稍稍扩大,发现口吃的王族也不少见:韩非前文已经提及;鲁恭王刘余,汉景帝之子,就是为扩建宫室,破孔子之宅,得古文经,开后世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那位;明朝王族八大山人朱耷,他有一闲章曰“口如扁担”,是难言之意。这些人同样受“负面影响”而变成口吃。 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之下,童年的朱见深和光绪都变成了口吃。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认为,光绪的口吃是“先天不足”;我认为光绪的口吃可能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冷漠而威严的慈禧活活吓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相似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朱见深和光绪虽然都患有口吃,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读帝师翁同龢日记,我们会发现印象里清秀、文弱的光绪,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性格非常矛盾。而朱见深的性格相对来说很宽和。 何以故?这是因为,口吃的孩子只能以建立某种防御策略的方式来应对、抗衡这个世界,并且得到满足感的获取。至于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由所处的整个环境的综合因素来决定的,是追求控制呢,还是倾向屈从?是乖顺呢,还是高筑壁垒把自己围困起来,并杜绝外人闯入?所有能采用的方法都取决于现实条件。 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困境,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信息交互方式。好比悲伤的人不一定都流泪。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悲伤的各种举动,触摸其受挫的情感、欲望与恐惧的深处。 四 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朱见深在临朝宣旨时,犹如背课文,因为事先诵读熟了,所以能“琅琅如贯珠”,至于召见大臣、商议朝政,临时应对,那就麻烦了。所谓“君相天赋,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测” 1464年,也就是朱见深即位后的第一年,大臣在奏疏中提出应开经筵,要求皇帝风雨寒暑不废,日御文华殿,午前讲学,午后论治,且礼仪繁琐。对朱见深来说,真是一场折磨。1467年,大学士刘定之请经筵照例赐宴,“毋烦玉音”,但是最终“君臣之间无一词相接”。 与朱见深同时代,在朝廷为官的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次上朝,诸司奏事,“事当准行者,上以是字答之”。也就是说,朱见深把不得不回答的词句尽量压缩到字数最少。成化十六七年间,“上病舌涩”,连说个“是”都很困难,鸿胪寺卿施纯马上揣摩到了朱见深的难处,就悄悄向近侍说:“是”这个字难说,可以改成“照例”两字。 在我这个口吃者看来,朱见深“是”字的发音也未必是流畅的。大部分的口吃者有几个特别难发的音,而“是”字本身包含的用来表态与承诺的意义,往往会给口吃者带来心理压力,“是”就成为口吃者特别难发音的一个字。可是,把一个特别难发音的字组成两个字的词组,有时是会变得容易发音一些,施纯确实“深谙此道”。由此可见,“上病舌涩”,只是朱见深口吃严重的托词,而陆容当真了。如果朱见深真的烂了舌头,不能发“是”字,又安能发“照例”两个字? 朱见深改为“照例”,觉得确实特别好用,“甚喜”,就问是谁出的主意,近侍就说出了施纯的名字,于是施纯得升礼部侍郎,掌寺事,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施纯凭借两字之功,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升到如此高位,朝野惊讶,当时就有人嘲讽他:“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五 在长久的焦虑与压力之下,朱见深除了口吃,还患有一种类似心理障碍的疾病:坐久了或见生人心里便发慌,很不自在。 据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皇后王氏去见朱见深时,被太监挡在了门外,理由是:“上不耐生人,勿数至。”对于太监给出的这个理由,皇后王氏“亦无愠色” 众所周知,朱见深是一个情种,对万贵妃情真意切,对其他女人包括皇后王氏在内都是冷冷淡淡的。皇后王氏也只是谨小慎微地在宫中生活着。 万贵妃比朱见深要年长17岁,对于朱见深如此宠幸,他的生母周太后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据《罪惟录》记载,周太后气呼呼地质问朱见深:“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说:“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朱见深的心理障碍,需要万贵妃陪伴,细心地按摩,才得缓解。 朱见深的暗疾,也“曲折”地见于正史。《明史?宦官一》记载,东厂太监尚铭与当红太监汪直有隙,尚铭怕后者报复,“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语奏之” 。尚铭把访查得来的汪直平时言谈之中泄露的“禁中秘语”都告诉了朱见深。所谓的禁中秘语,无非就是朱见深与后妃的床笫之事,也许还包括万贵妃的抚摩。尚铭之举很有效,因为汪直已经碰到了朱见深最隐秘的痛点,朱见深开始对汪直感到愤怒。汪直这颗当红的彗星开始急速下坠。 万氏小名贞儿,4岁时被选入宫中,成为宣宗孙皇后身边的宫女。“土木堡之变”后,孙皇后将3岁的朱见深立为太子,把朱见深放在身边抚养,而服侍朱见深饮食起居的,正是万贞儿。 在每一个孤独绝望的黑夜,朱见深从成熟的万贞儿身上得到了亲人之爱与情人之爱,最后,这几种温暖又像咖啡、奶、糖一样融合在了一起。 史载万贵妃“机警,善迎帝意”,朱见深每次出游,她都“戎服前驱”。《万历野获编》说万贵妃“丰艳有肌,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应该是民间传言多起来了。《罪惟录》记载“万贵妃貌雄声巨,类男子”,更接近真实。对朱见深来说,雄强的万贵妃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 ※ 面对口吃困境,i人如何逆袭与突围 作者因儿时的一次恶作剧,口吃如影随形,痛苦和焦虑吞噬着自信。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困境。而在漫长挣扎中,通过读书和写作,直面困境,让自己完成蜕变。也因这孤独的自我求索,作者对患有口吃的历史人物,如德摩斯梯尼、韩非、扬雄、毛姆、朱见深等,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与共情。 ※ 以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解读历史文化人物,获得沟通古今的全新视角 口吃作为疾病,它对于患者的心理、生活、创作均会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作者即从此角度入手,借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或参考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去体会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口吃人物,从而获得沟通古今的全新视角。其中既有细节,也有理论;既有故事,也有考证。 ※ 与心中的“兽”坦然和解:九个“书写即救赎”的故事 与“社恐”相似,口吃有时是内心自卑感的外显。每个人或多或少面临过口吃的处境。书中九位口吃人物都是创作者。通过创作,口吃所带来的疏离感、冷眼旁观的姿态、内省的性格,反而让他们找到观察、书写这个世界的独特角度,以及安身立命的方式。正如扬雄创作《太玄》,“他心中已经生成另一番包罗万象的天地万物,他再被自己创造的天地万物所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