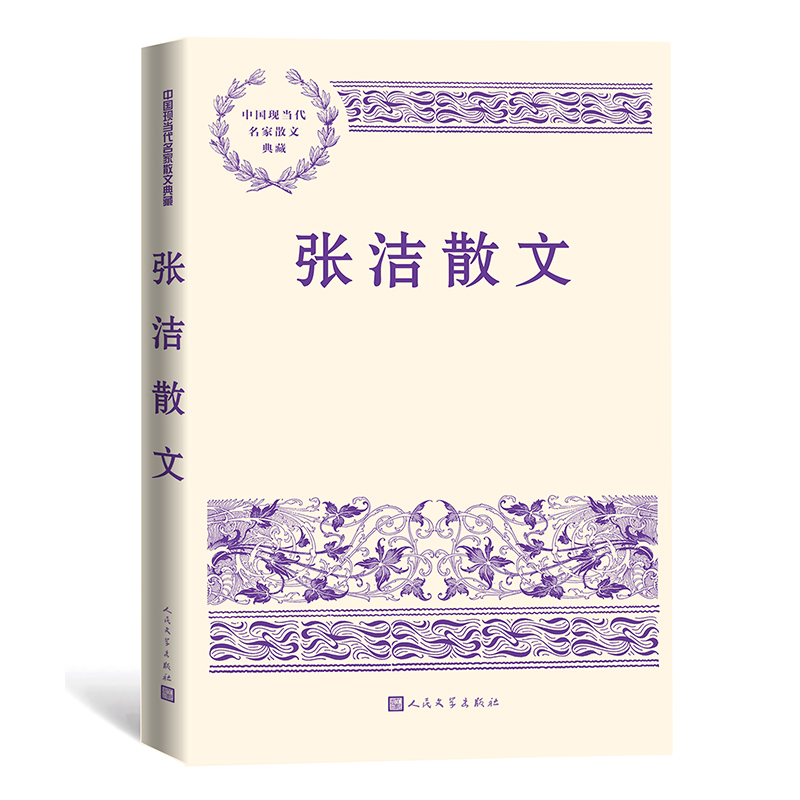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9.70
折扣购买: 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张洁散文
ISBN: 9787020186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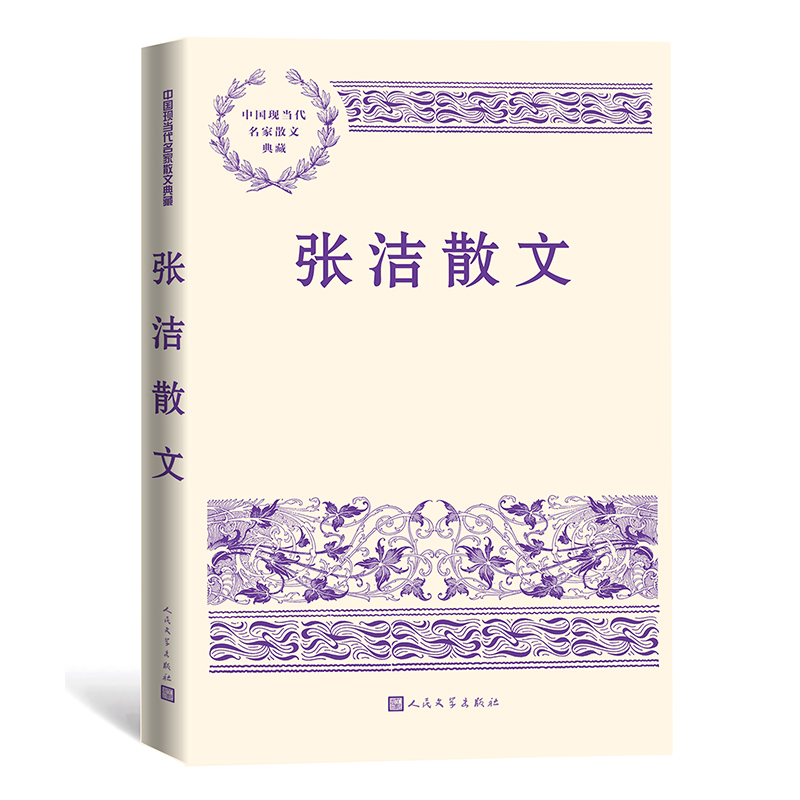
张洁(1937.4.―2022.1.),中国当代作家。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以及多种国际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出版。 张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最具开创性、代表性,最有个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她的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捡麦穗》《挖荠菜》等一举成名,风靡全国。长篇小说处女作《沉重的翅膀》更是轰动文坛,引发争议,最终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张洁也因此享誉世界,被各国文学界和大众关注。长篇小说《无字》再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张洁潜心写作,处世低调。 2022年1月,张洁在纽约去世。
捡 麦 穗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 谁不熟悉捡麦穗这回事呢?或许可以这样说, 捡麦穗的时节, 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时节。 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 挎着一个空篮子, 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捡麦穗的时候, 她想的是什么呢? 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 月亮, 像是偷偷睡过一觉, 重又悄悄回到天边。 方才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 走回自家破窑的时候, 她想的又是什么? 唉, 她还能想什么。 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 你永远不能想象, 从这一颗颗丢在地里的麦穗上, 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捡哪, 捡哪, 一个麦收时节, 能捡上一斗? 她把这捡来的麦子换成钱, 又一分一分地攒起来, 等到赶集的时候, 扯上花布、 买上花线, 然后她剪呀、 缝呀、 绣呀……也不见她穿, 也不见她戴, 谁也没和谁合计过, 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 偷偷地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 不过, 真到了该把那些东西从包裹里掏出来的时候, 她们会不会感到, 曾经的幻想变了味? 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 是她们在捡麦穗、 扯花布、 绣花鞋时幻想的那个男人吗……多少年来, 她们捡呀、缝呀、 绣呀, 是不是有点傻? 但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 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 再也找不到做它、 缝它时的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 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 谁也不会关心她们曾经的幻想。顶多不过像是丢失一个美丽的梦, 有谁见过哪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当我刚能歪歪咧咧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 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捡麦穗了。 对我来说, 那篮子太大, 老是磕碰我的腿和地面, 闹得我老是跌跤。 我也很少捡满一篮子, 因为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 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 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 篮子里的麦穗, 便重新掉进地里。 有一天, 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 “看看, 我家大雁也会捡麦穗了。” 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 “大雁, 告诉二姨, 你捡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 “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 还向我们周围的姑娘、 婆姨们, 挤了挤她那双不大的眼睛: “你要嫁谁呀?” 是呀, 我要嫁谁呢? 我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 “我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 像一群鸭子嘎嘎地叫着。 笑啥嘛! 我生气了, 难道做我的男人, 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 我不知道。 他额上的皱纹, 一道挨着一道, 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 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 那些皱纹, 给他的脸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 他那长长的白发, 在他剃成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 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 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 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 见到我就乐了。说: “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 露出一嘴的黄牙。 后脑勺上的白发, 也随他的笑声一起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了磕: “娃呀, 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不等你长大, 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 我着急了。 他要是死了, 那可咋办? 我那淡淡的眉毛, 在满是金黄色绒毛的脑门儿上, 拧成了疙瘩。 我的脸, 也皱巴得像是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 塞进了我的手里。 看着那块灶糖, 我又咧开嘴笑了: “你莫死啊, 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 答应着我: “莫愁, 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啊哒?”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 走到啊哒, 就歇在啊哒。” 我犯愁了: “等我长大, 去啊哒寻你呀?” “你莫愁, 等你长大, 我来接你。” 这以后, 每逢经过我们村, 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 一个甜瓜、 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说: “来看看我的小媳妇呀!” 我呢, 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见过———让我娘给我找块碎布, 给我剪了个烟荷包, 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 我缝呀, 绣呀……烟荷包缝好了, 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 说那不是烟荷包, 皱皱巴巴, 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 我说了, 等我出嫁的时候, 我要送给我的男人。 我渐渐长大了, 到了认真捡麦穗的年龄。 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 都是让人害臊的话。 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 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 我知道, 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倒是越来越依恋他, 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 我都会送他好远。 我站在土坎坎上, 看着他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 我看得出来, 他的背更弯了, 步履也更加蹒跚。 这时, 我真有点担心了, 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 过腊八的前一天, 我估摸卖灶糖的老汉, 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 我站在村口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 朝沟底那条大路上望着, 等着。 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 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 让冬日的太阳一照, 更是红得透亮。 那个柿子, 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 真怪, 可它也没有被风刮下来、 雨打下来、 雪压下来。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的人, 走近一看, 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 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 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 望着树梢上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 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 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 可是我却哭了, 哭得很伤心。 哭那陌生的、 但却疼爱我的、 卖灶糖的老汉。 等我长大以后, 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 再没有谁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 没有任何企望的疼爱。 真的, 我常常想念他, 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皱皱巴巴、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 可是, 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1979 年 12 月 对于我, 他没有 “最后”(片段) 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 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合影, 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补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 附信上写道: 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 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 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件事, 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 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 他就去了。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 那些感觉太过尖锐。 我在等, 等它们变得迟钝——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 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如今见到这张照片我已不再哭泣, 知道终于可以记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 面对汹涌的思绪, 或无章可循、无可解释的人生, 文字又是那样的乏力……但对我生命中遇到过的这个人, 即便没有力量的文字, 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 《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 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 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 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那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算我孤陋寡闻, 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 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 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二战期间任《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 斯大林、 莫洛托夫非常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 几乎将他驱逐出境。《纽约时报》的老总, 也不中意他总是发出自己声音的稿子,准备炒他鱿鱼。在报纸上公然预警,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 为此, 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之罪, 结果不幸被他言中。越战期间深入河内, 披露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 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 “外科手术” 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道轰动了美国和世界, 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 为此, 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 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 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 “外科手术” 轰炸。几乎走遍世界, 经历、 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 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每当我与他今生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时, 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 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七月六号, 星期二。 下午, 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 “妈,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 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 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 不大爱讲话, 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 “妈, 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 不要太伤心……” 母亲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 唐棣的话让我不由得缩紧了肩膀, 转过张皇的脸, 等待着那件需要我 “挺住” 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上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 昨天, 从罗德岛回康州的路上, 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 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 莎洛特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三, 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 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 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 “你行吗?” 莎洛特说: “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 “不过我妈会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