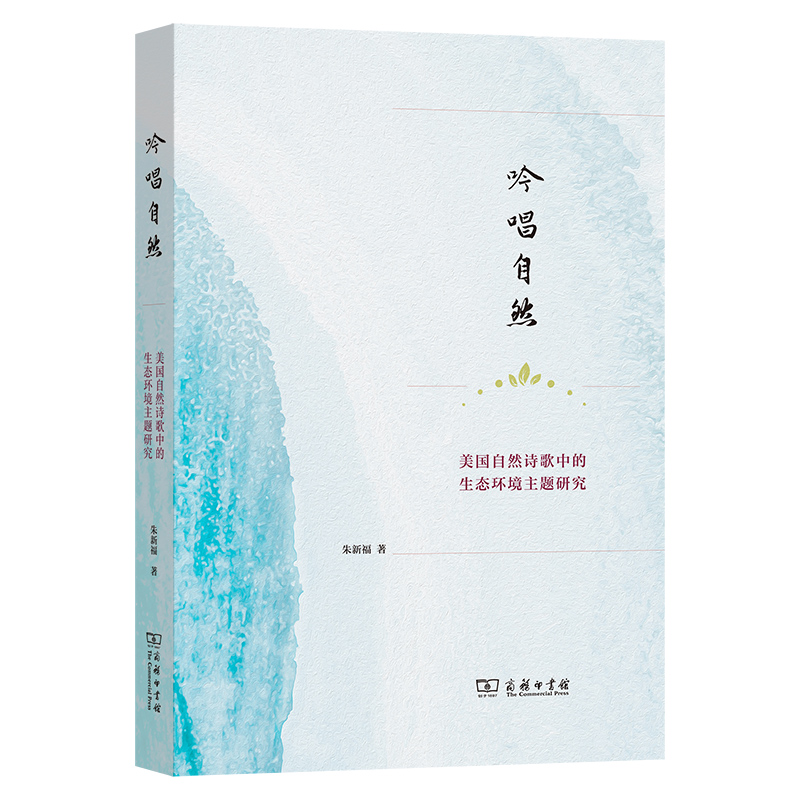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7.70
折扣购买: 吟唱自然: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环境主题研究
ISBN: 9787100242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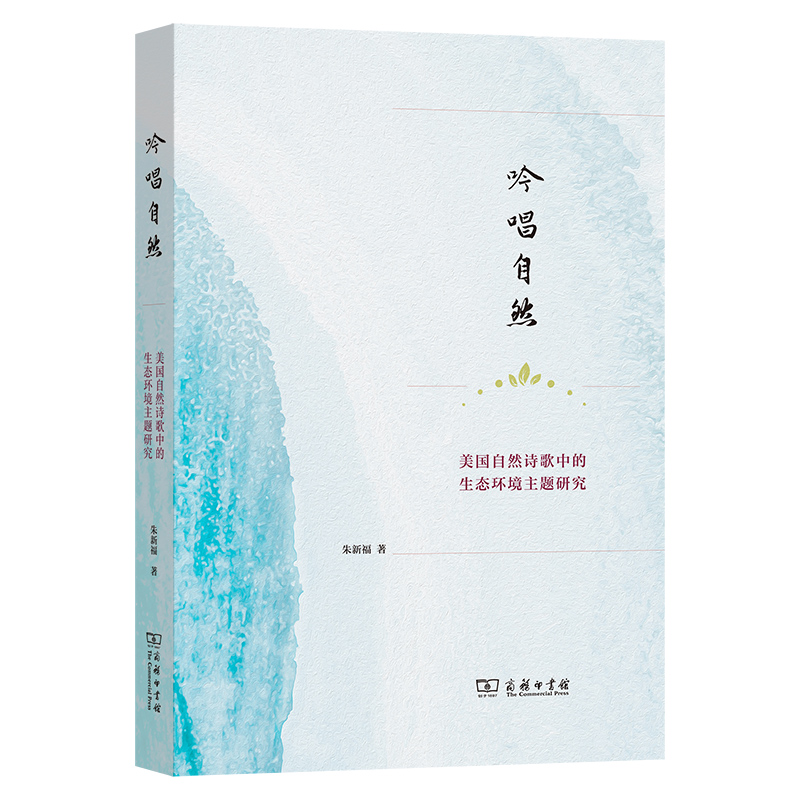
朱新福,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英语)建设点负责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美国诗歌、生态文学及英语教学。
每一部以书写自然为主题的诗歌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展示了诗歌的活力和价值。在当下的环境危机中,诗歌,特别是自然诗歌,具备一定的特殊功能,即能够在环境处于濒危状态时重新唤醒人类对自然的关注。 本书试图系统地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时期分析探讨美国文学史上代表诗人自然诗主题演变及其生态诗学思想的建构过程,通过了解美国自然诗歌的主题及其生态思想内涵,为构建我国生态诗学和美国文学研究及教学提供一定参考。研究美国自然诗的主题变化及其生态诗学思想的建构,需要关注生态批评关于人与自然、自然与人文的观点以及相关生态文化思想和生态文明观。本书内容涉及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和生态宗教学等学科,尝试把这些学科应用到对具体诗人及其作品的分析中,以加深研究内涵。本书尽量体现生态批评的纵深发展的标志,把相关主题放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经典”文本的颠覆和对自然写作的重估中进行。同时,内容密切注意当前生态批评的以下发展方向:对经典的批判、对文本的重构、对自然诗歌的重新评价、重建社会与生态的联系、语言与土地的重新接触等,突出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 本书以美国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的代表性自然诗人为研究目标,探讨他们自然诗歌的主题演变及其生态诗学思想建构。本书共分十七章,研究内容涉及十三位代表性诗人。具体内容包括: 一、探讨殖民地时期代表诗人的自然诗,揭示宗教背景下的自然描写及其生态意蕴,指出这一时期自然诗人朴素的、潜意识的生态意识。具体以布莱德斯翠特(Anne Bradstreet)的《沉思录》和泰勒(Edward Taylor)的《诗作》等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自然诗中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及其生态神学思想;阐述其自然诗中自然、人性、神性的结合及其生态意义,指出清教神学如何成就天堂般的生态阅读和描写,自然描写与清教神学二者如何共同建立对新英格兰的地域认同。 二、研究浪漫主义时期代表诗人的自然诗,通过分析其包含的超验主义思想、自然 精神与国家民族意识,揭示这一时期的自然诗歌如何从朴素的、潜意识生态意识演变为自觉的生态意识和自然思想。主要以布莱恩特(W. C. Bryant)、爱默生(R.W. Emerson)、惠特曼(W. Whitman)和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等代表诗人的自然诗为研究对象。 作为美国19世纪著名自然诗人,布莱恩特通过描写自然来阐发自己的诗学思想,其自然诗歌的主题表现在对死亡的随想、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对美国新大陆大自然荒野大地的赞美。布莱恩特的自然诗歌阐述了人生与自然的关系、死亡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森林、上帝和自然三者融合所表现的精神之美。同时,布莱恩特所从事的新闻事业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其新闻工作推动了当时美国的环保事业。 爱默生一生创作了许多自然诗歌,《杜鹃花》(The Rhodora)是他创作的众多自然诗歌中的一首。《杜鹃花》不仅体现了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强调的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内在价值,而且还阐述了“美为美存在”以及“人与花都是同一造物主的安排”这两大中心思想。《杜鹃花》充分体现了爱默生的诗歌特色,即诗的哲化与哲的诗化以及诗哲一体化的思想,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惠特曼在《草叶集》中通过对大自然的歌颂抒发了诗人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草叶集》中包含了生态思想的萌芽;而惠特曼的一部不为国内读者所知的散文集《采集日志》同样蕴含了深刻的生态诗学思想,自然是文学创造的源泉,诗人的使命是把大自然与人的灵魂联结起来,把常人眼中只看作物质世界和物欲对象的大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气息、精神韵致和神性内涵揭示给人们,使诗歌变成大自然沟通、走近和融入人的灵魂的精神通道。《采集日志》包含了对诗歌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生态功能的深切感悟。《草叶集》描写了大地、海洋、城市、乡村、风雨、鸟儿、动物、花园,甚至小小的不起眼的一堆肥料也是他笔下的闪光之点。惠特曼在描写自然界万物的同时,还试图在自然万物中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生态自然思想。特别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研究从19世纪美国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入手,结合美国本土的个人主义民族文化来重读《草叶集》。我们发现,惠特曼自然诗歌中还包含着明显的民主精神与现代化意识。“现代化”作为一个宏观化的辩证理念,象征着人类文明永不停息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思想理念、价值追求的全面革新。而惠特曼的诗作作为美国发展转折时期继往开来的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美国民主思想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大潮之下的全新发展与演进,是美国民主精神由抽象到具象,由理想化到世俗化转变的生动例证。 狄金森对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她明确大自然的功能以及自然与诗人的关系。狄金森创作自然诗歌和她的家庭背景、超验主义影响以及个人生活中的学习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同时和她的文学素养密切相关。科学知识使狄金森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玫瑰是狄金森自然诗歌中植物花草的代表;蝴蝶、蜘蛛、小蛇以及鸟儿是狄金森自然诗歌中的常客。狄金森通过“动物意象”即指以动物为载体的审美意象折射出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体会。狄金森作为19世纪一名女诗人,她想通过自然的描写来表述自我,表达那个时代的妇女意愿,表达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妇女在当时那个社会所遭受的孤独,表达真与美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表达一种狄金森式的哲学思想。 三、分析美国现代时期代表诗人的自然诗,研究其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三重疏远以及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批判的内涵,揭示这一时期自然诗歌生态演变的意义及影响,探讨这一时期自然诗人生态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特征。具体以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穆尔(Marianne Moore)和莱维托夫(Denise Levertov)的自然诗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他们与前期自然诗人在主题和艺术特征方面的异同来看自然诗的演变轨迹。 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Inhumanism)生态诗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现在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批判,强调人类不是世界万物的中心,不能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体现了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泛神论思想。岩石是自然的精华,赋予诗歌一种正能量;鹰是自然的灵魂,也是诗人本人的象征。杰弗斯的自然诗作涉及自然永恒、人类在自然面前渺小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警示等主题。在诗歌形式上,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诗学思想表现在回归英语古体诗歌的创作模式。作为一位激进诗人,杰弗斯提出“非人类主义”思想,其目的是追寻真正的人类价值,启迪人类拥有回归自然的心态。杰弗斯也是美国最早投身于生态文明构建事业的诗人之一,他继承了美国本土的超验主义思想,通过自然主义式的生态书写展示了原生自然的残酷多变与无穷魅力。诗人贯彻了“反文明”的价值理念,以辛辣的笔调批判了现代人破坏自然、庸俗腐化的物质主义倾向,直率地指出正是自然精神的丧失导致了现代人思想的空虚与迷惘。他的诗作虽颇有喜爱动物尤胜于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特色,但野性与人性之间的互通之处依旧鲜明,对动物淳朴天性的赞美反衬了诗人对于理想化人性的观照与追求。以非人格化的书写来反映人类生活,身居山野却仍心怀天下,这赋予了杰弗斯的自然诗作以更为广博的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 穆尔首先借动物诗歌来表现诗歌创作和诗歌艺术的本质和力量。穆尔的动物诗歌表达了她的道德立场和伦理思想,穆尔的一些诗歌虽然不是以动物为标题,但是依然以动物来“说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动物诗歌来表达她的自然思想和生态意义。著名诗篇《纸鹦鹉螺》(“ The Paper Nautilus”)中母爱情结与生态女性主义思及名诗《水牛》(“The Buffalo”)中的自然意蕴就是典型的例子。穆尔的动物诗歌告诉我们,动物是人类认识自然过程的媒介,几乎每一个人类的行动都可以用动物的行动来说明。她的诗歌中的动物意象和隐喻具有神、灵动、鲜明而准确,诗人将她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通过对动物的描写,穆尔自觉地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向我们展示她所理解的生态预警及对生命的敬畏,探索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莱维托芙把自己的诗歌风格称作“有机形式”(organic form),认为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诗人须投身社会生活,以提升诗歌的品质。有机的诗歌创作使莱维托芙把写诗看成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索,对大自然的不断思考,在大自然永恒的律动中找到平衡点。她用诗歌表达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包括生态环境意识。莱维托芙擅长以多视角、二元的观点来看待自然:在她看来,自然是美丽神圣,又充满恐惧和死亡的;自然不仅存在于乡村,而且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植物界的自然无处不在,而动物界的自然更是一目了然;自然是脆弱濒危的,又是繁荣昌盛的……她还创作了不少“生态抗议诗歌”,关注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 一、研究当代代表诗人的自然诗向生态诗歌的演变过程,揭示其体现的生态整体观、 生态预警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当代美国文坛最有代表性的四位生态诗人——默温(W.S.Merwin)、斯奈德(Gary Snyder)、奥利弗(Mary Oliver)和贝瑞(Wendell Berry)为研究对象。 默温创作的《林中之雨》(The Rain in the Trees)等几部诗集的内容表明,诗人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关注。作为一名生态诗人,默温强调“位置感”,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生态;他认为自然是语言的源泉,诗歌与大自然的韵律是和谐一致的,流露出鲜明的生态诗学思想。研究认为,我们从动物诗歌可以看默温的生态伦理结和诗学伦理结之解。在诗学伦理上,默温坚持诗歌是见证的艺术,诗歌形式是对一种听见当下生命经历的方式的见证。而默温一以贯之的诗艺探索和实践恰也见证了默温一生对人类破坏力的深刻反思、对自然世界绝对存在的笃信不疑、对诗歌艺术召唤沉默之声的毕生追求,以及诗内诗外知行合一的伦理操守。 斯奈德是美国当代资深生态诗人,他的生态诗学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北美印第安土著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思想,其二是东方文化中道家和禅宗佛学思想,其三是美国新大陆文化中由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倡导的回归荒野的自然思想。这三种文化思想的结合共同构建了斯奈德的生态诗学观。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绿色”诗人和散文作家之一,斯奈德推崇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政治与绿色无政府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心理学和环境保护主义思想。他所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斯奈德的诗歌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他的生态革命思想具有跨文化特征,融合了东西方诗学、土地和荒野、可持续性问题、跨文化人类学和大乘佛教等。斯奈德致力于挖掘和再现印第安文化和口述传统文学,寻找“古老的根”,以此作为社会革命、生态革命与无意识革命的文化基础。他在其自然诗歌中表达的“龟岛观”(Turtle Island View)与生物区域主义与印第安创世神话有何关联?他的自然诗歌中的印第安神话动物郊狼(土狼)要表达什么主题?他作品中使用的印第安神话动物郊狼和萨满与文化帝国主义有何关联?本书将分析他诗歌中的印第安文化元素,展现他对印第安人的立场,从而说明他的诗歌如何参与了国族构建和全球生态保护。 奥利弗一贯以书写自然著称。她的自然诗歌通过对大自然中最平凡意象的描写来反映自然界外表之下所隐藏的神秘与惊奇。她从小与自然为伍,自然环境造就她成为一名生态自然诗人。她以恋地情结抒自然情怀,以动物看世界。通过动物诗歌,奥利弗试图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动物生命、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与不协调关系、家园意识、自然世界具有的天然“完美”性以及城市环境问题特别是污染问题等等。奥利弗赋予自然真实的感觉,赋予它们情感、智力和精神。她替笔下主体说话并从中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对人类与自然界“客体”的脱离行为的批判,强调人类身体与自然客体接触的重要性。 贝瑞的生态自然思想离不开农耕、农场和农民这三个关键词。对贝瑞来说,农耕是连接他与土地的精神纽带,是他的宗教思想与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农场是他回归自然、批判工业社会的场所,是诗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特殊形式;农民是他作品中始终关注的对象。贝瑞的诗歌流露出他对土地情有独钟,蕴涵着他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表达了他对美国农业企业的批评,具有深厚的农业文化意识。贝瑞的自然诗歌表现出明显的建构生态家园的思想。生态家园理念作为贝瑞文学创作的思想核心之一,既反映了他对完整田园文化和理想化诗意生活方式的眷恋,也暗示了他对于当代美国人文生态环境的深深忧虑。虽然生活在美国农业文化日趋没落和都市文化迅速崛起的过渡阶段,贝瑞却始终坚守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力图维护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重塑大地伦理与荒野精神。他以开明的世界主义精神来解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分歧,建构了人类与动物间和谐互助、共存共荣的全新伦理关系,拒斥战争,拒斥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生态掠夺与生态殖民。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风格使他的诗作在纯粹的美学价值之外,承载了更为多元的生态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 本书以美国历史上的代表性自然诗人为研究目标,结合从殖民地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到现当代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研读各时期自然诗人的诗歌文本,分析美国自然诗歌的生态环境主题及其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