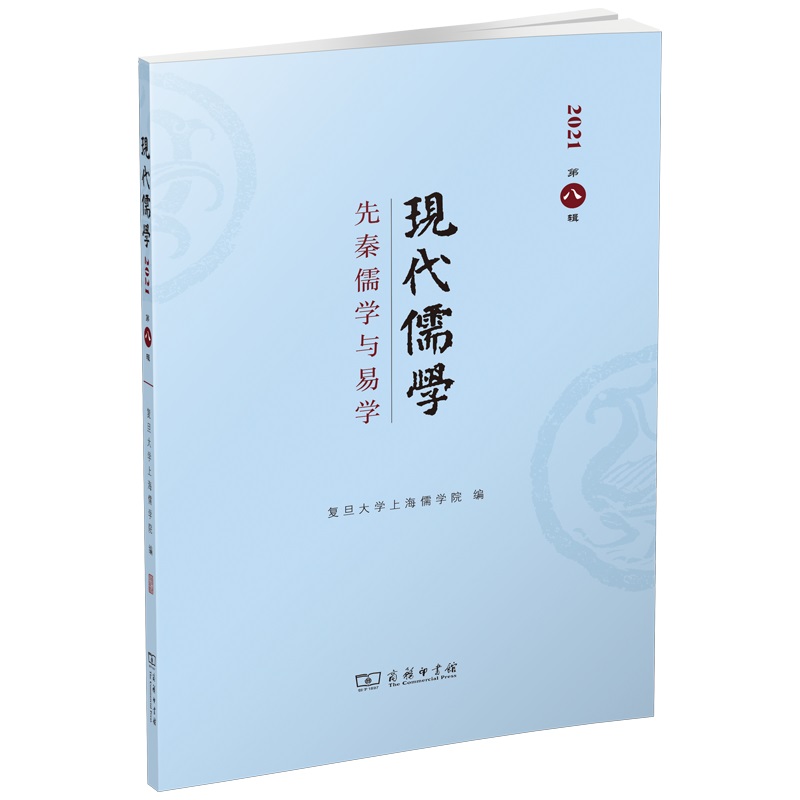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80.00
折扣价: 58.40
折扣购买: 现代儒学(第八辑):先秦儒学与易学
ISBN: 9787100199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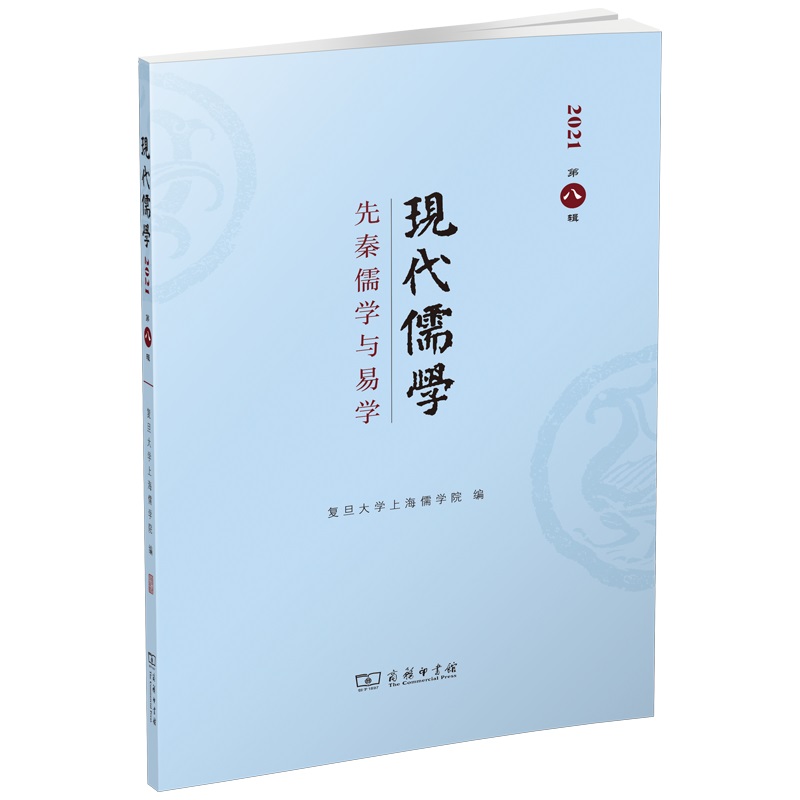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为复旦大学校设研究院,是从事儒学研究和传播的学术机构,以继承和阐扬中华文明传统、探索江南儒学的学术精神、推动儒学现代化、确立儒家思想的全球地位为使命。本期《现代儒学》由何益鑫博士担任主编。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著有《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等。近期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学、《周易》等。
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单个的德性不是“善”的最后标准。以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为例,有同情心是“仁”的基本含义。一个只要人家骗他说“有人掉入井里了”就会马上跳进井里去的人,确实很有仁心,而且不是一般的仁,是愿意舍己为人的仁。这样的“仁”很容易被人愚弄。可是不受骗上当,其实与“仁”无关,而是与“智”有关。用“智”来定义什么叫真正的“仁”在逻辑上不通。再比如,聪明是“智”的基本含义。一个能巧妙利用法律漏洞而成功逃避惩罚的人确实很聪明。我们不愿意说他“智”,其实是认为这样的“智”不义,这和“智”的本来含义无关。除非我们把“不义”也定义为“不智”。又比如“勇”的基本含义是大胆。一个敢于冲进火场去抢救一包方便面的人,确实很大胆。我们不愿意说这个人有“勇”,其实是因为一包方便面不值得冒生命危险。这样的“勇”很愚蠢。但愚蠢却也和“勇”的基本含义无关。用智慧来定义“勇”,逻辑上也有一个跨越。反之,单个的“恶”也不是“恶”的标准。柯普曼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点:一个极为固执而又有强烈控制欲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会非常有害,但他却可以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反抗暴政的斗士。 但是如果“德性”无法定义儒家伦理,那么“品性”恐怕也会导致同样的顾虑。品性是由各种德性组合构成的,大致相对于李晨阳所说的“价值组合配置”。如果单个的德性因有德性之蔽而没法用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之对错,那么各种德性的组合配置构成的品性也同样有各自的“蔽”,也没法据以判断其行为的对错。能够克服德性之蔽的,是经过“学”而获得的“发而皆中节”的功夫。 同时,“品性伦理”与“德性伦理”这两个标签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足以概括儒家伦理的丰富性。比如,儒家思想固然重视德性和人品的培养,但也以倡导传统的礼仪著称,以至于儒家体系甚至被称作“礼教”。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8.2)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克服德性之蔽的“学”,主要是学礼,因此礼也是儒家伦理的特点。孔子自己直到七十岁才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表明在此之前,他还是需要“矩”来约束自己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礼仪习俗和法律规范是超越了个人存在的社会现实,所以它们有一种客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前所述,在社会层面,不可能交付所有的人都去从心所欲地“权”,所以外在的规范体系是社会运作的基本保障。没有了这一点,很难解释儒家传统能够有如此持久的历史延续。 相比之下,我觉得用“功夫伦理”来概括儒家伦理更为理想。功夫概念是一个包含了“功法”“功力”“功效”和作为实践的“工夫”这四个子概念的概念簇,其总体的定义可以是“生活的艺术”。其中“功力”可以涵括德性和品性的内容(virtuosity,每一种德性virtue也都是一种功力),“功法”可以涵括礼仪规范和社会体制的内容,“功效”可以涵括功夫的有效性(efficacy)和美学价值,最后,“工夫”可以概括学以成人的重要性,修炼所需要的实践过程和进展的层次。 (倪培民:《德性之蔽——从<论语>中的“六言六蔽”说起》) 本期《现代儒学》结集了先秦儒学和易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 《现代儒学》第八辑的主题为先秦儒学与易学。“先秦儒学”栏目收入干春松、倪培民、张汝伦等知名学者的文章,内容包括对《论语》《中庸》《荀子》等经典的解读;“易学工作坊”文章都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第一届易学与哲学青年工作坊”(2020年),收入了易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期文章涵盖了“先秦儒学”和“易学”的重要分支,反映了学界研究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