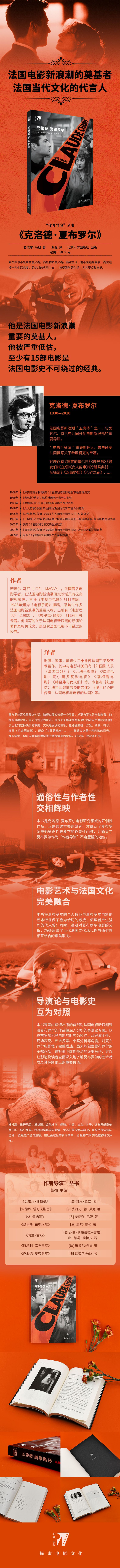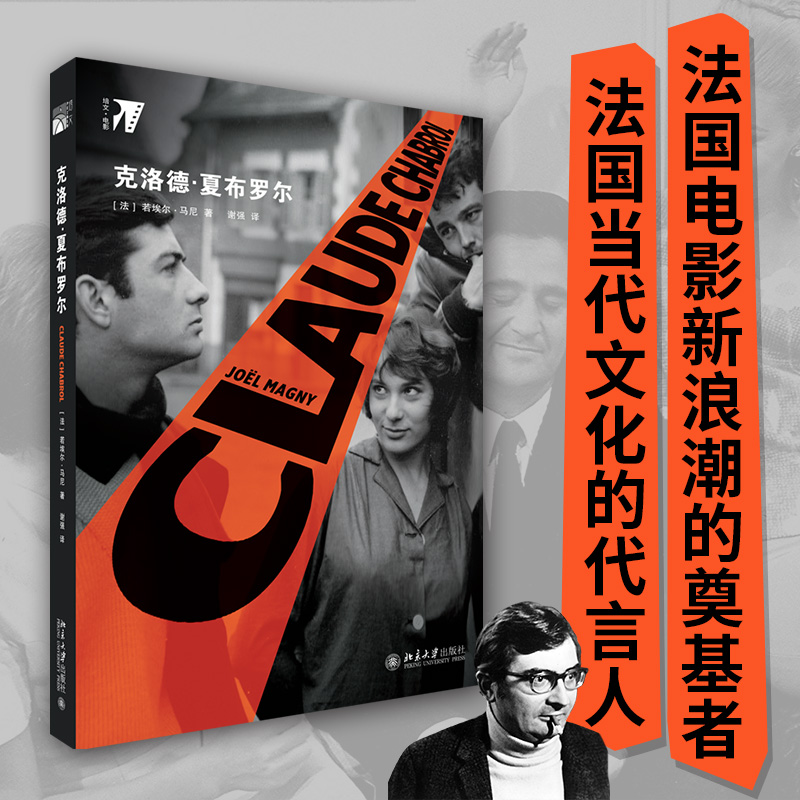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克洛德·夏布罗尔
ISBN: 978730131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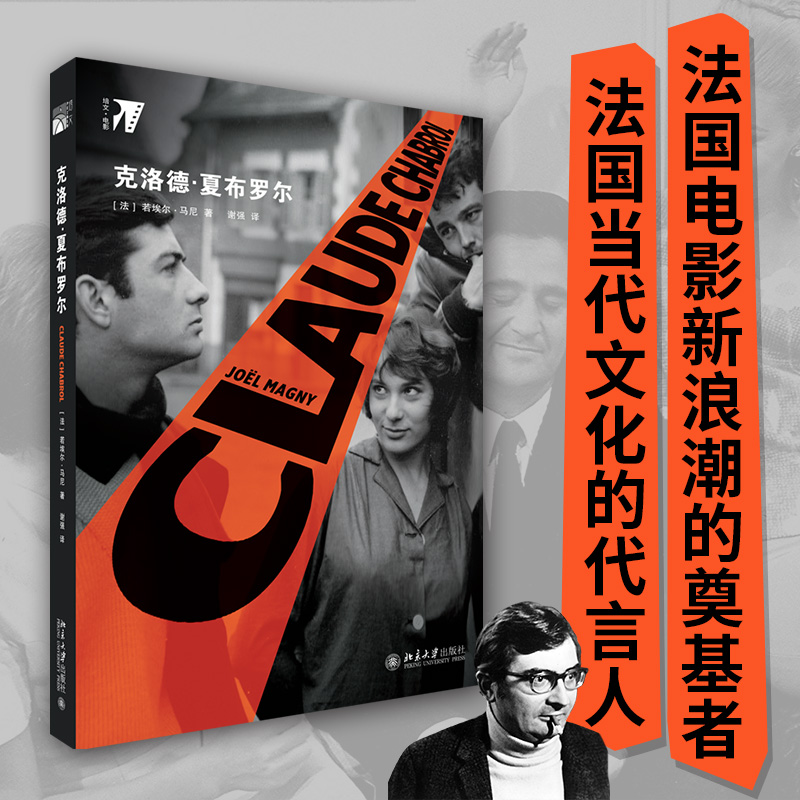
若埃尔?马尼(Jo?l Magny),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曾任《电视与电影》月刊主编。1986年起为《电影手册》撰稿,采访过许多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人物,出版有《电影理论》(1982)、《埃里克?侯麦》(1986)等专著。 谢强,译审,翻译过二十多部法国哲学及艺术著作,其中与电影相关的有《外国影人录(法国部分)》《运动—影像》《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福柯看电影》《特吕弗与女人们》等。专著有《红磨坊:法兰西激情与夜的文化》《漫不经心的传奇:法国电影与电影的法国》等。
走向新浪潮 1953年12月,克洛德·夏布罗尔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坦利·多南和吉恩·凯利的《雨中曲》的影评,从此走上电影舞台。与其他同路人相比,他入行稍晚,因为他没有参与《电影故事》(1950年5月至11月)前五期的撰稿。在这五期中,里维特、戈达尔、杜歇、多马奇等人纷纷出场,杂志社社长、创办人是莫里斯·谢雷,即埃里克·侯麦。夏布罗尔只是偶尔为《艺术》周刊的栏目撰稿,该周刊大力宣传年轻的特吕弗,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传播后来成为新浪潮的思想主张。夏布罗尔与特吕弗共同为该刊撰写了“相识希区柯克”的文章。 其实,这位20岁出头(1930年6月24日生于巴黎)的电影爱好者早就认识“侯麦这一伙人”。夏布罗尔曾在克勒兹省的一个村庄里“建立”了萨尔登影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废弃的旧仓库放电影)。“二战”中,他在这里度过童年,1945年回到巴黎。先(勉强地)通过中学会考,学了一点医药学(为了继承父业和祖业),而后又学了文学和法律。在此期间,他常去大学电影俱乐部,尤其是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正是由侯麦主持的,“一个瘦高挑,棕头发,很像吸血鬼的人”。他在这里还遇到了最忠诚的会员,如保罗·热古夫、弗朗索瓦·特吕弗、夏尔·毕什、克鲁德·德吉弗雷、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他们经常相会,比如在迈西尼街举办的电影晚会上,或者在帕拿斯影院以及代尔尼影院、百老汇影院、艺术影院、反射影院和麦克马洪影院。 骂该骂的人 “我,从来不是好影评人,我的确不是干这事儿的料。”后来他这样解释道。他是真的不具有理论天赋,还是朋友的媒体炒作?人们只要稍微仔细阅读他的文章,尤其是1957年他与侯麦合著的关于希区柯克的书,就不会再怀疑了。几年后,他在界定评论的功能时,告诉我们他这代人投身写作的原因:“我随时愿意捍卫正确的东西,这没说的,必须倡导好的东西,但为了宣传好的东西,就必须什么都好,甚至包括对那些该骂的人的回敬。”人们认同这个团体的论争态度,尤其是1954年1月弗朗索瓦·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檄文《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之后。批评界首先向学院派,向德拉诺瓦、奥当—拉哈、让·奥朗什和皮埃尔·博斯特的冷漠和空洞的技术宣战,捍卫茂瑙、朗格、刘别谦、雷诺阿、希区柯克这样有“高度”的作者。 但对夏布罗尔来说,电影评论不是自己的目的:“除了巴赞,大多数做电影评论的人不是要做电影,而是要深入研究某些美学或其他问题:他们不是出于一种乐趣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喜欢或不喜欢某部影片。”还是在谈论巴赞时,夏布罗尔明确了电影评论的界限:“巴赞首先由于喜欢分析,才喜欢上电影创作。这样说太笼统,但这里确实存在着创作的某种综合元素,巴赞对此不感兴趣。”正是这种不是针对观众,而是服务于电影实践者的综合元素,深深吸引着这位未来的导演:“总之,电影评论是有益的。人们最终可以发现某种方法、某种美学,就是说……个人的美学。” “但愿快乐长存” 这位未来的导演显然没有全力投身到电影批评之中,但这些早期的文章告诉我们,这些作者的爱好以及他们作为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夏布罗尔希望看到的效果出现了,他试图在自己独特的新闻写作中获得这种效果。夏布罗尔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已经成为一个预期:“但愿快乐长存”。 除去夸张、热烈和抓人的语气,以及多南和凯利音乐剧激发的快乐状态,将一种所有人接受的大众类型,与这个题目所代表的巴赫大合唱在文化上的阳春白雪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悖论。不客气地说,美国电影是最不纯粹的电影,其形式毫无高贵可言,属于混杂的商业娱乐形式,但却最有可能成为承载巴赫世界的美丽与神圣的现代艺术载体。对于电影评论者而言,影片的成功首先在于类型,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张力:“舞蹈是人类表达无法言说的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而人类始终无法言说的东西——人类在卑鄙和失望时可以喋喋不休——就是自己的快乐。” 夏布罗尔的抱负不是要在手册的栏目中把音乐剧定位为高贵的类型片,因为早在1953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他是想把这部影片界定为作者电影——批评主要集中在吉恩·凯利对于合作者斯坦利·多南的重要作用上——把它视为完整的电影手法,也就是说只服从于电影和场面调度的唯一权力。《雨中曲》“从头至尾,彻彻底底是导演的作品,一个使用老工具玩出新花样的导演的作品,运用这些新技巧,以最引人入胜的严谨性表达心灵中最短暂但却最美好的感动”。 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电影手册》的路线,至少反映了《电影故事》的倾向,后来,人们称之为“希区柯克—霍克斯”倾向。 夏布罗尔最鲜明的特点是执意对具体范例进行演示,因为他对整部作品或一些段落在观众中产生的效果很感兴趣:“前几分钟,劲爆而欢快,让我们进入完美的接受状态;尽管我们开始时有些抵触,尽管思想上有些担忧,但这些都神奇般地被一扫而光,没有任何抵抗。”这位批评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吉恩·凯利不需要取悦,而是要说服……要证明整部影片的大胆风格。”他细致分析了导演的目的:影片“不是要取悦感官(如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满怀欣喜地获取感官愉悦),而是要获取心灵的愉悦——这多么令人难忘啊”。 说服、证明,这是这位未来导演的心语。他审视导演所遇到的问题,思考不同的解决方法,对应该绕开和规避的陷阱与错误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庸俗的、所谓‘圣洁’的色情乃至多愁善感的路术,他都禁止使用;对于恶毒的讽刺、可耻的模仿、恶人的武器,他绝对弃之不用;对于任何滑稽、无端的假想,任何柏格森式的搞笑机制,他也予以杜绝。” 这种勾画的热情、对叙事和场面调度等具体问题的关注,并不是要赞美技艺,或是对观众的充满魅力和诱惑的无情操纵。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部电影在各个方面实现同一目标的方式:“像这样精致的音乐片不应该存在……所有构成它的元素——比布雷斯冷餐元素还要丰富多样——都在表达这种心境……”在另一段中,夏布罗尔提出一个更加苛刻的电影概念:“因此,把这些舞步看作一种思想的严谨表达是荒谬的。” 这段文字清楚地勾勒出一个评论家的肖像,他已经以导演的身份来看待电影了,综合性的考虑多于分析。在一篇名为《个人的事》的笔记中,他断言导演安托尼·贝里西耶“懂得许多电影真谛;比如,必须指导演员;影片的特殊性必须紧扣人物关系;确实存在眼神的炼金术,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最好的交响乐并不总是使用大鼓”。这也是他几年后的电影实践。他所说的大鼓效果似乎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导演之路辩护,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大鼓,但不是为了增强效果,而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最明显方式,“(这位导演)似乎对自己的艺术胸有成竹,意识到要消除效果,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中,夏布罗尔是最早的开创者,也是作品最丰富、拍摄类型最多样的导演。作为新浪潮五虎将之一,夏布罗尔的电影艺术成就被严重低估。与戈达尔、特吕弗、侯麦、里维特相比,夏布罗尔不仅知名度不如他们,而且在评价上也经常被人们忽视。但实际上,夏布罗尔的电影创作具有极高的艺术自觉与个人特色,他连通了艺术与通俗、现实与梦想,也是连接法国电影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在国外,对于夏布罗尔的正名,正在逐步展开,但在国内,关于夏布罗尔的专著尚未出现,本书的出版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想要了解夏布罗尔,或者完整了解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影迷和读者,具有极高的阅读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