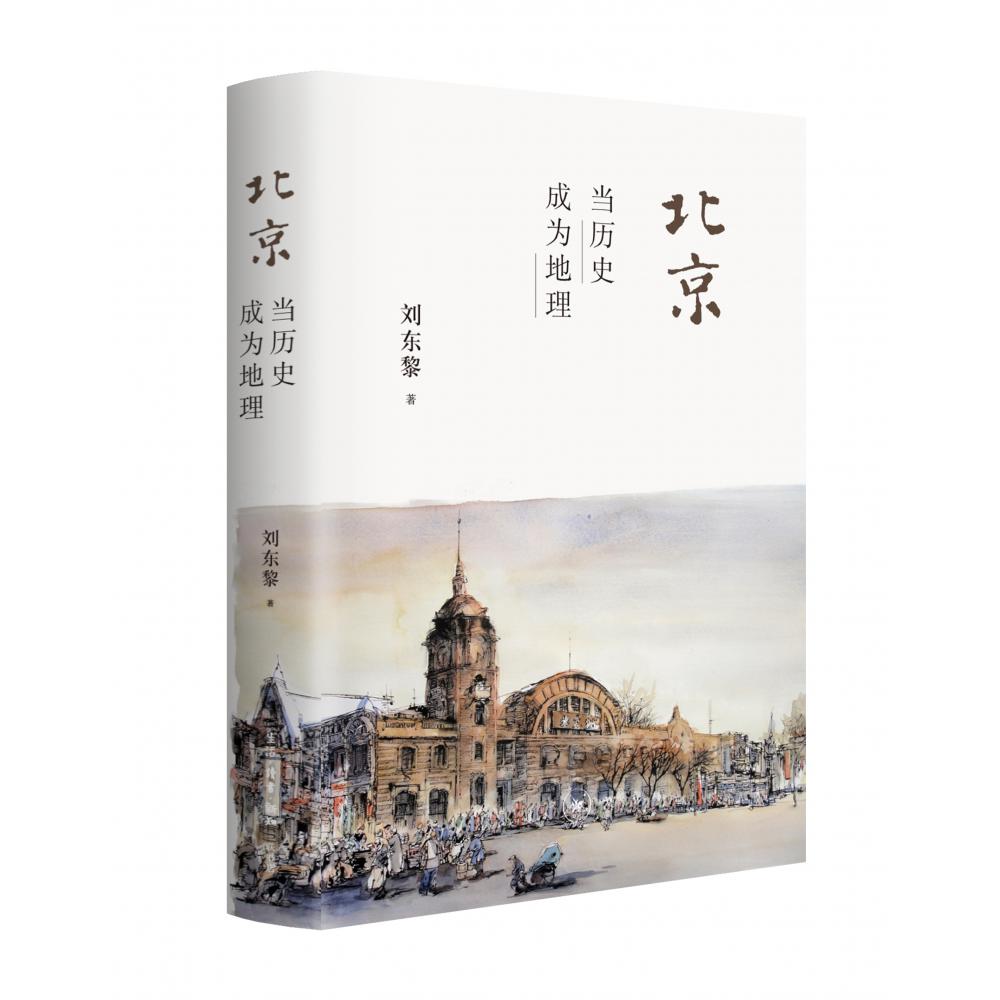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9.64
折扣购买: 北京(当历史成为地理)(精)
ISBN: 978710807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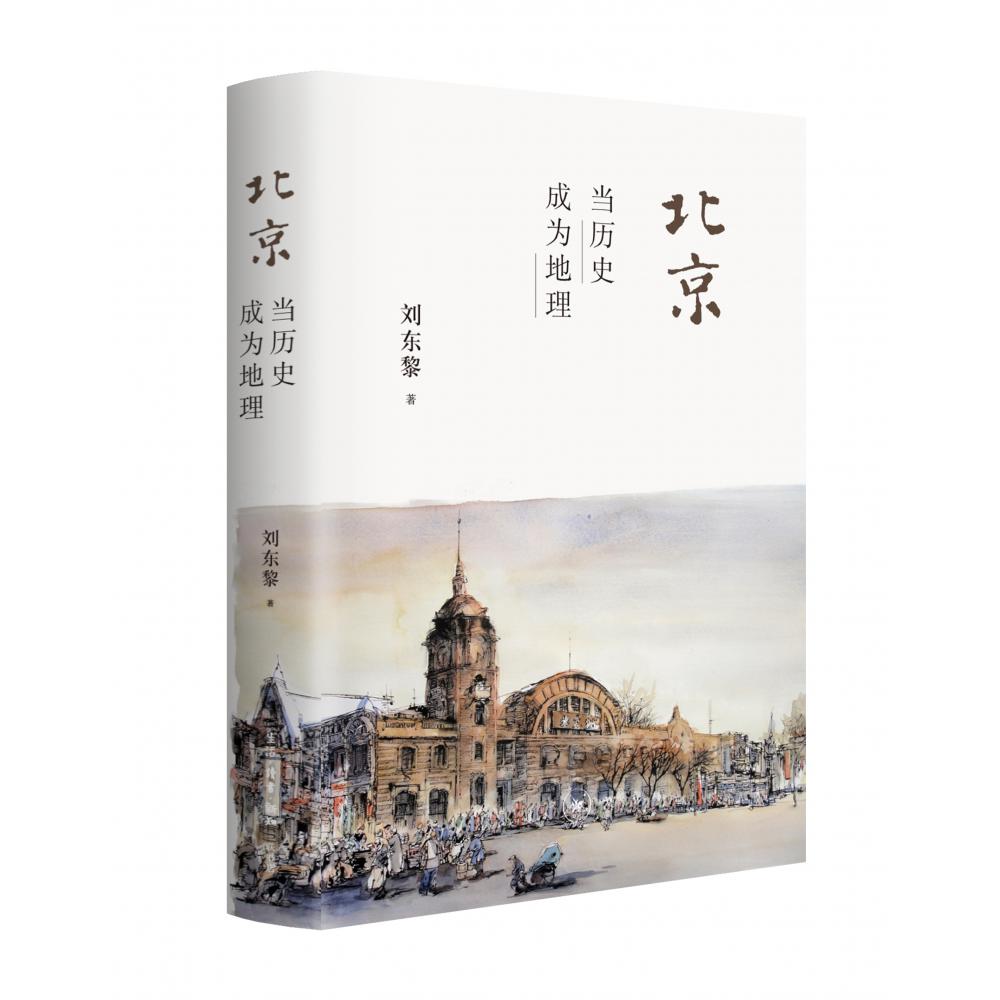
刘东黎,文化学者。著有《北京的红尘旧梦》《月涌大江流》《印象玫瑰》《江河在上》《黄花落 黄花开》等多部作品。
《忆念中的春明旧事》 北京的秋,如今已然和郁达夫眼中的故都很不同了。几十年日新月异,许多事物付之逝水,也包括与文化古都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的情调,再难“招魂”。北京的风景也永在变幻,星移斗转,景异人殊…… 这几年来看了不少北京民俗方面的书,有不少是邓云乡先生所著,作者用个人客居京华的生活经历,写燕京风物、市尘民俗,文笔清幽,读来饶有趣味。尤其在书中遥望到的京华胜景,残留着 20 世纪 20 年代市井文化的气息,那一缕早已逝去的旧京情调,着实令人感怀。 可以看出邓云乡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身上深深地濡染着中国乐感文化的历史遗留,笔下有着浓重的末世士大夫的情调。包括他的“文化古城纪事”系列,也是传统中国文人寂寞中的生活所依,精神趣味所恋。“说来也简单,就这样在老人们的爱抚教导中,使我养成了热爱京华风物,留心京华旧事的习惯。遇到旧时文献,或前人著述,或断烂朝报,或公私文书,或昔时照片,以及一张发票、一张拜帖、一份礼单、一封旧信……均赏玩不置,仔细观看,想象前尘,神思旧事。” 灯火阑珊,旧京难忘。邓云乡从 1953 年离京,一直客居海上。岁月沧桑,返求内心,总是难免有无法释怀的时刻。翻其著述,扑面而来的都是故土的乡愁,“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我对燕京乡土,亦充满了故园之情,故旧之思,故都之爱”云云,满目皆是弥散着敦厚之气的旧京味道。 燕京是北京的别称,唐都长安城东面三门的中间一门叫春明门,后人以长安和春明作为当时的都城的别称、雅称。至明清时,长安春明专指都城北京。翻开《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增补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北京四合院》等书,节候、风物、胜迹、风景、饮食、技艺,都豁然呈现。书中涉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京胡同、街道、城楼、四合院、厂甸、庙会、商业区、旧书肆、剃头挑子、提笼架鸟、童谣与市声、驴夫与洋车夫、豆汁儿、腊八粥、天桥、影戏、评书与戏曲、说书人等等,将旧京风情的段落串联成一幅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城墙宽厚严整,城门雄伟壮丽,天桥、厂甸热闹非凡,四合院里和谐宁静,四时八节百食不厌的小吃,街头巷尾淳厚、质朴的民间风情…… 这些记忆都不因岁月而褪色。我品读出一位俯仰尘世、出入雅俗的老人,确乎有着中国古典传统的大家风范,是属于旧时代的名士风流。掩卷之余令人忽然想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怀乡病的根源。邓云乡的一抹乡愁越过时空感染着我,时过境迁,人事如烟,让人不禁思之黯然。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第二次成为民国首都。国民政府选择南京作为都城,固然因南京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地位,同时,也是考虑到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遗嘱:“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癔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 历经金、元、明、清四朝的中华之都北京,从此变为“北平”。一下子丧失了首都地位,过剩的建筑设施和劳动力,大多将用于休闲消遣,北京文化精神里最富魅力的气质由是发扬到了顶峰。 不愁衣食的闲散,为一座都城带来了别样的生活情调。没有了漕运的重负,没有了首都的光环,但明月依旧,城郭如故,可以安静地做它的文化古城。北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并前所未有地成了平民的乐园。在四合院里,老北京人种下了夹竹桃和天冬草,“天棚、鱼缸、石榴树”所构成的温馨气氛更加宜人。 还有众多的学者和艺术家,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沉稳的文化情怀。而从容不迫、宁静安详、阅尽繁华的故都气象里,也有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温柔敦厚的历史风气,“五四”新文化开创的传统,都深深地在故都积淀着。可以说民国时代的北京,有着文化形态上最大限度的完备性。这时的北京,也就是后来经常勾起人们感怀的“老北京”,它宽和醇雅的气息流散至今。 那时的北京,在西方人的眼中,是散发着东方气韵的中国故都,是“全世界最悠闲、最舒适的城市”,是辉煌东方栩栩如生的象征。这可是八百年的皇皇帝都啊,一景一物,都大有来头和讲究。 在国人眼中,更让人充满感怀、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最壮美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是昔日皇家园林里植于辽代的古柏、倒垂的翠柳、汉白玉的桥梁,以及随处可见的花草…… 颐和园、雍和宫、白云观、潭柘寺……遍布城内外的宫观寺庙,每一处都引人入胜、美不胜收;琉璃厂、大栅栏的京味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前门外到处都有戏棚子和茶馆,也是其乐融融;天桥有把式,厂甸有庙会,隆福寺有的是可心又便宜的东西。风骨凛然、意态不凡的老城墙,是老北京安身立命、走到天涯海角都忘不了的所在;就连那些不起眼的、纵横交错、彼此相通的胡同,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把人引向某座幽深静谧、大有来历的古迹名刹。 在时人的眼中,南京,在 1938 年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进步和工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京呢,则代表了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命的和谐。北京是少数具有独特文化性格的城市,它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如此自然地凝结在一起。“巴黎和北京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北京比巴黎更美。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用英文写了追怀北平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以自己的方式描述北京“难以抵御的魅力,以及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 对于许多现代城市的居民来说,“房间种树”已是一种奢求了,而老北京城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领悟却是如此之彻底,它简直是“树间种房”。盛夏之际,四合院里的绿树为你撑起了一把巨大的遮阳伞;而在数九寒冬,树叶没了,直射而来的阳光让你满屋生辉。照郁达夫的说法,这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你站在景山往下看,只见如洪水般的新绿。因为北平的四合院本就低矮,院子里又往往种有枣树、柿子树、槐树,到了春夏时节,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绿荫中,很难再见屋顶。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除了红墙黄瓦的皇宫,其他全都被绿树所掩盖。皇宫不像民居,不能随便种树,有礼仪、审美的因素,也有安全的考虑。北平的四合院里,有真树,有假山,大缸里还养着金鱼和小荷,把大自然整个搬回了家。 “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老舍的一席话道出了北平的妙处。 文化古城的时代,俗调与名士流韵,记载着另一个历史,那是沉淀在历史深处的人情的晶石,是与紫禁城里的风尚大不相同的。海王村公园中央出售茶水的高台,琉璃厂东街一家叫作信远斋的小铺,是那个时代受人追捧的前卫小店;春节时分,书画商们在隆福寺外面搭制一些大席棚,悬挂屏联条幅,陈列扇面古卷,铺排散册残页和金石文玩。夕阳西下,微风吹衣,旅居京华的文人学者访得久觅而不得之书,夹之而归,更是人生一乐。 在那十几年间,北洋时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都已不复存在,作为首都时代的雍容气派,已杳不可寻。北京城变为了一个彻底的文化名城,其生活氛围之清雅平和,无以复加。英国作家哈罗德在那个年代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只不过住了短短数年,然而在回到伦敦十几年后,他仍然一直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渴望在自己的余生里,能够回到这座有着独特东方韵致的古城。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文教事业进展神速,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城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以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等高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重镇,使北京成为最有学术氛围和人文精神的地方。新锐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活跃,让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肇始之地。“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学贯中西,成为晚近中国现代文明的盗火者,而北京城的包容精神,也使得处于不同文化境遇和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都有足够的空间振翅高飞。 当时很多大学都建在旧日王府,如中国大学在郑王府,民国大学在醇王府,华北大学在礼王府,协和医大在豫王府,燕京大学在睿王园,清华园则在淳王的“小五爷园”。北京的大学有着最纯正的学风、最高雅的品位和最自由的空气,包容着古旧和现代。“除了巴黎和(传说中的)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北平是宏伟、北平是大度的。它容纳古时和近代,但不曾改变自己的面目。”(林语堂) 当时有“左边红帽子(陈独秀)、右边黄马褂(辜鸿铭)”的说法,至今想想仍是别致的一景。国子监、翰林院里有着中国士子的治学传统,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式的教育空降而来、落地开花,也不显突兀。新与旧、雅与俗之类的二元对立,在北京却很少有什么冲突与抵牾,都能被宏伟宽厚的北京城一一接纳。 只是一个忽闪,历史的追光就从这片土地划过去了。风物追怀,成为流亡南方或远走海外的学者文人们一生无法放下的心灵慰藉。“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老舍《想北平》)风清云冷,凄寒难耐,旧京的美丽风物却在这个怀乡人的泪眼里无尽地漂浮。千里之外,即使有梦,那梦境也更加遥远缥缈了;深夜里有稀稀落落的犬吠声和更夫的梆子声,他以为是过往的梦境。这位历尽沧桑的作家,在异乡追忆着故乡北京那些不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晨光熹微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模糊。 时局动荡,内忧外患。老北京人的生活却并没有停下来,似乎一切都按部就班,整个世界处于生活之外;即使在 1948 年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北京城面临战争还是和平的抉择,八方风雨,河山鼎沸。城内的国民党官兵,心事重重地四下里走动着。然而当天一亮,人们还是进行着日常的生计,依旧随处可见蓝布棉帘,万字栏杆,老店铺门槛,城墙下的小果摊,以及鲜红的冰糖葫芦。即使在这个城市面临最严峻态势之时,蓝天下划过的鸽哨声,也几乎让人刹那间忘却就在身外的烽火硝烟。 现在,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变化大得让人目瞪口呆,高楼大厦、环城高速公路、城铁、高尚住宅小区、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涌动的人群,已经重新切分和组建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取代了曾经作为北京文化象征的蜿蜒的胡同与庭院深深。我想起那种我们文明进化过程中深恶痛绝的资源“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行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呈现的方式也随之而变了,千里万里,也能在数小时内抵达。如同一首被按了“快进”的歌,顷刻播完,节省时间的同时,也节省了聆听。 这本小书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旧京草木风物浸到我心里的不止这些,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我沉溺于一个个场景,一些或平淡或特殊的心情。一些历史记忆不去触碰,还不觉得如何,这一铺陈写来,心里隐隐便泛起惆怅。 这大概就是一种北京情结吧。“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北京的秋,如今已然和郁达夫眼中的故都很不同了。几十年日新月异,许多事物付之逝水,也包括与文化古都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的情调,再难“招魂”。北京的风景也永在变幻,星移斗转,景异人殊。 柔和的秋阳斜铺到身上,几只喜鹊呼唤着在枝头盘旋,闪光的翅膀上仿佛驮着许多古老的故事。水墨黄昏和暖色灯光,深灰色的墙和暗青色的路,午夜漏断人初静的梆声,胡同里穿梭往来的吆喝,马车顶盖和独脚推车……我忽然觉得这副情景是这么熟悉,仿佛从这里走出去就是古老的中国,清贫而纯真、匮乏而优雅、混乱而温情,那是纳兰性德、林语堂、老舍、梁实秋的北京;是“常四爷”“祥子”“英子”们的北京;是那个被称作文化古城的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