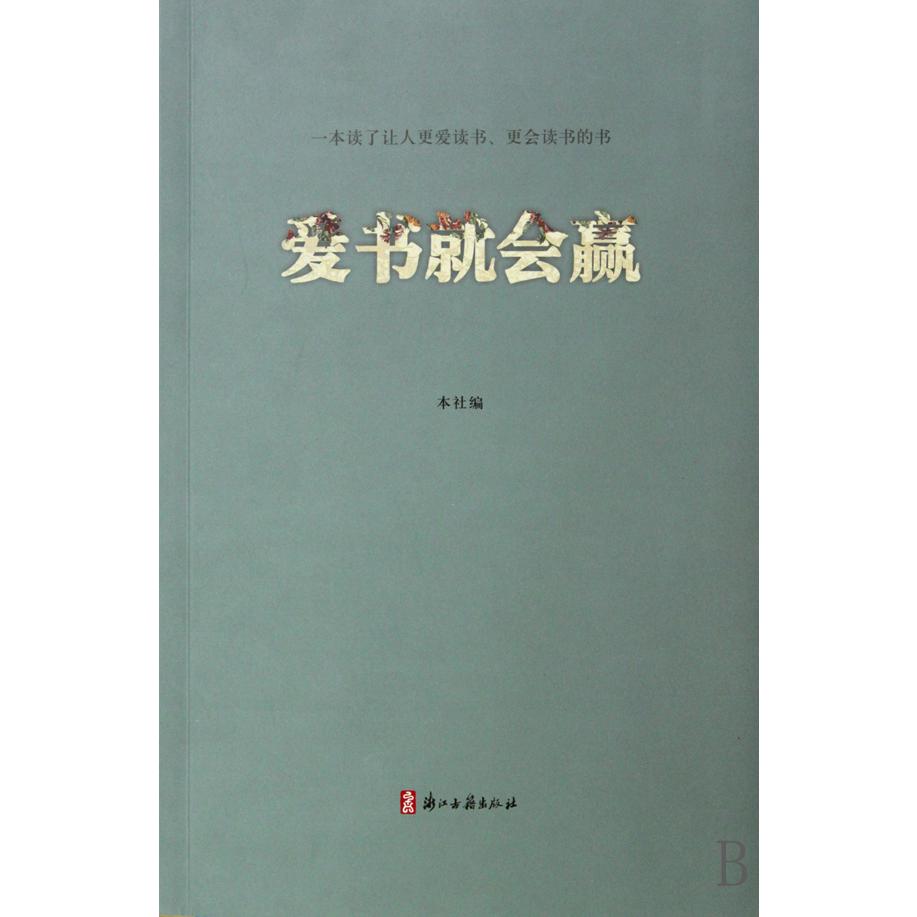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古籍
原售价: 10.00
折扣价: 6.50
折扣购买: 爱书就会赢
ISBN: 9787807155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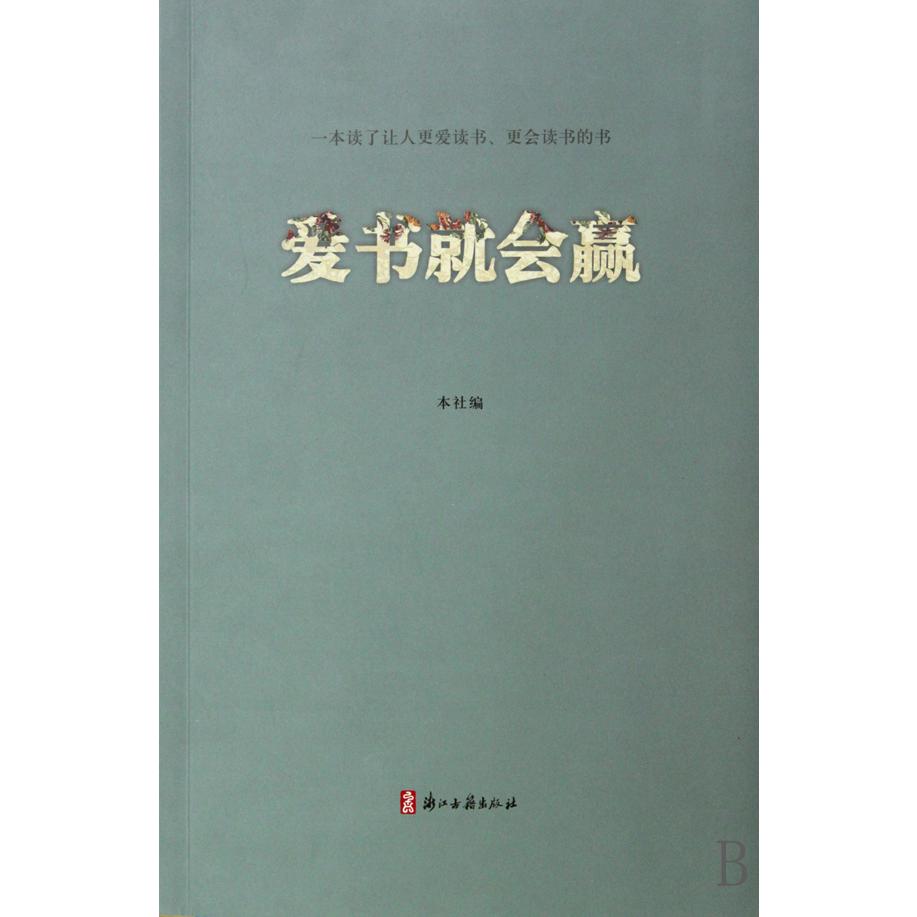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 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 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 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 ,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它的书,几 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用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 地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 自己记别的方便。我曾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 装书,在舟车上或其它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 笔做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 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 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 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蔡 元培《我的读书经验》) 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 所得。例如: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 动手的。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 记。不则还塞之矣。”(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手到的 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 ,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 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 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 你自己的了。(胡适《读书》) 认字不可随便放过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 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 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 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 ,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 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 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 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胡适《读书》) 自思索,自做主 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 ,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 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 了。(鲁迅《读书杂谈》) 记笔记,做卡片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 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 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 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 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 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 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 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做卡片的 训练,宜于早下工夫。(朱光潜《谈读朽》) 读书须先知味 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 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都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 法。读书须先知味。读书知味。世上多少强读人,听到此语否?这味字, 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 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 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 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 胃滞诸病。(林语堂《论读书》) 读出自己性灵来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说回前面论点,最后一点,也即读 书全部之主旨,读出自己性灵来。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 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 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 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 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竞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 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 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 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畿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 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 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哗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 知畿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 》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 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林语堂《论读书》)P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