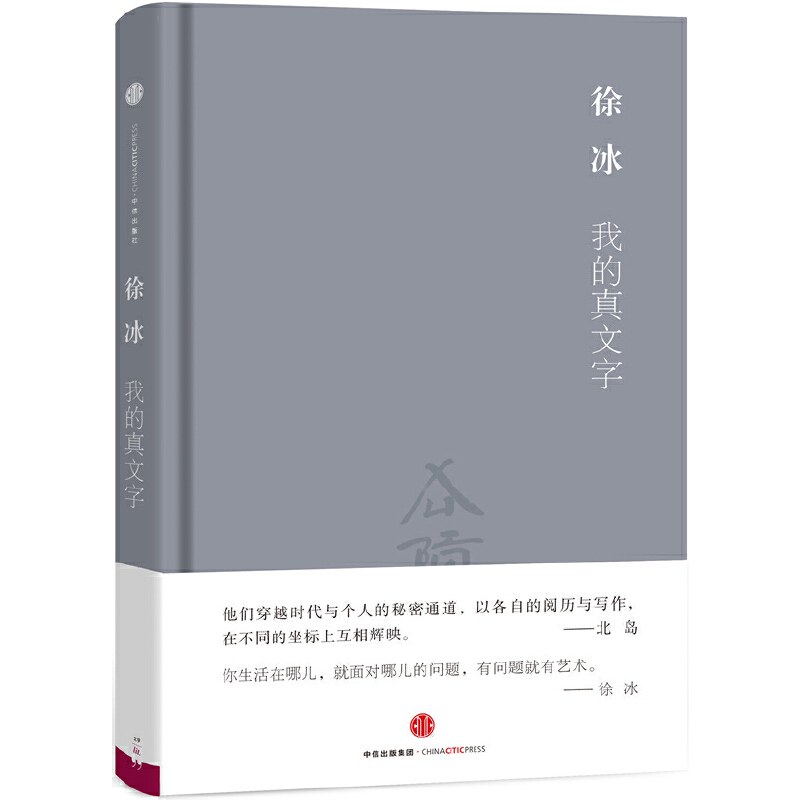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我的真文字
ISBN: 9787508655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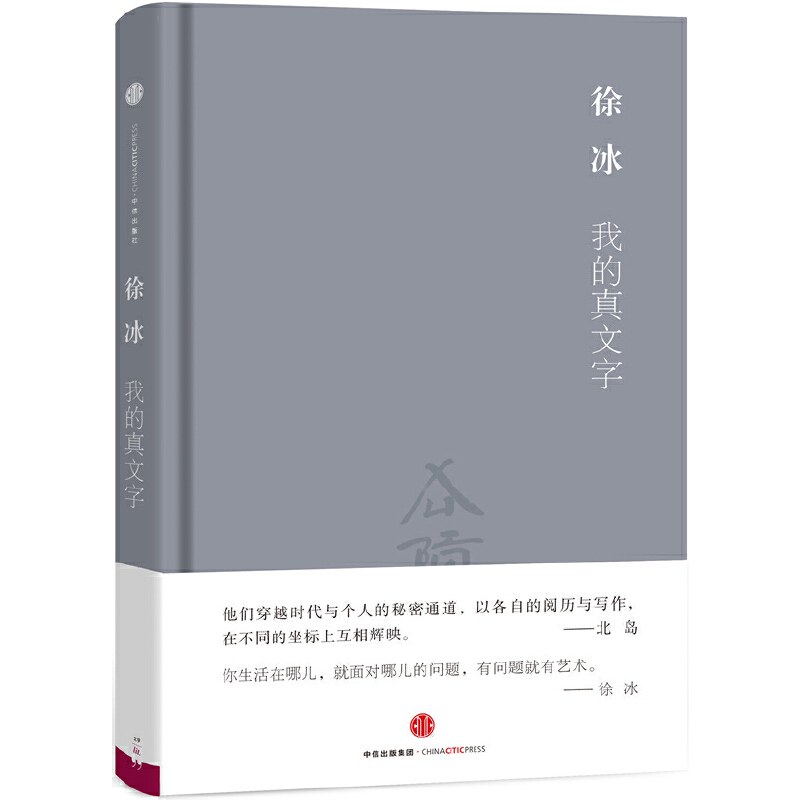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 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 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 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 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 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 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 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 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 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 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 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 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 黄镇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 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 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 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 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 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离被围堵的“青 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 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 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 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 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 在那时真是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 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于是 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 —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相互默许 。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 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 年领袖。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 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进入学院的机会。应该说 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 的成长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 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 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 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 人民”的,有些人上一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 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 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精神病的( 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精神病的特别多 ,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 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 :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 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 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 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 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 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 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 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 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 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 ,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 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 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 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 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