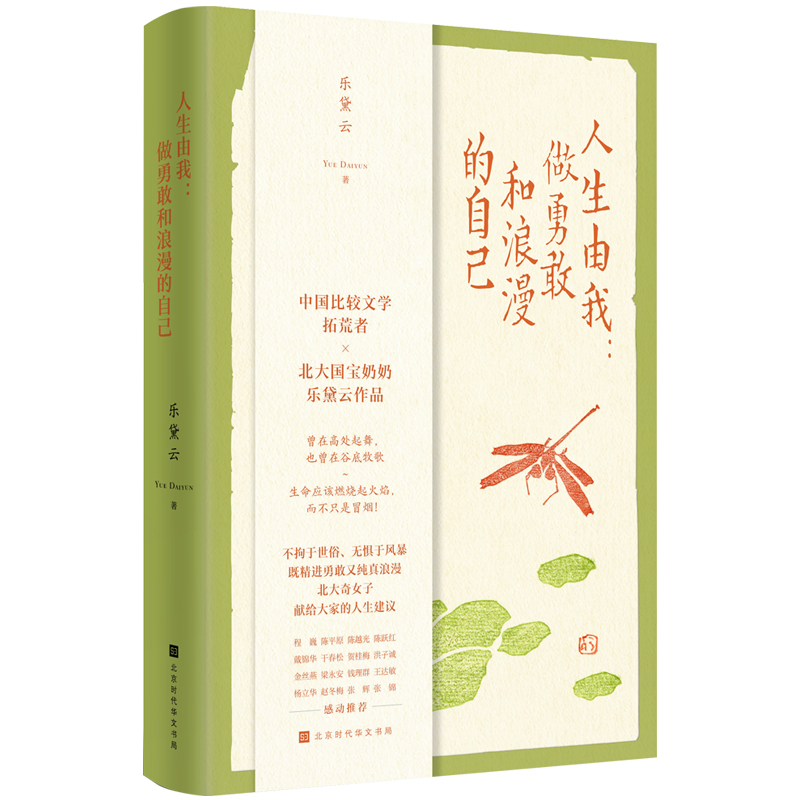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5.40
折扣购买: 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
ISBN: 9787569950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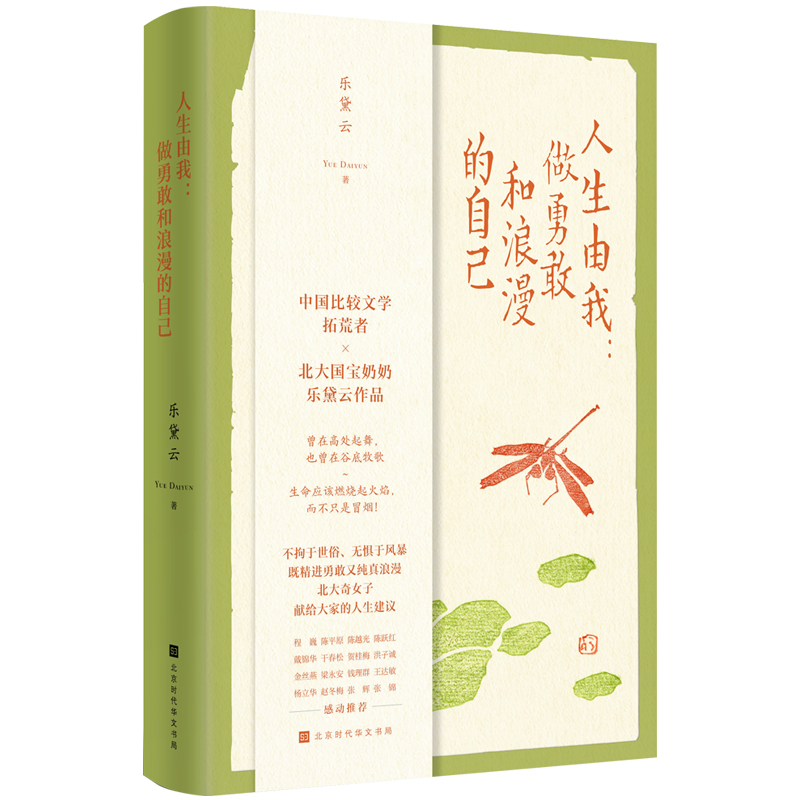
乐黛云 著名学者、作家、文学教授。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著有专著《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等,编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出版散文集《透过历史的烟尘》《绝色霜枫》等。

一、 汇集比较文学奠基人乐黛云经典散文作品,全面展现“北大国宝奶奶”的传奇人生! 她是文学史家、教育家王瑶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文章曾得沈从文的赏识;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钱理群的老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的妻子;她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她的经历值得一读! 二、“曾在高处起舞,也曾在谷底牧歌”,当最好的年华里遭遇磨难,看大器晚成的传奇学者如何笑对人生的坎坷曲折 她是一位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的北大国宝级教授,她是五十岁才真正“上路”,此后一路狂奔的比较文学奠基人,她是置身群贤之中而自成传奇的中外“跨文化之桥”的构筑者。阅读乐黛云,就是在阅读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亦是在阅读一种洒脱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不拘于世俗,无惧于风暴——北大奇女子献给女性的人生建议 魏晋女性的生活具有怎样的特点?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对现今有何启示?女性符号在中国文化中呈现哪些复杂的内涵?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叛逆与殉道精神具有怎样的意义?乐黛云观照历史、寄情文学、着眼现在,对两性相处之道和女性的自我建设提出建议,肯定女性自我价值,启发新时代女性生活态度。 四、风雨同舟数十载,未名湖畔“两只小鸟”的神仙爱情 他们自称是未名湖畔携手相伴数十载的“两只小鸟”,爱情佳话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们一个温和谦逊、儒雅内敛,是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大师;一个热情奔放、勇敢豪迈,是探索中外文化差异的文学教授。他们在革命的年代相知相遇,在动荡的年代不离不弃,在和平的年代相濡以沫。
书籍目录
辑一 梦开始的地方
父亲的浪漫
母亲的胆识
伯父的遗憾
我的初中国文老师
故乡的月
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我心中的山水
蜻蜓
小粉红花
辑二 北大,北大
初进北大
四院生活
快乐的沙滩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记北大鲤鱼洲分校
美丽的治贝子园
我们的书斋
忧伤的小径
从北大外出远游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辑三 何处佛光照影来
献给自由的精魂——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怀念马寅初校长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永恒的真诚——难忘废名先生
大江阔千里——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一个冷隽的人,一个热忱的人——纪念吾师王瑶先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忆女友
绝色霜枫——家麟
辑四 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
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
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叛逆、牺牲、殉道——现实和文学中的中国女性
情感之维
问世间“情”为何物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塑造我的人生的几本书
人生变奏
何时始终,何处来去
80岁感言
编后记
试读内容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女性这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中,也像在其他文化中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并且一向由男性定名、规范和解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绝代佳人,她们是男性所追求,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美丽之物”(尤物)。绝色美女总是和灾祸联系在一起。她们不仅是男人欲望的对象,也是男人失败的替罪羊。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皇帝如何沉迷于女色,导致国破家亡。然而男性所写的历史指责的却不是皇帝而是女人。
第二种是贤妻良母。中国是一个强调“百善孝为先”的国家,因此,抚育儿女的母亲具有很大的权威。母亲被描写为对子女的成材负有极大责任,因而也有极大的权威。在《红楼梦》中,当一家之长鞭责儿子时,偏袒孙子的祖母一出现,儿子就得跪下请罪。只是她们所维护的都是男性所制定的规范。《红楼梦》中的祖母在迫使叛逆的孙子就范时,与她的儿子并无二致。
第三种是侠女英雄。中国小说戏剧中有许多才华盖世、武艺高强的女英雄。她们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越男人并常拯救对方于困境。但在经历一番辉煌之后,都不得不重返男性为她们设定的旧轨,结婚生子,再也不过问“家庭”以外的事。
第四种是以死相拼的女英烈,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
中国传统文学的这四种不同的女性从不同层面揭露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剥夺和压抑。这样的文学只是“描写女性的文学”,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女性文学”。
中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女性浮出喑哑无语的世界,并寻找各种可能呈现自己。这种呈现自己的挣扎和奋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女性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定式,不再成为满足男性欲望和繁殖后代的工具,最切近的选择就是对夫权和父权的反叛,逃离家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鲁迅《伤逝》)然而,什么是“我自己”?“我自己”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并没有确定的内涵,甚至没有足以形成这种内涵的话语。逃离家庭的女性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女儿、妻子、母亲,那么,她们是什么呢?当时的“新女性”们只能从一个家庭浮现,又在另一个家庭沉没,回归于原来的角色。鲁迅的《伤逝》就深刻地描写了这种情形。
直到三十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大都市的发展为逃离家庭的新女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她们可以投身社会,逃脱寄生的命运。然而,她们仍然很难成就自己的事业,大部分也只能成为都市文化市场橱窗中的一只花瓶;女性如果不走这条路,就只有恋爱、结婚、建立家庭。然而,“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中心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一旦结婚,这种结构模式又变得坚不可摧。妻子无权参与丈夫的生活主流(“外”)。妻子为了防范丈夫有“外遇”,不得不用尽心机。二十年代初期曾经作为神圣的“拯救”偶像的“爱情”已经让位给背叛与反背叛,抛弃与反抛弃,出卖与反出卖的无休止的“两性之战”。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妇女已不再是色相商品,她们可以找到发挥她们专长的职业,“夫妻之战”也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主流,然而,两性生活中平庸、单调和由于太熟悉而互相厌倦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对于广大婚后女性来说,被人吞没的命运是那样不幸,坚守自我却又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样的两难处境仍然是许多女性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女性的自我,也就是如何取得女性的精神上的独立。中国文学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塑造了一大批浓眉大眼,“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男性化的女性人物,“男人能做的一切,女人同样能做”。这样的女性以放弃自己的女性特色为代价,在建设和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并非所有女性都愿意如此。如张辛欣所说:“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向前闯!不知不觉,我变成了这样。”(《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一种女性渴望把自己从男性中区别出来的热潮。这种对女性自我的认识,从性别经验的差异入手,从风格、结构、主题、文体以至文学史等各个方面,寻找出女性文本的特色,扩展为对整个女性文化的探索。这种研究对于消解男权中心社会,启发女性自觉,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对女性经验的分析正是以男性为参照系而得出的,始终在男女二元结构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很难超越阳刚阴柔之类的传统分野。如果只强调女性经验和女性特殊的心理,势必将女性局限于狭小的女性天地而放弃了与男性共处的广阔空间。总之,既反对女性的“男性化”,又不愿囿于女性的“女性化”,如何才能超越这一悖论,正是中国女性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女性和社会的关系。事实上,女性不可能生活在只有女性的环境,而是生活在男女共同组成的复杂社会之中。著名女作家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一文中,主张首先应该关注“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她问道:“当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起码的平等关系时,还有什么男人与女人的平等?”因此,首先应该写那些“使男人和女人感到共同苦恼”的,“迫切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张抗抗持相同观点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认为,女性文学在给女性自身以启迪的同时也必须给其他所有人以启迪,这就既要有女性内容和女性意识,又要超越女性内容和女性意识,否则女性文学只是“女性的文学”,而不可能成为其他一切人的文学。事实上,中国百年来社会斗争的胜利都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奋斗的结果。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涌现出了无数与男性并肩作战的女英雄,可惜从女性文学的视角对她们进行研究和反映都很不够。
总之,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社会转型时期。所谓转型就是观念的全面更新,一切曾经被认为是确定不移的道理和成规都要受到重新检验和评估,并决定取舍;这将是一个横向开拓,边缘与中心、上层与下层交叉发展,多元并存的时期。女性主义的突起正是这一文化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意义就在于对原有社会的不平等的两性结构进行彻底颠覆。几千年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结构体制统治了整个社会。这不仅大大压制了女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压抑了男性在很多方面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只有在男女平等互补的条件下才会变成现实。
这种颠覆并不是寻求一种倒转过来的“阴盛阳衰”的新模式,也不是以抹杀男性和女性特点为代价。事实上,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恰恰显示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途径和方式,也是人类丰富的精神能力在不同性别群体上的体现,它们原来就不是互相压制和抵消而是互相补充和相得益彰的。女性主义不应是以“摆脱”男性为最终标志,女性文学也不是以造就一个由女作家、女评论家和女读者群构成的“女性文学”网络,同男性相抗衡。未来的更合理的性别结构应是各自发挥特长,“男女共同主外,男女共同主内”。只有这样,男性和女性的聪明才智才能不受拘束地得到充分自由发挥。
面向二十一世纪,唯有男性和女性的相互谅解和通力合作才能面对人类共同遭遇的复杂局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并不一定要在与男性的对立中来发现“自我”,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需要对抗,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更多地合作,以形成一个不断进取、丰富而美好,也更富于魅力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