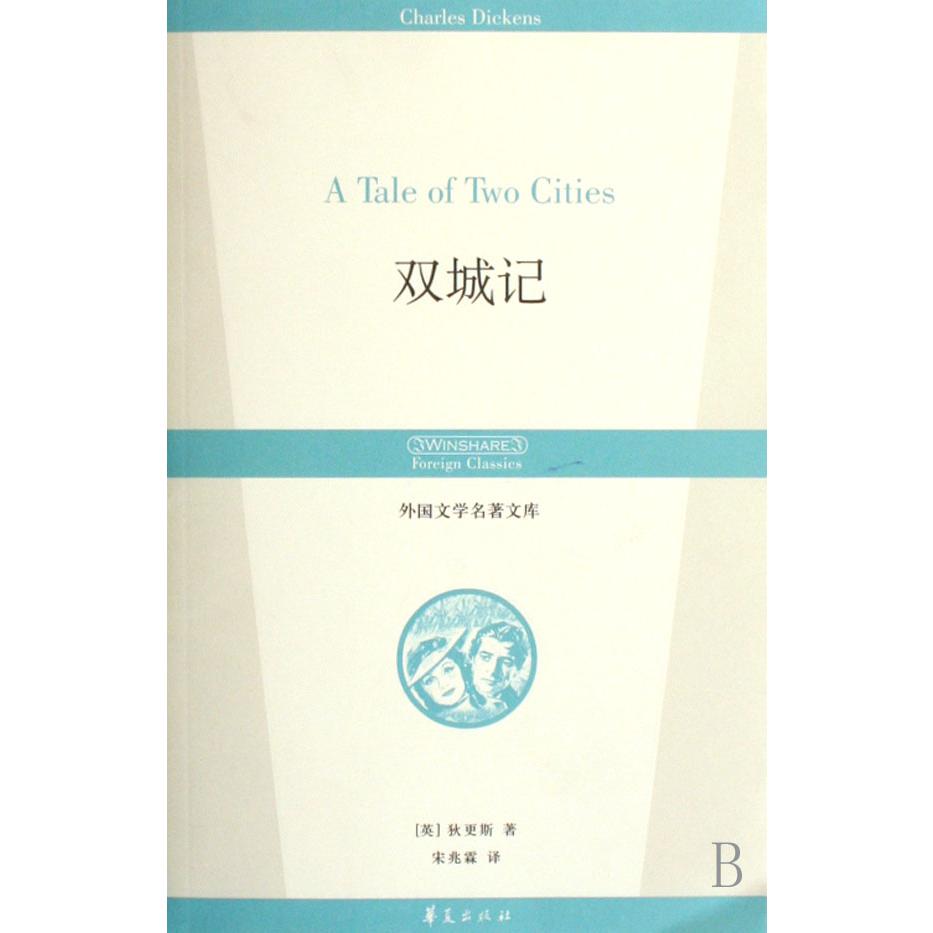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15.00
折扣价: 9.30
折扣购买: 双城记/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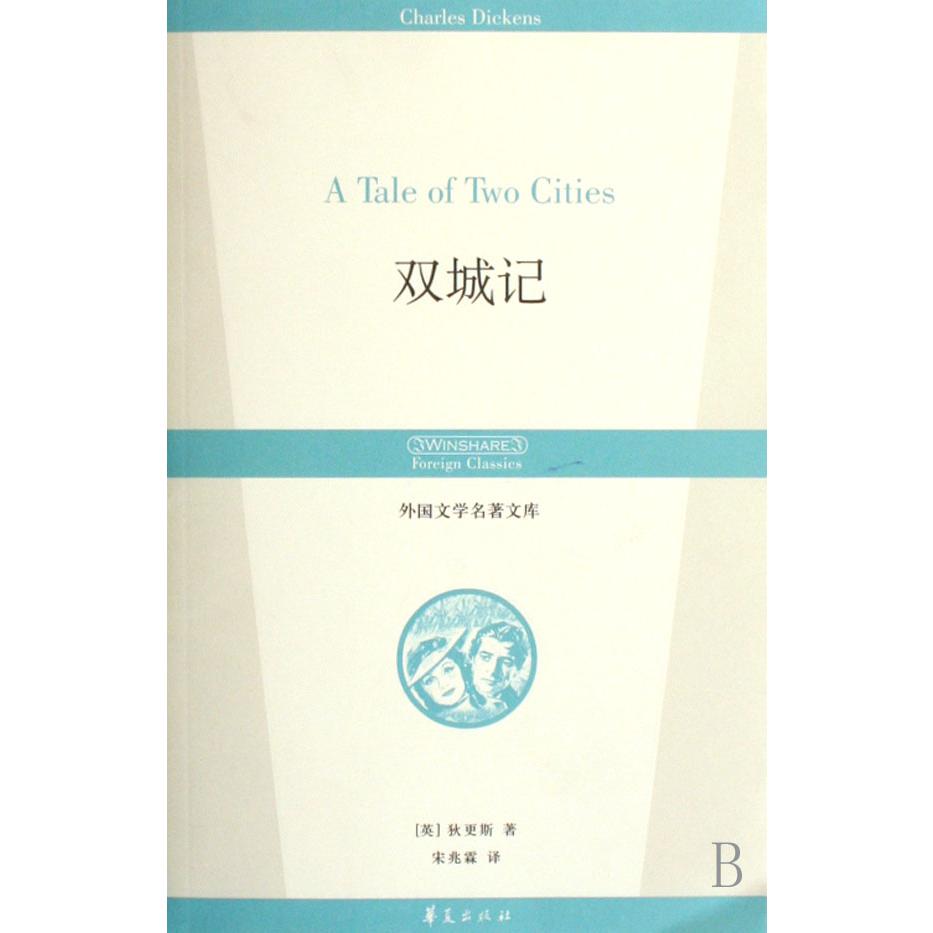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1812年生于英国的朴次茅斯。父亲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负债累累。年幼的狄更斯被迫被送进一家皮鞋油店当学徒,饱尝了艰辛。狄更斯16岁时,父亲因债务被关进监狱。从此,他们的生活更为悲惨。工业革命一方面带来了19世纪前期英国大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庶民社会的极端贫困和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使狄更斯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15岁时,狄更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并学习速记,此后,又在报社任新闻记者。在《记事晨报》任记者时,狄更斯开始发表一些具有讽刺和幽默内容的短剧,主要反映伦敦的生活,逐渐有了名气。他了解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这些都体现在他热情洋溢的笔端。此后,他在不同的杂志社任编辑、主编和发行人,其间发表了几十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雾都孤儿》、《圣诞颂歌》、《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 狄更斯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相关联的事件。他在书中揭露了济贫院骇人听闻的生活制度,揭开了英国社会底层的可怕秘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本书起笔便描写了主人公奥利弗生下来便成为孤儿,以及在济贫院度过的悲惨生活。后来,他被迫到殡仪馆做学徒,又因不堪忍受虐待而离家出走。孤身一人来到伦敦后,又落入了窃贼的手中。狄更斯在其作品中大量描写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平民阶层寄予了深切的向情,并无情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他在小说描写的现实性和人物的个性化方面成绩是突出的。他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塑造作品人物数量最多的一个作家。
第三章 夜影 细想起来,这事实在奥妙,任何一个人,对别的人来说,都是深不可 测的奥秘和难解之谜。每当我在夜间进入一座大城市时,就会有一种一本 正经的想法,那些黑压压的鳞次栉比的房子里,都藏着各自的秘密。每幢 房子的每间屋子里,也都藏着它自己的秘密,而各间屋子里无数胸膛中跳 动着的每一颗心,就它自己的某些心绪来说,即使对最亲近的另一颗心, 也是一桩秘密!有些可怖的事情,甚至于死亡,就起因于此。我再也不能翻 阅我所钟情的这本可爱的书了,即使我希望能及时读完它也是枉然。我再 也不能凝望那深不可测的水流深处了,在光线射人的瞬间,我曾瞥见深埋 其中的珍宝以及其他沉入其中的东西。这本书注定了在我仅仅读完一页后 便会砰然合上,永不再开。当阳光在水面上嬉戏,而我茫然地站在岸边的 时候,这水注定了要被永恒的坚冰封死其中。我的朋友去世了,我的邻居 去世了,我的爱人、我的情之所钟也去世了。那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秘密, 也就被永远牢牢地封存了,而我也将把我心中的秘密一直带进我的坟墓。 在我走过的这个城市的任何墓地里,在我看来,有哪位长眠者内心深处的 奥秘,比那些忙忙碌碌的居民更加神秘莫测?而在那些居民看来,又有哪位 长眠者比我更神秘莫测呢? 说到这,我们那位骑在马背上的信差,也和国王、首相,或者伦敦的 富商巨贾一样,同样拥有这种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遗产。挤在那辆笨重 缓慢的旧邮车狭窄车厢里的三位乘客,也是如此。他们互为不解之谜,就 像各自坐在自己六匹马或六十匹马拉的马车里,彼此相距有一郡之遥,相 互全不了解。 信差放松辔头,让马儿缓步往回走,还不时停下来在路边的小酒店里 喝上一杯,可是一直做出讳莫如深的样子,还将帽子低压在眉间。那顶帽 子和他的眼睛十分相称,眼睛的表面黑溜溜的,但颜色和形状都很浅薄, 而且也靠得太近了——仿佛生怕隔得太远,就会被人单个逮住,查出干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眼睛上面低扣着一顶三角痰盂似的旧三角帽, 下面是一条裹住下巴和脖子、几乎拖到膝盖的大围巾,使得藏在中间的眼 睛显得格外凶恶阴险。他停下来喝酒时,就用左手撩起围巾,右手端起酒 杯,一饮而尽,随后便立即将围巾重新裹紧。 “不成,杰里,不成!”信差骑在马上,一路唠叨着,“这对你不利, 杰里。杰里,你是个本分的生意人,这对你的行当可不利啊!复活——!他 要不是喝醉了,那才怪哩!” 他捎的那个口信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三番五次摘下帽子来直搔头皮 。除了顶上一块秃得高低不平外,他的头上长满又硬又黑的头发,向上竖 着的参差不齐,向下挂着的几乎垂到又肥又大的鼻子。他的头发就像是铁 匠做的活儿,根本不像一头头发,更像是牢牢钉在墙顶的铁蒺藜,就连跳 背游戏的能手,也会望而却步,把他看成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不敢从他身 上跳过。 信差加鞭催马往回赶路,要把这口信捎给圣堂栅栏旁台尔森银行门房 里的值夜人,再由他传给里面更有权的管事人。由于这口信,他只觉得黑 夜里幻影幢幢,那母马,由于它自己的不自在,眼前也出现了种种幻影。 一路上,幻影似乎还不少,每碰上一个,它就惊得向后一退。 这时候,邮车正载着那三个彼此莫测高深的同伴,摇摇晃晃、颠颠簸 簸、吱吱嘎嘎、跌跌撞撞地行进在单调乏味的旅途上。三位旅客睡眼惺忪 ,神思恍惚,眼前也出现了种种夜问的幻影。 邮车里,浮现出台尔森银行的一片繁忙景象。那位在银行工作的旅客 ——他一只胳膊套在皮圈里,以免在马车颠簸得特别厉害时和旁边的乘客 相撞,因而被挤到角落里去——正半闭着眼在座位上打盹。那些小小的车 窗,从车窗照进来的昏暗的车灯灯光,还有对座乘客臃肿的身形,全都变 成了银行,而且正在做一笔大生意。挽具的咯嗒声变成了钱币的丁当声, 五分钟内承兑的票据,甚至比台尔森银行及其国内外全部分行在三倍时间 内承兑的还要多。接着,他眼前又出现了台尔森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他知 道,里面藏有那么多贵重的宝物和机密(对此他颇为了解),他带着一串大 钥匙,手持一支光焰微弱的蜡烛,一间间走过去,只见样样东西都像他上 次看到的一样,安然无恙,稳稳妥妥,原封未动。 可是,虽说他眼前几乎一直浮现出那银行的情景,虽说他始终坐在邮 车里(晕晕乎乎,像服了麻醉剂一样),却还有另外一种思绪整夜缠绕着他 。他正要前去把一个人从坟墓中挖出来。 在他眼前浮现出来的众多面孔中,到底哪一张是那个被埋的人的真面 目,他无法从那些夜间的幻影中认出。不过,他们全是一个年纪四十五岁 左右的男人的面孔,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表情以及憔悴枯槁的程度。骄 傲、轻蔑、反抗、倔强、驯顺、悲伤,一种表情接着一种表情,还有各种 各样下陷的面颊,死灰般的脸色,枯瘦的双手和手指。不过脸庞大体上还 是同一个,头发也总是个个都未老先衰地白了。打着盹的旅客对这个幽灵 问了上百次: “埋了多久了?” 回答总是一样:“快十八年了。” “你已经完全放弃被人挖出的希望了吗?” “早就放弃了。” “你知道要让你复活吗?” “人家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想你是想活的吧?” “我说不上。” “要我带她来见你吗?你愿意见她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有时灰心丧气地回 答:“等一等!要是马上见到她,会要了我的命的。”有时又满怀柔情、泪 如雨下地说:“带我去见她吧!”有时则瞪着眼,迷惑不解地说:“我不认 识她。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在想象中作了这么一番交谈之后,这位旅客又在幻觉中使劲地挖呀, 挖呀,挖呀——一会儿用一把铁锹,一会儿用一把大钥匙,一会儿用自己 的双手——要把这个可怜的人挖出来。终于挖出来了,脸上、头发上都沾 着泥土,接着,突然倒地化成尘土。旅客一惊醒来,放下车窗,让现实中 的雨和雾打在自己的脸上。 可是,就在他睁眼出神地凝望着雨雾,凝望着车灯游移的光斑以及那 一颠一跳向后退去的路边树篱时,车外的幢幢夜影和车内的串串幻影,又 渐渐混成一片了。圣堂栅栏旁那家真的银行,往日里那些真的买卖,那些 真的保险库房,那封专差给他送来的真的快信,那捎回去的真的口信,全 都一一在眼前隐现。那张幽灵般的面孔,再次在其中显现,于是他又跟他 攀谈起来: “埋了多久了?” “快十八年了。” “我想你是想活的吧?” “我说不上。” 挖——挖——挖,一直挖到两个旅客中有一个不耐烦地用动作示意, 要他拉上车窗。他把胳膊牢牢地套在皮圈里,面对着那两个昏睡的人形揣 摩起这两个人来。但不久,他又神志恍惚地抛开了他们,重又溜进那家银 行和那座坟墓了。 “埋了多久了?” “快十八年了。” “你已经完全放弃被人挖出的希望了吗?” “早就放弃了。” 疲惫不堪的旅客一觉醒来,只见天已大亮,深夜的幢幢幻影早已不知 去向,可是,这些话就像刚说过一样,话音仍在他耳边萦绕——像他在现 实生活中听到过的一样,清清楚楚地留在耳边。 他拉下车窗,望着窗外刚刚升起的朝阳。车外是一片刚犁过的土地, 地头还留着从马身上卸下的犁铧。再远处,是一片幽静的矮树林,林中还 有许多火红和金黄的叶子挂在枝头。大地虽然寒冷潮湿,天空却一片晴朗 ,太阳正冉冉升起,灿烂、宁静而又美丽。 “十八年!”旅客望着太阳说道,“慈悲的造物主啊!被整整活埋了十 八年啊!” P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