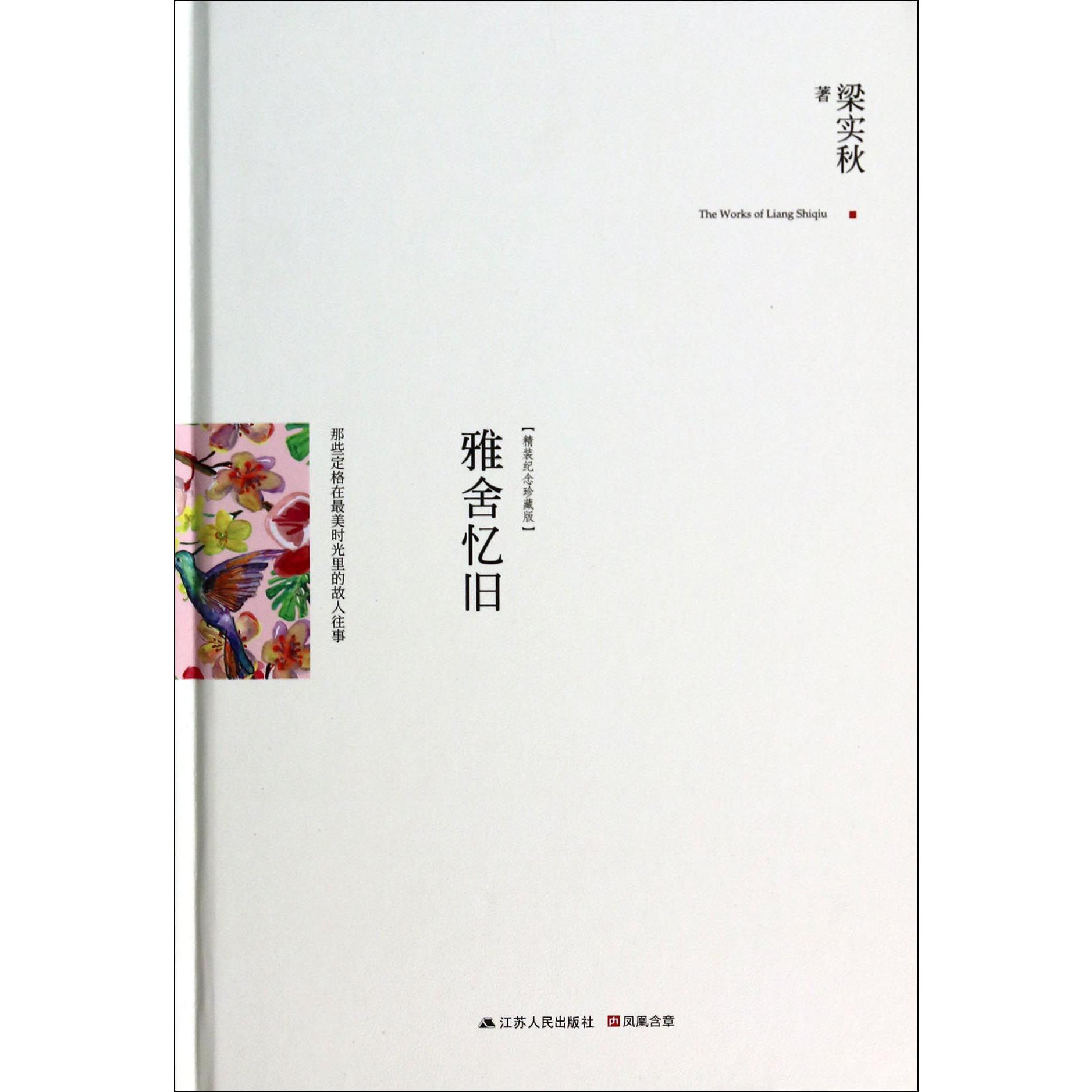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人民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雅舍忆旧(精装纪念珍藏版)(精)
ISBN: 9787214121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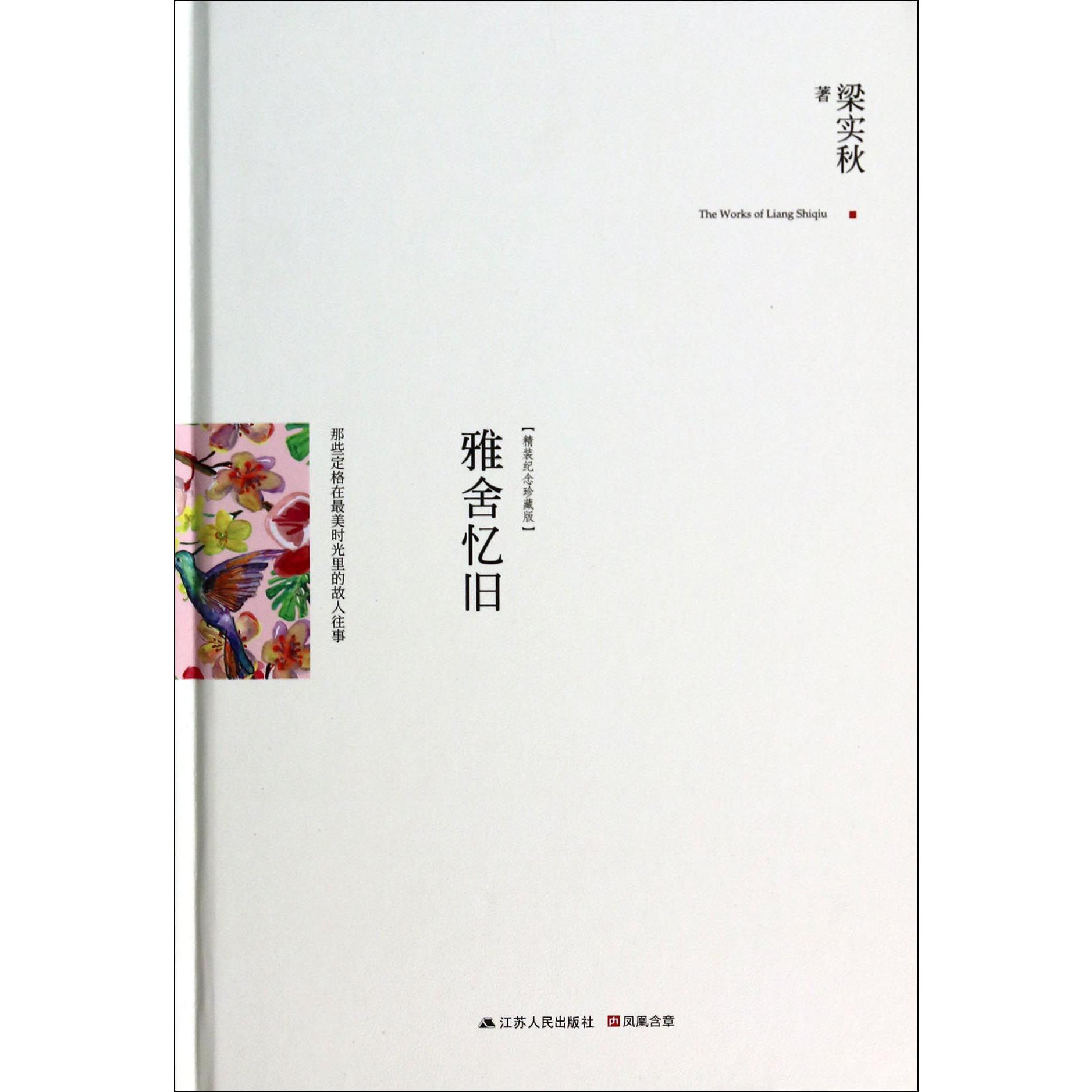
梁实秋(1903—1987), 1903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县(今杭州)。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译作《莎士比亚全集》,文艺批评专著《浪漫的与古典的》,等等。 其散文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时而流连于衣食住行,时而沉醉于琴棋书画,有时天文地理,有时人情世故。没有生之无聊死之激烈的大悲大喜,而是在简洁的文字中透出高雅、平和,以及一种积极温暖的情味。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是孟郊的句子,人 与疲马羁禽无异,高飞远走,疲于津梁,不免怀念自 己的旧家园。 我的老家在北平,是距今一百几十年前由我祖父 所置的一所房子。坐落在东城相当热闹的地区,出胡 同东口往北是东四牌楼,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东 四牌楼是四条大街的交叉口,所以商店林立,市容要 比西城的西四牌楼繁盛得多。牌楼根儿底下靠右边有 一家干果子铺,是我家投资开设的,领东的掌柜的姓 任,山西人,父亲常在晚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溜达着 到那里小憩。掌柜的经常飨我们以汽水,用玻璃球做 塞子的那种小瓶汽水,仰着脖子对着瓶口汩汩而饮之 ,还有从蜜饯缸里抓出来的蜜饯桃脯的一条条的皮子 ,当时我认为那是一大享受。南小街子可是又脏又臭 又泥泞的一条路,我小时候每天必须走一段南小街去 上学,时常在羊肉床子看宰羊,在切面铺买“干蹦儿 ”或糖火烧吃。胡同东口外斜对面就是灯市口,是较 宽敞的一条街,在那里有当时唯一可以买到英文教科 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以后又添 了一家郭纪云,路南还有一家小有名气的专卖卤虾、 小菜、臭豆腐的店。往南走约十五分钟进金鱼胡同便 是东安市场了。 我的家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地基比街道高得 多,门前有四层石台阶,情形很突出,人称“高台阶 ”。原来门前还有左右分列的上马石凳,因妨碍交通 而拆除了。门不大,黑漆红心,浮刻黑字“忠厚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门框旁边木牌刻着“积善堂梁” 四个字,那时人家常有堂号,例如三槐堂卫、百忍堂 张等,积善堂梁出自何典我不知道。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语见《易经》,总是勉人为善的好话,作为我们 的堂号亦颇不恶。打开大门,里面是一间门洞,左右 分列两条懒凳,从前大门在白昼是永远敞着的,谁都 可以进来歇歇腿。一九一一年兵变之后才把大门关上 。进了大门迎面是两块金砖镂刻的“戬谷”两个大字 ,戬谷一语出自《诗经》“俾尔戬谷”。戬是福,谷 是禄,取其吉祥之义。前面放着一大缸水葱(正名为 莞,音冠),除了水冷成冰的时候总是绿油油的,长 得非常旺盛。 向左转进四扇屏门,是前院。坐北朝南三问正房 ,中间一间辟为过厅,左右两间一为书房一为佛堂。 辛亥革命前两年,我的祖父去世,佛堂取消,因为我 父亲一向不喜求神拜佛,这间房子成了我的卧室。那 间书房属于我的父亲,他镇日价在里面摩挲他的那些 有关金石小学的书籍。前院的南边是临街的一排房, 作为用人的居室。前院的西边又是四扇屏门,里面是 西跨院,两间北房由塾师居住,两间南房堆置书籍, 后来改成了我的书房。小跨院种了四棵紫丁香,高逾 墙外,春暖花开时满院芬芳。 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迎面是一个垂花 门,门旁有四大盆石榴树,花开似火,结实大而且多 ,院里又有几棵梨树,后来砍伐改种四棵西府海棠。 院子东头是厨房,绕过去一个月亮门通往东院,有一 棵高庄柿子树,一棵黑枣树,年年收获累累,此外还 有紫荆、榆叶梅,等等。我记得这个东院主要用途是 摇煤球,年年秋后就要张罗摇煤球,要敷一冬天的使 用。煤黑子把煤渣与黄土和在一起,加水,和成稀泥 ,平铺在地面,用铲子剁成小方粒,放在大簸箩里像 滚元宵似的滚成圆球,然后摊在地上晒,这份手艺真 不简单,我儿时常在一旁参观,十分欣赏。如遇天雨 ,还要急速动员抢救,否则化为一汪黑水全被冲走了 。在那厨房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厨师嫌我们碍手碍脚 ,拉面的时候总是塞给我一团面叫我走得远远的,我 就玩那一团面,直玩到那团面像是一颗煤球为止。 进了垂花门便是内院,院当中是一个大鱼缸,一 度养着金鱼,缸中还矗立着一座小型假山,山上有桥 梁房舍之类,后来不知怎么水也涸了,假山也不见了 ,干脆作为堆置煤灰煤渣之处,一个鱼缸也有它的沧 桑!东西厢房到夏天晒得厉害,虽有前廊也无济于事 ,幸有宽幅一丈以上的帐篷三块每天及时支起,略可 遮抗骄阳。祖父逝后,内院建筑了固定的铅铁棚,棚 中心设置了两扇活动的天窗,至是“天棚鱼缸石榴树 ……”乃粗具规模。民元之际,家里的环境突然维新 ,一日之内小辫子剪掉了好几根,而且装上了庞然巨 物钉在墙上的“德律风”,号码是六八六。照明的工 具原来都是油灯、猪蜡,只有我父亲看书时才能点白 光炎炎的僧帽牌的洋蜡,煤油灯认为危险,一向抵制 不用,至是里里外外装上了电灯,大放光明。还有两 架电扇,西门子制造的,经常不准孩子们走近五尺距 离以内,生怕削断了我们的手指。 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两间。祖父在的时 候,他坐在炕上,隔着玻璃窗子外望,我们在院里跑 都不敢跑。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听见胡同里有“打糖 锣儿的”的声音,一时忘形,蜂拥而出,祖父大吼: “跑什么?留神门牙!”打糖锣儿的乃是卖糖果的小 贩,除了糖果之外兼卖廉价玩具、泥捏的小人、蜡烛 台、小风筝、摔炮,花样很多,我母亲一律称之为“ 土筐货”。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祖父还坐在那里 ,唤我们进去。上房是我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 且是一经呼唤便非进去不可的。我们战战兢兢地鱼贯 而入,他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着什么?”我说:“ 糖。”“什么糖?”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支 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取名为 狗屎橛;这白的为猫屎橛。”实则那黑的是杏干做的 ,白的是柿霜糖,祖父笑着接过去,一支咬一口尝尝 ,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次买的时候也 给他买两支。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锣儿一响, 一拥而出,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 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搭腔:“我吃猫屎橛! ”这是我所记得的与祖父建立密切关系的开始。 父母带着我们孩子住西厢房,我同胞一共十一个 ,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姊妹兄弟四个孩子睡一 个大炕,好热闹,尤其是到了冬天,白天玩不够,夜 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还是吱吱喳喳笑语不休。母 亲走过来巡视,把每个孩子脖颈子后面的棉被塞紧, 使不透风,我感觉异常的舒适温暖,便怡然入睡了。 我活到如今,夜晚睡时脖颈子后面透凉气,便想到母 亲当年那一份爱抚的可贵。母亲打发我们睡后还有她 的工作,她需要去伺候公婆的茶水点心,直到午夜; 她要黎明即起,张罗我们梳洗,她很少睡觉的时间, 可是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情形又周而复始 ,于是女性惨矣!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