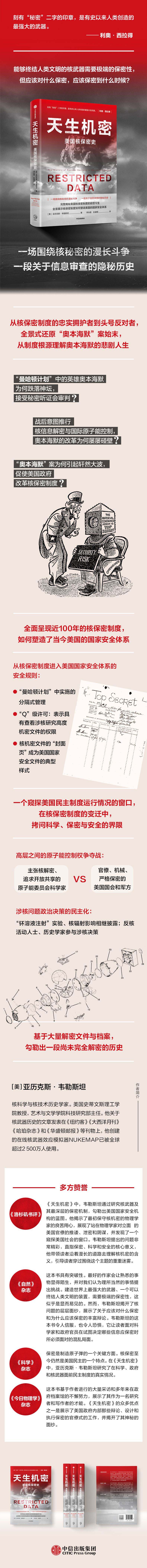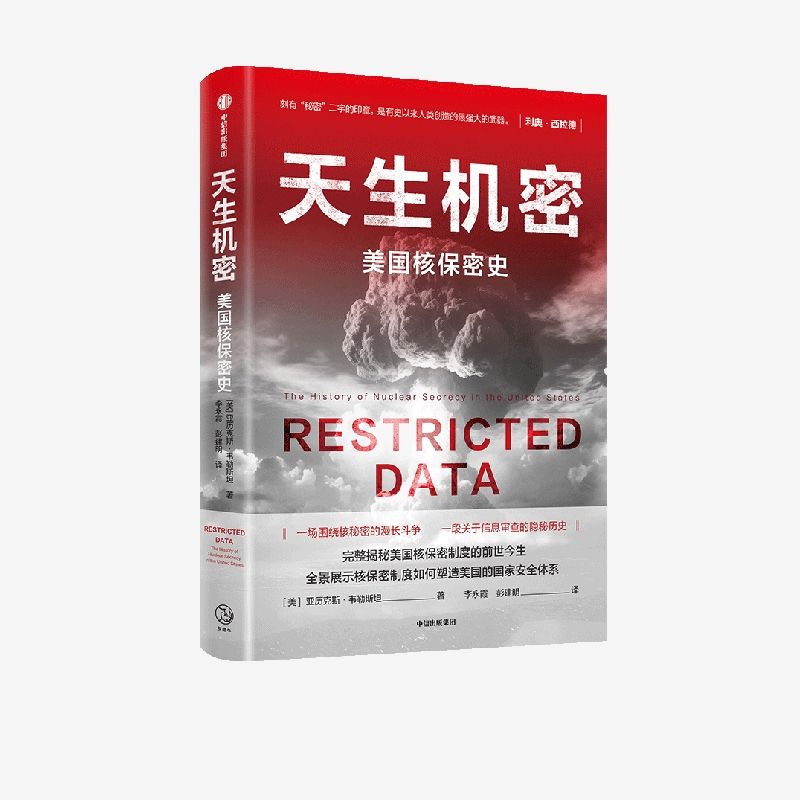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9.90
折扣购买: 天生机密
ISBN: 9787521758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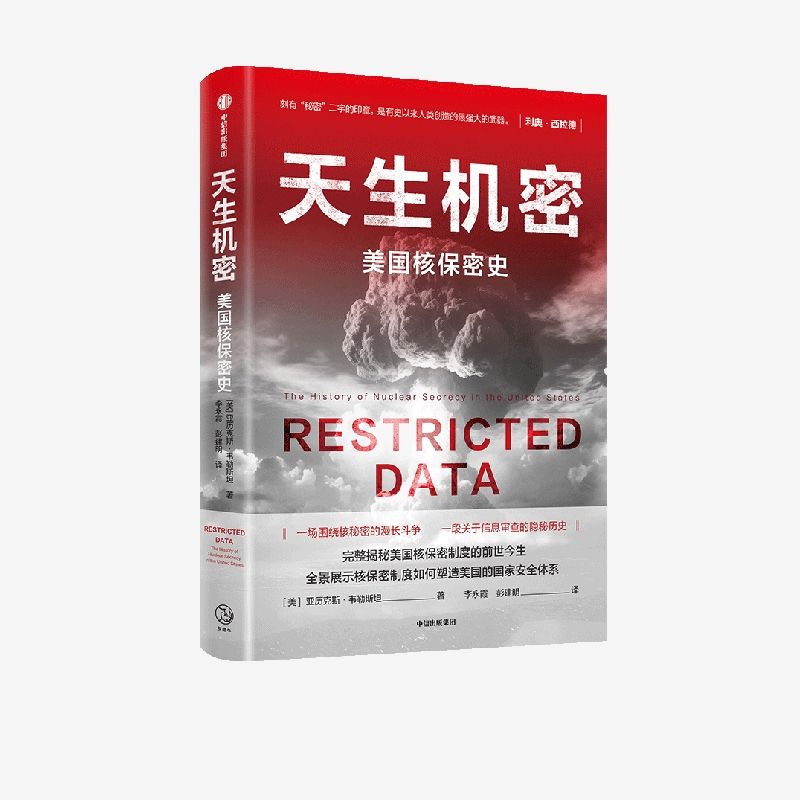
亚历克斯·韦勒斯坦,核科学与核技术历史学家。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教授,艺术与文学学院科技研究部主任。他关于核武器历史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客》《大西洋杂志》《哈珀杂志》和《华盛顿邮报》等刊物上,他创建的在线核武器效应模拟器NUKEMAP已被全球超过2500万人使用。
1945年8月6日上午,白官发布了一份足以改变世界的新闻稿。以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伟大科学项目存在的事实及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公之于世: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武器摧毁了日本广岛。新闻稿中称:“这枚原子弹体现人类驾驭了宇宙的基本力量。”而在此之前,从美国制造核武器的初衷,到真正着手制造、测试并部署核武器的过程,一直都是最高机密。原则上讲,泄密者可能会被处以死刑。 核武器一直是核心机密,美国原子弹也是秘密问世的。从科学家开始研究其可能性的那一刻起到大规模研发的过程,美国一直在极力阻止相关信息传播,所有新的研究成果都在掌控之中。这种控制欲源于恐惧。对于第一批研究美国原子弹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所惧怕的是可怕的敌人,即纳粹德国,会利用这些信息制造核武器。后来,这种恐惧转变为担忧,官员们担心过早将这种新型武器公之于众会削弱其对日本人的震慑作用,并对项目本身的成功造成潜在威胁。虽然这种保密工作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之下的各种忧惧,但此后的形势演变造成了新的恐惧,保密工作也在因时而变,因为新的敌人不断出现。不管是一些小麻烦,如外交困局,还是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如全球热核战争,都让美国感到恐惧,正是这种分散的、多样化的恐惧激起了美国的控制欲。 然而从一开始,各方对核保密的立场就是互相矛盾的。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已习惯于执行保密制度,时时保持警惕。有些人出于恐惧心理,支持完全保密;有些人觉得,即使曾经有必要保密,但一直保密会令人感到窒息。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人们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与忧思。 原子弹是科学和工业结合的产物,但其基本原理在战争爆发前就已为科学家所知悉。如果任何国家、任何实验室的任何科学家都能成功复制或发现某个现象,它怎么能实质性地变成国家机密呢?一名士兵构思出的军事计划能无限期地保密,但是物理、化学学科中可验证的原理可以吗? 许多科学家和决策者进一步质疑是否应该对科学研究保密,以及这样做是否会对安全产生反作用。原子弹不仅是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也是几十年来科学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和全球合作的结果。许多在保密制度下工作的科学家认为,该制度遏制了科学的发展。如果让保密成为一种规范,科学还会繁荣发展吗?甚至科学还能存续吗?到底怎样做才对国家安全更有好处,是保守秘密,还是尽可能快速、公开地推进科学研究? 核科学造就了核武器,也带来了廉价、丰富的清洁能源,以及其他造福大众的用途。人们对原子能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恐惧,是否会压倒以核科技造福民生的希望?保密,一直是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未来应该长期如此吗?白宫在核爆广岛的新闻稿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上述几个问题,并故意不予回答。新闻稿中还特别指出,“向全世界隐瞒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是美国科学家的习惯,也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相关工作的信息都会被公布。但是二战刚刚结束,动荡的国际局势要求对原子弹的制造技术继续保密,至少在短期内应当如此。白宫在新闻稿中解释说,为了保护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免受“突然毁灭的威胁”,将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审慎的研究”。 与原子弹相关的全面科学保密工作是全新且非同寻常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信奉科学和民主的美国而言,核保密是一个陌生事物,它与上述两者的兼容性备受争议。但催生了原子弹的国际局势,以及原子弹本身,似乎都在要求延长保密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风险。这种核保密状态“不断演进且丝毫未见松懈”,并延续至今。 暮然回首,二战结束距今已70多年,苏联解体距今已30多年,核武器、核保密和核恐惧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若非如此,世界又会怎样?这一切让人细思极恐。 本书讲述了美国的核保密制度的历史,时间跨度从原子弹最初被认为具有实现可能性的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上半叶的今天。本书记录的故事涉及一群身份各异的人——科学家、管理者、军人、政治家、律师、法官、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大众。他们都深受同一个问题的困扰:核信息是否应当被视为需要管控的对象,以及有多少经过讨论的结果、精心实施的政策和干预,塑造了美国延续至今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本书中,这一反复出现的新奇主题令人感到紧张。原子弹可能是在保密中诞生的,但这种保密的正当性一直备受争议。 人们对科学与保密之间关系的关注,常常伴随着对民主与保密之间关系的担忧。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将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启蒙思想奉为圭臬。这些理想虽从未被视为绝对法则,但它们又事实上具备法律、政治和话语力量。\"这意味着虽然二战后美国支持核保密的一方势力兴盛,但其影响力也并非无限扩张,即使是在全球核武器不断发展,核威胁愈演愈烈,几乎已经造成人类生存风险的情况下。 同时,核政策和保密制度改革一直与民主愿景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研发核武器及创立保密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政客阻碍推行公众审议的举动称为“对原子的严厉抑制”,这对于了解核秘密的人来说既是奖赏,也是负担。?许多赞同奥本海默的人认为,这种保密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基础,让美国公众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和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这很危险。 在上述这些充满张力的对立关系中,既有保持科学理想与坚守核保密之间的对立,也有要求核信息公开与严守核安全性之间的对立,正是这些对立关系使美国的核保密演进历程变得不可预测、令人惊讶,有时甚至是怪异的。这里给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第三章中将详细讨论):美国可能是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公布原子弹技术发展史的国家,公布时间仅在第一次使用原子弹后的几天。这样做既是为了提升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话语权,也是为了进一步保护机密。以简明而直白的语言,将之前用暗语和严格限制知情人员等方式重重保密的“曼哈顿计划”用一份文件公布出来,这本身就很奇怪,此后没有其他国家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该项目的最高科学、军事和政治代表都认可该文件的实际效力,并在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长崎的几天后就亲自游说总统将其公之于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子,说明保密和解密不仅是相匹配的,亦可服务于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机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