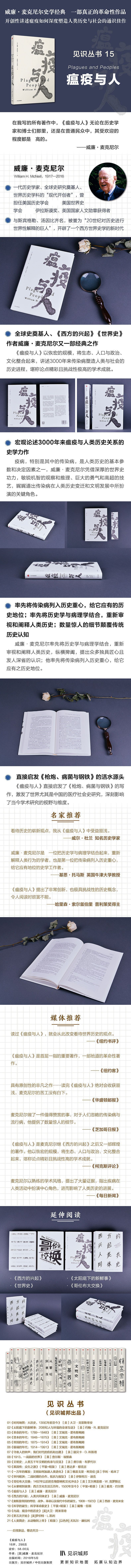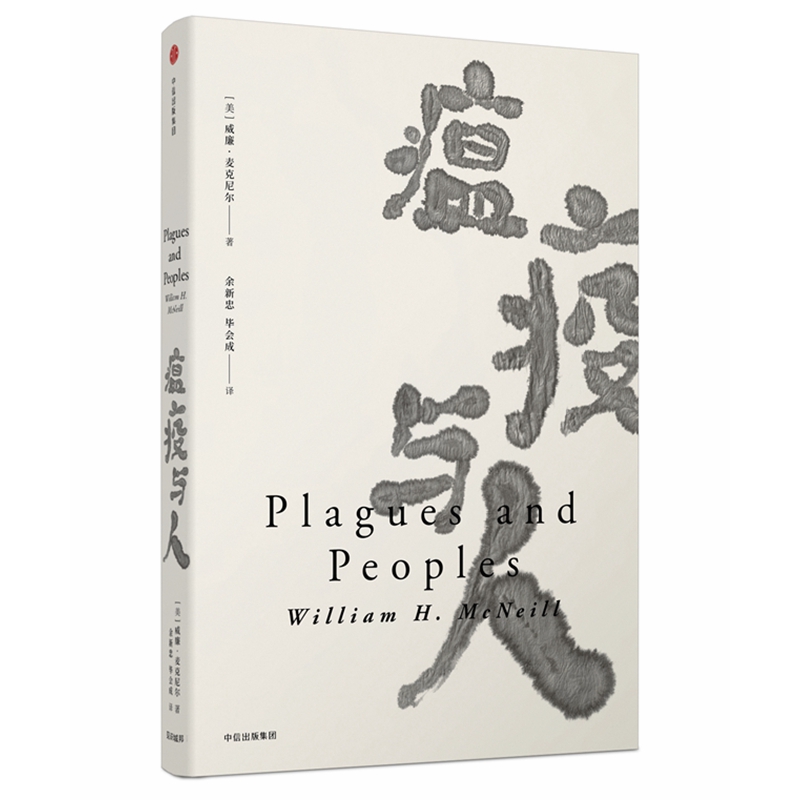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9.50
折扣购买: 瘟疫与人(精)
ISBN: 9787508677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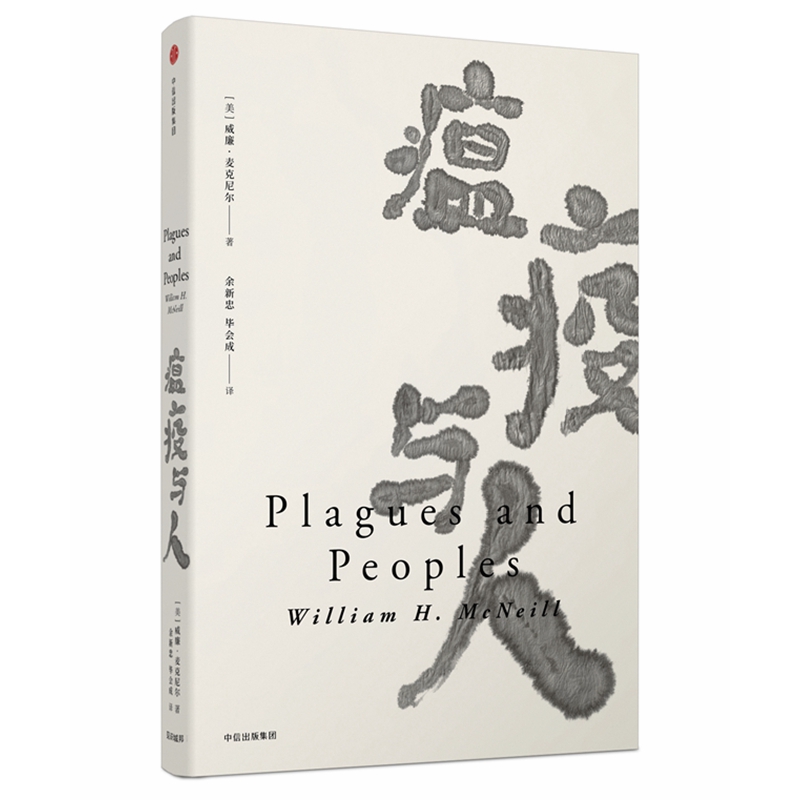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一代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止,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因其“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其他主要作品有《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与其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追寻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在远东,自公元前 600 年起,耕作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农业活动突破了早期仅限于半干燥的 黄土地区的地理边界,并且把主产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把巨大 的冲积平原改造成星罗棋布的稻田,意味着每片稻田都配备有可调节的水道,需要大量劳动力来进行筑堤、排水、修造运河以及开垦沼泽地等农务。此外,为了防范河水泛滥,整个农作区还必须修造全面而复杂的水利工程体系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黄河。 黄河在地理意义上是世界最为活跃的大河。在较近的地质年代, 它合并了来自其他排水系统的重要支流,在流经中游的黄土地区时, 侵蚀了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当挟带淤泥的河水流经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时,流速减慢,上游大量的侵蚀物便沉积下来。结 果,泥沙很快在冲积平原上抬高了它的河床。而当人们开始用人工堤坝限制水流时,麻烦出现了,堤坝只能逐年加高,以应付河流底部的沉积导致的河床升高,“ 悬河”由此形成了。为把河流局限在堤坝内,需要大量人力;堤坝中渗出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时补救, 都可能迅速扩大而成为激流;或许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在堤坝中撕开裂口,而一旦出现大的裂口,整条河流就会溢出人工河道,奔向新 的更低的河道。这条大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于山东高地以北(像目前这样)或以南,幅员达数百英里。 黄河地理上的不稳定性,虽因人类的活动而加剧,但总体上非 人为所致,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稳定的调整仍需经历地质时间长度。 而另外一个影响早期中国生态平衡的因素,则主要是人类的活动。 比如,在政治层面上,因稻田耕作而扩大了的食物来源支持了几个世纪的王侯战争,直到公元前 221 年,一个征服者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邻地区。稍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一个新的 王朝—汉朝,在公元前 202 年取得了主宰地位,并且至少在名义上统治中国直到公元 221 年。 由帝国官僚机器所维持的国内和平,可能降低了此前长期战 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然而汉代的和平也意味着建立在农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类双重寄生关系的强化。从同一农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征税的皇室官僚无疑处在竞争之中,尽管他们相当有效地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机制。他们的利益从根本来讲是一致的, 因为帝国官僚成员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从拥有土地的食利阶层中遴选出来的。 然而,在古代中国开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着另一个强 有力的因素。随着中国地主对农民控制的加深,一套别具特色的行为观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阶层中扎下根来。这套观念通常被称为儒学(Confucian,直译为“ 孔家学说”),“ 孔圣人”(公元前 551—前 47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阐述和界定这一新观念。儒家文化在帝国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传播,造就了不断限制权力专制或滥用的精英阶层, 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将对农民的压榨控制在传统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内。 到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 农民和两大寄生阶级之间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其中不乏周期性的变动,但并没有结构上的断裂。总的来说,地主和税务官征收的税收尽管繁重,但还没有过度 到使得中国农民难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则,中国人口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邻近地区,就不会进行缓慢却极其壮观的扩张,乃至向南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农民也不会为建立其上的传统文化和帝国结构提供不断强固的基础—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问题。 现有的文献还不足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扩张的脉络。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 从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 1000 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 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现实优势,一种既不见于史料也不见于人的肉眼,但我们仍然相信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却隐然阻碍着文明的 农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拓 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 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 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 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 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 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 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 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 灌溉农业时,他们肯定也经受了全新的、起初或许还很可怕的罹病 考验。但是与这一变化相联系的任何微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都与更 显著的和更耗时的技术层面和巨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齐头并进。要发 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需要几个世纪的 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也同等重要和 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 上的更显著的转型同步。 很难在两个平行的过程中明确区分哪个过程更为关键。但巨寄 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因为,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公元 前 403 年—前 221 年)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到古代中国的巨型寄生平衡达到新的帝国规模的汉朝(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1 年),中国农民已有 400 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远在巨型寄生关系稳定之前的几代甚 至几个世纪就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 时,这种转变肯定会产生显著的后果。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 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 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事实上,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和道德基础与有关的工程技术一起,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期被建立起来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 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而中国移民只是在 5~6 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 言之,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 地发展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正如中东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145—前 87 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 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 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 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 但作用无疑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现代疾病的分布,仅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经典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 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传染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en,古希腊名医) 的用词翻译成 20 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18] 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 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也表明了它在中国人的早期扩张中意义重大。[19] 中国 19 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血吸虫病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另一重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 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 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21] 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 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 600 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 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 200 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 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 211 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盖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 亡(211 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马上要谈到的,当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着剧烈而意义深远的疾病调适。 ★ 全球史奠基人、《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又一部经典之作;它以恢宏的规模,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堪称论点精彩且挑战性极高的学术成就。 ★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力作,匠心独运,颇为可读。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凭借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威廉?麦克尼尔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提出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他率先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之历史地位;他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细节,论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常见的关键角色。 ★《瘟疫与人》一书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瘟疫与人》是“见识丛书”系列第15册,“见识丛书”系列装帧设计别具一格,封面用纸采用国际FSC环保认证的特种凯斯棉,内文纸为72克月白纯质,精装圆脊,再加上内封独特的压纹工艺,为读者呈现不一样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