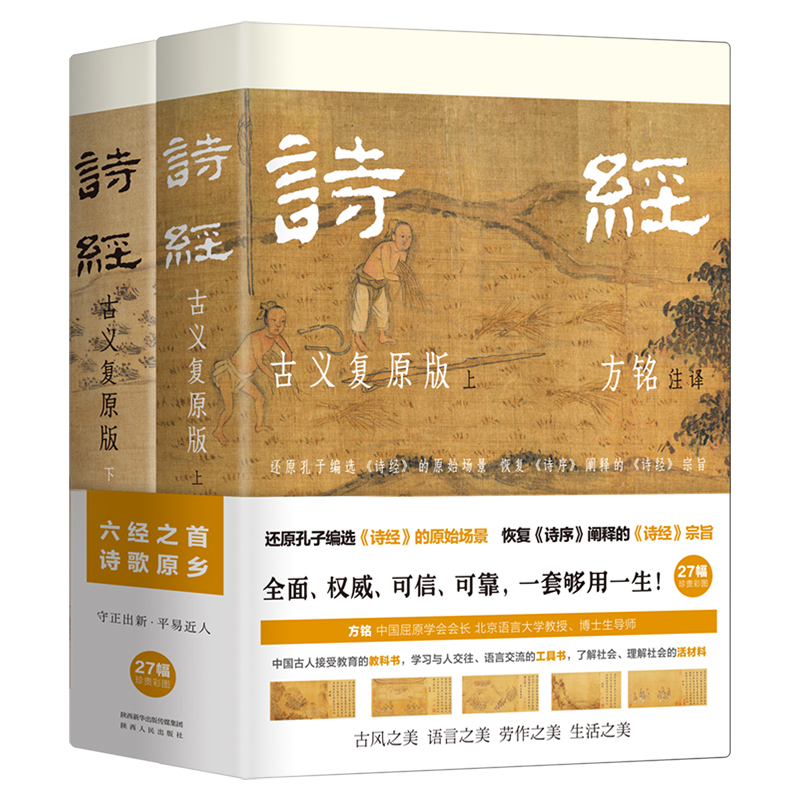
出版社: 陕西人民
原售价: 228.00
折扣价: 148.20
折扣购买: 诗经(古义复原版上下)
ISBN: 978722414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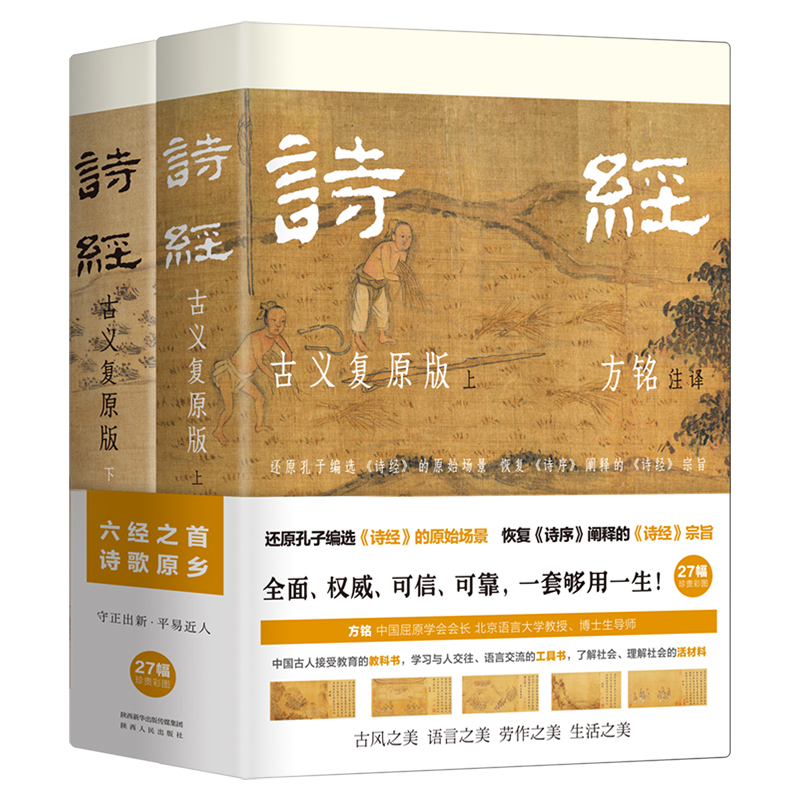
方铭 1964年生,甘肃庆阳人。从1980年起,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近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经学、诸子学、辞赋学等方面的研究。
前?言 《诗经》是孔子所编六经之一,也是我国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有305篇诗歌,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这些诗歌绝大部分是西周时代创作的,但也有部分作品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叶,时间从公元前11世纪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历时500多年,而如《商颂》等作品,其创作时代应该在商朝,《豳风》的部分作品时代也应该是在周灭商之前。它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诗经》初一般被称为《诗》,或者叫《诗》三百、《三百篇》,至《荀子·劝学篇》次称诗为经,至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正式有了《诗经》之名。 一 周代诗的收集和编辑,有专门的机构和负责的人,《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孔丛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这里提到的采诗之人有采诗之官、行人、国史的区别。西周之际采诗应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国史总其全责,而行人以周游列国的便利成就其事。《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就说明国史在采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汉代设立专门的乐府机构的初衷,应该是为了学习周代的采诗制度。 国史是史官,在记史之时兼记各国产生的诗歌大概也是其职责。《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中期以后,周天子威仪不再,礼崩乐坏,宗周式微,诸侯国不再把天子放在眼里,史官在诸侯国地位尴尬,“王者之迹熄”,而诗的采集也就消失了。 虽然西周的诗是经过国史、行人、采诗之官采集而来,但不能说这些诗完全来自民间,现存《诗经》中真正出自里巷的歌谣应该并不多。毕竟在那个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学习文化的时代,民间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创作活动。从三百篇来看,多数创作者都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国语·周语》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国语·晋语》曰:“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左传·襄公十四年》亦有类似记载。周代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陈诗,诵谏于朝,这些作品之中优秀的作品肯定会保存在《诗经》中,公卿列士所献之诗,相信除了自己的创作外,也有采集自列国的作品。 诗歌收集到中央后,还要经过编辑与整理。从事这一工作的应是王室的乐官。《周礼·春官·大师》曰: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师,就是乐官,他们在传授诗歌时,自然会对诗歌进行整理加工,其中也包括修饰润色等艺术上的加工。至孔子,则对周代收集的诗进一步加工整理。司马迁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等文献。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古时诗有三千余首,到孔子时,可能已经不全了。所以,《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不一定看到过3000多首古诗,他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可见,孔子对《诗》所做的主要是整理编辑工作。 孔子编辑、删节、整理《诗经》后,用《诗经》作为教材教授子弟,而春秋时代的行人士大夫,多能登高赋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而后,子夏对《诗经》的传播居功甚伟。秦烧书后,在汉朝,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的《诗经》立于学官,称《齐诗》《鲁诗》《韩诗》,为今文经学。后来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治古文经,称为《毛诗》。今天流传的《诗经》是《毛诗》。 在十五《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或者殷商后期的作品,其他当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作品。《大雅》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周王朝的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包括周王朝的上层贵族,也有诸侯国的贵族和地位低微的下层士大夫。《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鲁颂》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应该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 《诗序》还提到变风、变雅的问题,所谓“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认为,“二南”属于正风,其他十三《国风》属于变风,《鹿鸣》至《菁莪》16篇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黄》58篇为变小雅,《文王》至《卷阿》18篇属于正大雅,《民劳》至《召旻》13篇是变大雅。正风、正雅是歌颂西周先王和盛世的,变风、变雅是在衰乱之世的怨刺淫乱之言。 《国风》的篇《关雎》,《小雅》的篇《鹿鸣》,《大雅》的篇《文王》,《周颂》的篇《清庙》,又被称为“四始”,是《诗经》各部分的经典之作。 二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先王政典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周王朝教育子弟,祭祀、朝聘、宴享等场合所需要经常重温的重要内容,在一般的外交及日常政治、文化交往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赋诗言志,是当时政治、文化、外交场合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在《左传》等典籍中,记载古代赋诗言志的例子很多。 现存《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国风,共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凡160篇。有人把“二南”拿出,专门设立“南诗”一类,则只有十三《国风》。又《邶风》《鄘风》《王风》皆王风,《豳风》《秦风》为一国之风,所以又有十一《国风》、九《国风》的说法。雅105篇,有《大雅》《小雅》的分类,《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有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根据《孔子诗论》,国风在汉以前的名字应该叫“邦风”,大约是缘于汉以前的诸侯国本来就叫“邦”,只是因为避刘邦讳,所以,经过汉代儒生流传下来的文献,把“邦”改为国,因此才有诸侯“国”的说法。 国风主要反映诸侯国民众的生活,大小雅则以政治讽喻诗为主,颂主要是歌颂先圣王的著作。国风来自诸侯国,是土风,大小雅来自朝廷周天子的近臣,颂来源于国史、大师这样的专业人员。所以,国风应该是王朝采诗官(大师、行人、史、采诗官)所采集,用来反映诸侯国世情民俗的;大小雅中的政治讽喻诗多数为士大夫所献;祭祀、宴享的颂诗应该多数是巫、史所作。 《诗序》说风的意思是“讽”,“下以风刺上,上以风化下,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周天子了解诸侯国社会状况的重要途径。雅包括大雅、小雅。“雅”又称为“夏”,《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由于政有大小,所以有大雅、小雅之区分;《大雅》的篇幅较长,《小雅》的篇幅较短;《大雅》多为歌颂祖先与神明的赞美颂扬的诗,《小雅》则更多为对社会的揭露与批判的诗,以及记录贵族生活的诗。又称为“”“讼”,《诗序》说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颂一般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明时的祭歌,内容多是对祖先功德的歌颂与赞美,也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的情况。 《诗经》各篇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的争论,要探讨《诗经》各篇的主题,我们不能不考虑《诗经》总体在当时文化氛围中的地位和功能。《诗序》说先王用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说明《诗经》各篇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内涵。 赋、比、兴,是为《诗经》六义之三。但赋、比、兴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诗序》并未作出明确的交待。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此三者为“诗之所用”,也即今天所谓诗的表现手法。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此的解释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他认为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赋是铺陈,是对事、物等的直接的描述。雅、颂等基本上是采用赋的手法,因为赋的描述性使它善于叙事,如《生民》《公刘》等史诗,全篇都是在叙述历史事件。赋也可以写景状物,如《小雅·采薇》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过去的景与现在的景联系在一起,铺叙之中包含着深切沧桑的情感。《卫风·硕人》对庄姜的描绘出神入化:“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句细致地叙写了庄姜美丽的手、皮肤、脖子、牙齿、额头,而后再写她美丽的微笑,流转的目光,整个美人的形象顿时灵动起来,熠熠生辉。《豳风·七月》是一首叙事诗,诗中即用赋来叙事,如“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等,在其中占大部分篇幅。该诗也用赋来写景,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叙事写景相错,充分地体现 了赋的作用。《国风》中较多用赋的还有《郑风·溱洧》《卫风·氓》等。 比就是比喻。《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而且比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明喻如《陈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在铺排赋写的同时又应用了巧妙的比喻。《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也是明喻。暗喻如《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为虺蜴”等。有的比喻只出现了被比作的事物,如《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直接将卫宣公称为籧篨,这是借喻。有的比喻将一个事物连续比作多个事物,称为博喻。如《小雅·天保》曰:“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川莫不增。”连用了五个比喻来形容兴盛的事业。又如《卫风·淇奥》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连用了四个比喻来形容君子不同一般的翩翩风度。不但比喻的形式多种多样,喻体的选择也是多样化的,从前面的例子里便可看出,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甚至地理环境、现象等,都可当作喻体,而人的活动,如对玉的切磋、琢磨也可当作喻体。比的多种多样使得诗歌的形象更加明晰,更利于领会理解,诗歌的意象也更为活泼自然。 兴有时容易与比混为一谈。先言他物,他物与下文所咏之词必须有某种内在联系。但两者之间并不是打比方,而是以他物为抒发感情的发端。因此兴常常用在篇首或章首,又称为“起兴”。《国风》比较广泛地采用了兴的手法。如《周南·螽斯》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先以螽斯(蝗虫)起兴,再由蝗虫成群结队地展动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联系到多子多孙,借以祝人子孙满堂。《邶风·凯风》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温暖和煦的风从南边吹来,以此想到温柔和善的母亲。这首诗不但以凯风南来起兴,还暗将幼子比作“棘心”(酸枣树幼苗),兴中还有比。兴还能描绘景色,烘托全篇气氛。如《周南·桃夭》以鲜艳的桃花起兴,渲染新娘出嫁时的喜气洋洋,《秦风·蒹葭》以萧瑟秋景起兴,烘托主人公的失意迷惘。《邶风·谷风》一开篇“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勾画出凄凉的气氛来表现女主人公悲愤的心境。赋、比、兴作三种表现手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三种手法往往交错为用。一般地说,赋有时可以构成全篇,通篇用比的比较少,而兴则只在篇首或章首了。 《诗经》的语言质朴简单,同时又非常优美典雅,体现了高超的语言艺术。《诗经》里的诗都是可以和乐而歌的,因而浅显易懂。重章复沓之处比较多,使诗歌显得单纯明朗,具有质朴的艺术美。如《周南·苤苢》曰:“采采苤苢,薄言采之。采采苤苢,薄言有之。采采苤苢,薄言掇之。采采苤苢,薄言捋之。采采苤苢,薄言袺之。采采苤苢,薄言襭之。”诗歌描写妇女们采摘车前子时愉快的劳动场面。每章的变化只有动词,语言明白如话。而从动词又可以看出其用词的准确性,“采”“有”“掇”“捋”“袺”“襭”六个动词都是描写采摘的动作,不 同的词表现出不同的动作,而且还反映了采摘的进度和采摘的用具,准确而精炼。同时,诗歌的每一句都用“采采”打头,显得轻快活泼,体现了《诗经》语言的又一特点,即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来增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文心雕龙·物色》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正是这些词的大量使用,使诗歌所表现的形象鲜明准确, 而且使音节宛转流畅,即使我们今天朗诵起来,仍是朗朗上口,如出天然。 《诗经》以四言体为主,四言体与早期的二言体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表现在它的容量增大,容纳了丰富的词汇,句式增多,能表达各种语气,有时音节不足四言,就用词头或语气词来补足。如《苤苢》中的“薄言”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头,而《鄘风·柏舟》中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既补足成了四言,还表达了强烈的语气。四言体之外,杂言体诗的数量也不少。其句式参差不齐,灵活机动,完全由语意来决定句子长短。虽然杂言体形式不整齐,但节奏自然灵活,错落有致,使《诗经》显得比较富于变化。在章节上,《诗经》多是重章叠句的形式。章节复叠的形式很多,有的诗每章都有复沓的部分,有的诗只有部分章节复沓。这种复沓的形式利于歌唱时反复吟诵,增加节奏感且利于记诵。而且在回环往复之中又能深化主题,加强感染力。如《王风·采葛》在反复歌唱中,主要改变的是“三月”“三秋”“三岁”,一章比一章递进深入,相思的心情溢于言表。 《诗经》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的个高峰,它在创作上的成就,使它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典范。《诗经》善于描写社会生活,表现具体的生活场面,并体现出对时政、国家与人民的关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对自由平等的热烈追求。这一类诗主要在国风和大小雅之中,后人就将这种精神称之为“风雅”。 三 作为六经之一,《诗经》及其阐释,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诗经》阐释史上,《诗序》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由尊《诗序》到废《诗序》,是《诗经》阐释史的一条基本发展线索。 讨论《诗序》问题,首先面临的是《诗序》的作者问题。《诗序》作者问题争议的起源,在于郑玄的多次貌似矛盾的表述,为后代好疑古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而郑樵《诗辨妄》断言《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诗序》的价值。这种显然不合实际的观点,今天仍然为有些学者所坚持。 我们注意到,虽然关于《诗序》作者的说法不少,但除了汉儒的说法应该来源于师传以外,其余的学说或者是在汉儒的见解之基础上的发挥,或者是纯粹的臆测,没有什么足以打倒汉儒之说的证据。因此,在讨论《诗序》作者的时候,我们首先所应注意的,应该是汉儒的说法。其原因是汉儒去古不远,亲受师说,而汉儒虽经焚书之祸,却是重视师承。自孔子而后,迄两汉之亡,学者之学,皆守祖训,师弟相传,不绝如缕,如有背叛,不仅不容于师门,亦为君主及博士弟子所不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具有盛名的大儒,是不能信口雌黄的。 汉朝是《诗经》学术繁荣的时期。就汉而论,经师既众,著作也就不少,而其中又各自立门户,号称四家。其中今文学家《齐诗》《鲁诗》《韩诗》三家,西汉初俱在学官,得立为博士,而《毛诗》在汉平帝及王莽时,也在学官。其中盛况,班固《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而《汉书·儒林传》说,西汉传《诗》而成门派的,《鲁诗》有韦氏之学、张氏之学、唐氏之学、褚氏之学,《齐诗》有翼氏之学、匡氏之学、师氏之学、伏氏之学,《韩诗》有王氏之学、食氏之学、长孙氏之学。东汉之时,传诸家诗者,有高诩、包咸、包福、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张匡、卫宏等,而大儒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传《毛诗》,因此《毛诗》大盛。 汉代治《诗》的学者虽多,著作却基本不存。《诗序》的作者问题,相信在两汉之际并不是需要大家研究的问题,所以。汉代学者几乎没有专门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检索两汉学者的观点,唯有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儒郑玄在他的论述中提到了《诗序》的作者问题。其观点如下:,《毛诗南陔白华华黍序笺》云子夏作;第二,《诗谱》云子夏、毛公合作。由于子夏作《诗序》及子夏、毛公合作《诗序》的说法皆出自郑玄,因此,子夏所作和子夏、毛公合作的说法应该是两个不相矛盾的版本,其中的歧义应该来源于郑玄说话时的不同语境所突出的侧重点,所以子夏所作和子夏、毛公合作说实际是同一主张。 郑玄之言《诗序》为子夏所作或者子夏、毛公合作,其观点与其说是指子夏或者子夏、毛公作,倒不如说是子夏述《诗序》。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曰:“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而《毛诗南陔白华华黍序笺》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事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毛诗正义·小雅·棠棣》引《郑志》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意即《诗序》虽为子夏所作,但其基本观点当传自孔子,子夏书诸文字,而毛公为之增益润色。郑玄笺《诗》,“于毛义有未合者,间下己意,或参取三家说之。计异于毛者,无虑数百事”。则郑玄也实在没有故意杜撰出一个大名鼎鼎的子夏作《诗序》来和自己作对的理由。 关于郑玄所述的《诗序》著作权问题,略后于郑玄时代的魏晋六朝及唐代的学者并没有异议,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注》、陆德明《经典释文》、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萧统《昭明文选》、成伯玙《毛诗指说》、魏徵等《隋书·经籍志》皆肯定郑玄所说的《诗序》与子夏的关系。 《诗序》为子夏所作,而其来源为孔子教授弟子的讲义,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孔子的讲义也不应该是凭空杜撰的,成伯玙《毛诗指说》云:“序者绪也,如蚕丝之有绪,申其述作之意也。”则《诗序》的初作者应该是《诗》的原作者或者整理者,后来被大师引用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之教学活动,常以《诗》为教材,述而不作,必用前人之《序》。如果认为采诗官所收集的诗可能没有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以六诗教国子和陈诗以观的大师不知道每一首诗的主题,天子在欣赏诗乐舞时不知道所赖以“观风俗、知善恶、自考正”的《风》《雅》的主题,庙堂祭祀者不知所奏音乐的内容,那无疑是荒唐的。所以,王安石云:“《诗序》,诗人所自制。”又云:“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美媵,《那》之为祀成汤,《殷武》之为祀高宗。方其时也,无意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程颐之主张国史写《小序》之首句,说诗者续补,作诗大义非后代人所可知者,如《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曰:“《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这种观点,虽出自推测,但与郑玄的主张并不对立。因为郑玄谓子夏受之孔子,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能成功地把诗人或者国史所写的《序》传之后世。当然,如果认为孔子及子夏没有发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诗序》应该是诗人或者采诗官所记,大师所传,至孔子删诗,有所删正,子夏传之,毛公加以申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诗序》包含毛苌以前经师所传的“首两语”,及毛苌以下弟子所附的“续申之词”。虽嫌模糊,却也庶几近之。 可以认为,《诗序》是诗人创作动机及汉代以前的学者研究《诗经》的结晶。而其中浸染的孔子的心得一定不少。《论语》《诗论》与《诗序》的精神相合,而孔子的《诗经》学说远不止此。上海博物馆《孔子诗论》的发布,更加说明《诗序》的可靠性。 郭店楚简《语丛一》曰:“《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其观点与《诗序》相同。诗者言志,所言之志,当然首先是作诗者之志,而作诗者之志,不能靠后人的推测,所以,作者的手阐述是为重要的。由于《诗序》即是现存早的关于《诗经》各篇主旨的论述,其中必然包括诗人的阐述和采诗官的解说。今天我们没有充分坚实的证据证明《诗序》是“村野妄人”之杜撰,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其准确性。 《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根据班固的意见,我们可知《毛诗》之学,来源于子夏,而子夏是孔子学生中“文学”一科的代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司马贞《史记》曰:“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论语·八佾》载有孔子与子夏讨论《诗》的对话,子夏作为《诗》的专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家《诗》及《毛诗》皆祖子夏,因此,《诗序》绝不是《毛诗》一家之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诗序》云《孟子·万章上》说《北山》之诗意用《小序》;惠栋《后汉书补注》证明东汉的服虔、杨震、李尤、蔡邕皆用《诗序》之言;而朱冠华更指出《礼记·乐记》用《鄘风·桑中序》,《易传·兑卦·彖》用《豳风·东山序》,又云三家诗义与《诗序》并无矛盾,与《毛诗》的差别只是解说的水平高下而已。《隋书·经籍志》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意多异,世所不行。”三家《诗》消亡的原因,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叙》说得很清楚:“两汉信鲁而齐亡,魏晋用韩而鲁亡,隋唐以迄赵宋称郑而韩亦亡,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三家是随着《毛诗》与《毛诗故训传笺》的攀升而衰落,并终消亡, 其原因在其自身。正如陈奂所言:“三家多采杂说,与《仪礼》《论语》《孟子》《春秋》内、外传论诗往往或不合。三家虽自出于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没,微言已绝,大道多歧,异端共作。又或潜以讽动时君,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志,故齐鲁韩可废,毛不可废。”也就是说,虽然研究《诗经》的学派和著作众多,但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优胜劣的自然发展过程,《毛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的。黄焯先生《毛诗郑笺平议·序》云:“《诗》自夫子录为三百篇,以授子夏;子夏取其义著之于《序》,数传而至大毛公,作《故训传》。小毛公承其学,故名其诗曰《毛诗》。汉初,《诗》别有齐、鲁、韩三家,说往往与毛异。 盖自秦焚弃儒术,三百篇虽以讽诵得传,而于篇义,久之或莫能省记。至取《春秋》,采杂说,而弥失其本义。又以口耳相传,说《诗》者或以作诗之人与赓诗之事兼收并采,记之者乃互有详略,有记作诗之人而遗赓诗之人,记赓诗之事而遗作诗之事者,于是说互歧而派别立。校其朔,则皆出子夏,与 《毛传》足互相发明,有未可偏废者,《毛诗》以篇义独完,故详于训故,而于义稍略,于数家中可依据。故两汉诸大儒多有论述。顾以出稍晚,未得立于学官。”黄焯先生论述三家《诗》及《毛诗》的消长,可谓极其客观。 《序》之渊源久远,但《序》分散入各篇则在汉代。郑玄说毛亨在作《故训传》时把《序》冠于各篇之首,应该是准确的。也正因此,《南陔》等笙诗才能在诗亡以后存有诗意,而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诗经》无《序》的情况也可以为郑玄的说法提供证据。可以认为,三家《诗》及《毛诗》等经师,他们在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是没有《序》及注解的版本,而诸家师徒相传,主要是按照《诗序》的线索来解说。也正因此,《诗序》到了子夏所处时代时才有文字版本。这就为《诗经》的普及提供了方便,这也是适应孔子设立“私学”以后,学生和导师增多的现实需要的。毛亨把《诗序》置于《诗经》各诗篇首,更加便于《诗经》的阅读者直接掌握各诗之主旨,相信是在学习《诗经》不依赖于博士讲授以后有效的方法,这肯定在客观上为《毛诗》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方便。 《诗序》是学习和研究《诗经》诸篇的门径,但并不是说《诗序》的每一句话皆不可怀疑。特别是作诗之人,多用修辞,或比或兴,言多不足实证。如果字字坐实,必然损害诗的整体。在这个时候,坚定对《诗序》的认识,不仅仅关系到某一首诗的正确解读问题,而且关系到对《诗经》传承的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之隐约而微,是适应表现其志的要求的,因此,难于等同于入道见志之书的明白畅晓。扬雄《法言·寡见》云:“说志者莫辨乎《诗》。”《诗》之说志辨,就在于为隐晦。《孟子·万章上》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在解说《北山》诗时,揭橥此一原则,就是强调,不要因为对《诗》的文辞的不同理解而影响对《诗》的主旨的把握,更不能因此成为怀疑《诗序》的口实。正像钱大昕所说:“诗人之志见乎《序》,舍《序》而言《诗》,孟子所不取。后儒去古益远,欲以一人之私意,窥测古人,亦见其惑矣。”黄焯先生指出:“《诗》之本义,皆见于《序》,《序》意乃孔子亲问于大师,以授子夏。使《诗》而无《序》,虽圣人不能知其本义。今试读同时人集,去其前题,而以意测其诗旨云何,犹鲜有当者。况出于古人二千余年以上之诗篇哉。吕氏《读诗记》引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序》间有后人附益,或毛公续作者,然要为周秦旧说,确具师承,皆可依信。”因此,我们研究《诗经》主旨,主要任务不是发明与《诗序》不同的《诗经》主旨,而是应该在《诗序》所确定的框架内,尽力解决看似有“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地方,真正恢复作《诗》者的本意。 四 本注本以阮元《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参考其他传世善本,并及出土文献。在注释过程中参考了前修时彦的宏论,尽可能一一标明。对不易理解的诗句,斟加串讲,意图通过探索《诗序》与《诗经》文本的联系,复原《诗经》的本来面貌,给读者一个学习《诗经》的参考范本。 感谢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研究会副会长、*人文社科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慨然赐序。感谢高高国际高欣先生对此书出版所做的各种努力,没有高高国际的支持,这本书可能就会一直搁置在电脑之中了。 《诗经:古义复原版》一书,从开始撰写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了,十余年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陈静、宋博雅、李梦、林满平、徐伟、郭琦、胡静、殷世宜、许震群、向上、刘勤(马来西亚)、丁海玲、刘娟参加了校注和修改工作,博士后工作人员李燕博士、博士生冯茂民同学先后进行了文字文献校对,工作人员李雁博士校对了清样,在此一并致谢。 1.“不学《诗》,无以言。”它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与文化基因、美学底色,字字皆动人,句句是人生。《诗经》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礼乐文化,也因其朴实感性的语言、丰富形象的修辞手法,充分展现了中文的语言之美与风雅精神,自其诞生之后的2500多年里,一直是古代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入门教科书、学习与人交往交流的语言工具书、了解和理解社会复杂性的现实主义活材料。 2.《诗经:古义复原版》以《诗序》为纲,守正出新,是复原《诗经》古义的集大成之作。本书旨在还原孔子选编《诗经》的原始场景,恢复《诗序》阐释的《诗经》宗旨,尽力解决众多《诗经》研究作品中存在的“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通病。 3.《诗经:古义复原版》集引证、注释、解读、注音于一体,可诵、易懂、好读,兼具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欣赏价值、收藏价值,一套可用一生。《诗经:古义复原版》引证丰富,收录古今近100位学者所著的150余种《诗经》作品的研究成果;注释繁而不复、生僻字皆有注音,且从字词到诗篇,方铭教授均奉上了独到精彩的解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4.底本可靠,精编精校,恢复《诗经》文字原貌。本书以清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传世善本及出土文献,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国诗学的开山之作——《孔子诗论》、安徽大学藏竹简本——安大简《诗经》,原汁原味、底本可靠,向读者展示《诗经》文字原貌。 5.方铭教授师出名门且长期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在学术研究与资料收集上,足以为《诗经:古义复原版》的全面、可靠、翔实背书。方铭教授既从一代儒宗马一浮的高足经学大师吴林伯教授那里继承了遵从孔子,尊重汉学的传统,又从一代《诗经》学研究宗师黄焯先生手中继承了以《诗序》为法的《诗经》研究之法,随后师从著名的先秦两汉文学专家、文学史家褚斌杰教授,近30年来一直从事古籍的整理工作,从而保证其占有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且底本可靠。 6.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作序推荐。用《诗经》研究专家和普通读者双重视角,对《诗经:古义复原版》的师门渊源、学术价值、研究方法、成书特点等方面,给予中肯专业的点评与解读,不啻一篇专业精炼的导读文本。 7.内附27幅来自中日两国的高清传世名画,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审美视角复原诗经的风雅世界。宋马和之所绘、宋高宗赵构楷书的《诗经》三百篇,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细井徇所绘《诗经名物图解》,展示中日两位古代绘者,从各自民族的文化审美视角,复原现《诗经》古义中蕴含的来自周王室、贵族、诸侯、士子、平民的古风之美、生活之美、劳作之美、自然之美。 8.装帧精致典雅,裸书脊锁线胶订,可180度自由翻转,让阅读更随心。用纸考究,光滑护眼,版式疏朗大方,绿色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