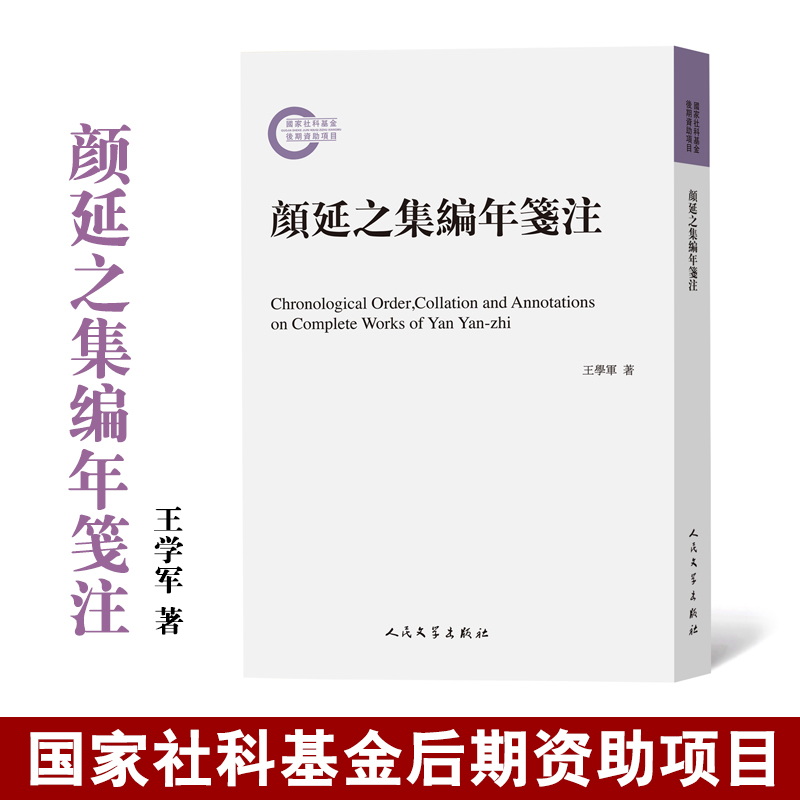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138.00
折扣价: 91.10
折扣购买: 颜延之集编年笺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166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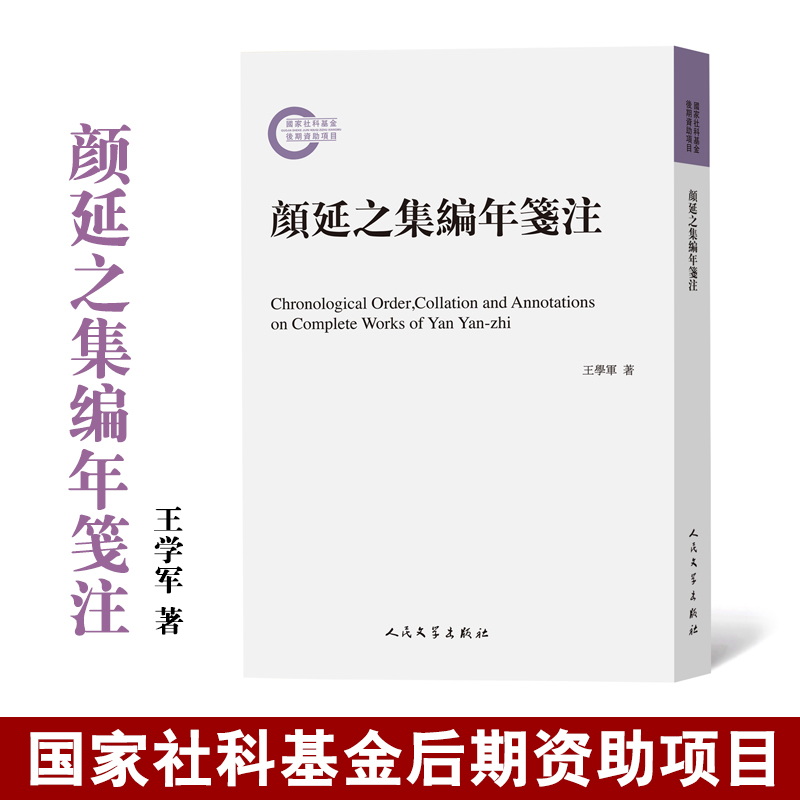
王学军,安徽芜湖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与文献,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河南省“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南阳师范学院卧龙特聘教授等荣誉或奖励,主持完成“颜延之集编年笺注”“汉魏六朝礼制与文学研究”2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文化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史学月刊》《孔子研究》《古代文明》《中南大学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6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3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新华文摘》论点摘编1篇。
北使洛〔一〕(一)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二〕(二)。振楫發吳洲〔三〕,秣馬陵楚山(三)。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四)。前登陽城路,日〔四〕夕望三川(五)。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六)。伊穀〔五〕絕津濟,臺館無尺椽(七)。宮陛〔六〕多巢穴,城闕生雲烟(八)。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九)。陰風振涼野,飛雪〔七〕瞀窮天(一〇)。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一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一二)。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一三)。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一四)。 【校】 本詩以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七所載爲底本,用《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六臣注文選》卷二十七、《古詩紀》卷五十六、張燮《顏集》、張溥《顏集》參校。 〔一〕《藝文類聚》詩題作《北使至洛》。 〔二〕“難”,諸本作“艱”,二字義同。“險難”一詞早出,先秦已有,如屈原《九歌·山鬼》云“路險難兮獨後來”,而“險艱”此前未見使用,故此處作“難”。 〔三〕“洲”,李善注《文選》《藝文類聚》作“州”,諸本作“洲”。“州”爲“洲”之古字,二字同。 〔四〕“日”,《藝文類聚》訛作“旦”。 〔五〕“穀”,《藝文類聚》作“洛”,《六臣注文選》《古詩紀》、張燮《顏集》、張溥《顏集》作“瀔”。“穀”“瀔”二字通。 〔六〕“陛”,《藝文類聚》作“階”,二字義近。此處“宮陛”指皇宮,漢魏時期已有此用法,如《後漢書·董卓傳》載:“(呂布)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而“宮階”則無此義,故此處作“陛”。 〔七〕“雪”,《藝文類聚》作“雪”,諸本作“雲”。“飛雪”較“飛雲”更契合下文“瞀窮天”的描述。 【注】 (一)北使洛:顏延之時任中軍行參軍,奉中軍將軍府之命出使洛陽。洛,西晉故都洛陽,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時收復。 (二)改服:更換衣服,這裏指換上行裝。飭:修整、整治,這裏指整備行裝。徒旅:旅客。首路:上路出發。跼:彎曲,這裏指路塗蜿蜒漫長。 (三)振楫:揮動船楫,借指水路行船。吳洲:吳地河洲,這裏指建康附近的水洲。秣馬:飼馬、喂馬,借指陸路騎馬。楚山:本義指荆山,在今湖北西部,這裏泛指建康附近的山(戰國屬楚地,故以楚山代稱)。此句謂顏延之從建康出發,水陸船馬交用北上。 (四)梁宋郊:東周魏國、宋國都城附近之地。戰國中後期魏國定都大梁,故別稱梁國;宋國定都商丘。“梁宋郊”在今河南東部,顏延之出使洛陽塗經此地。道由周鄭間:出使所行道路位於東周王畿和鄭國屬地範圍內(今河南中部)。 (五)陽城:地名,據《晉書·地理志》,晉時陽城縣屬河南郡,在今河南登封。三川:黃河、洛河、伊河的合稱,秦在三河交滙帶設三川郡,西晉改設河南郡,都城洛陽位於此地。 (六)在昔:從前,往昔。期運:機運,時機。蔡邕《陳太丘碑》云:“含元精之和,膺期運之數。”經始:開始量度、籌畫,這裏承上句,指由此開始。《詩經·大雅·靈臺》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闊:疏遠,遠離。此句謂西晉末年國運衰微,中原長期淪陷於異族,聖賢久不現世。 (七)伊穀:伊水、穀水的合稱,二水爲洛水支流。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云:“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李善注引《漢書》云:“穀水出穀陽臺,東北入洛水。”津濟:渡口。臺館:樓臺館閣。無尺椽:沒有一尺長的屋椽,借指樓臺館閣蕩然無存。李善注引曹植《毀故殿令》云:“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 (八)宮陛:宮殿的臺階,借指洛陽皇宮。城闕:城樓和宮闕,代指西晉都城洛陽。 (九)王猷:王道。束晳《補亡詩》云:“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八表:八方之外,指極遠的地方。暮年:老年,晚年,此時顏延之祗有三十四歲,因而暮年非實指年齡,而是指身體、精神衰弱頹廢。 (一〇)涼野:荒寒的曠野。飛雪瞀窮天:飛雪勢大,天色晦暗不明。《說文解字注》釋“瞀”云:“目不明皃……皆謂冒亂不明。”窮天,高入天際。 (一一)臨塗:在行塗中。置酒:陳設酒宴。 (一二)隱憫:隱居不得志而憂傷,這裏指憂慮歎息。嚴忌《哀時命》云:“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威遲:指道路曲折綿延。顏延之《秋胡行》云:“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良馬煩:良馬煩躁,形容旅塗勞頓。 (一三)遊役:指此次出使洛陽之行。芳時:花開時節,指美好時光。屢徂愆:屢次耽誤歸期。徂,往,去。愆,超過,延誤。《詩經·衛風·氓》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一四)蓬心:蓬草之心,比喻知識淺薄,不能通達事理,這裏是自喻淺陋的謙辭。《莊子·逍遙遊》載:“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成玄英疏:“蓬,草名,拳曲不直也……言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飛薄:這裏爲自傷之辭,形容自己身如飛蓬,以至長塗跋涉,異地飄零。《文選》李善注此句云:“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 【繫年】 《北使洛》是現存顏延之最早創作的詩歌。硏究者多認爲此詩作於義熙十二年冬,如繆鉞《顏延之年譜》、沈玉成《關於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諶東飆《顏延之硏究》等。由文本出發,結合相關材料考察,《北使洛》當作於義熙十三年二月左右。 《宋書·顏延之傳》(省稱《宋書》本傳)載: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 這裏“道中作詩二首”,卽《北使洛》和《還至梁城作》。與《宋書》類似,《南史·顏延之傳》(省稱《南史》本傳)載: 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淒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 可見顏延之此次出使,緣於劉裕北伐取得重要戰果,“有宋公之授”。劉裕世子劉義符時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爲慶祝“殊命”,中軍將軍府派遣行參軍顏延之出使洛陽。《南史·宋本紀》、《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七載劉裕封宋公在義熙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此年十二月壬申爲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顏延之北使洛陽的出發時間當在此之後。 顏延之作《北使洛》時已至洛陽。《北使洛》敍出使行程云:“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一》載潤州“西北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里”、上元縣“東北至州一百八十里”,可見建康(唐代屬潤州上元)距洛陽約兩千里。東晉慶祝“殊命”使者的出行速度未見明文記錄。《唐六典·尚書戶部》“度支員外郎”載唐代驛路一般日行里程云:“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參照這一標準,顏延之乘馬(“威遲良馬煩”)從建康至洛陽約需一個月。考慮此次出行所遇風雪阻路的不利天氣條件(“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顏延之實際所用時間可能更長。因此,顏延之至洛陽當在義熙十三年二月左右。 收復洛陽是劉裕義熙十二年北伐取得的重大成果。洛陽爲西晉故都,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而義熙十二年十月,卽北伐先鋒軍收復洛陽後的次月,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向朝廷求取九錫。義熙十三年正月,在晉安帝授劉裕宋公、加九錫的詔書發布後不久,劉裕率領北伐軍主力由彭城向洛陽進發,其軍事用意是在洛陽會合先鋒部隊,以便下一步西進關中;政治用意是在西晉故都洛陽接見各地“慶殊命”的使者,進一步樹立聲望,強化威權。可以佐證的是,東晉皇室遣使授劉裕九錫亦在洛陽。《宋書·范泰傳》載:“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 由於沿塗遭到北魏軍隊的阻擊,北伐軍主力行程緩慢,直到義熙十三年三月,劉裕才抵達洛陽。《宋書·武帝本紀》載: 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三月庚辰,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至洛陽。七月,至陝城。 由於之前的時間延誤和之後軍事行動的需要,劉裕到達洛陽後不久,卽接見東晉皇室授九錫的使者袁湛、范泰以及包括顏延之在內的各地“慶殊命”的使者。劉裕到洛陽後,受到戰亂破壞的洛陽城已得到修繕,劉裕爲此重賞負責修治洛陽城的毛修之,“戍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直二千萬”(《宋書·毛修之傳》)。顏延之《北使洛》云:“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這當是顏延之到洛陽之後,洛陽城修繕工作尚未完成時的場景。因此,《北使洛》當作於顏延之到洛陽之後、劉裕到洛陽之前,在義熙十三年二月左右。 若將《北使洛》繫於義熙十二年冬創作,會出現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建康距洛陽約兩千里,義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晉安帝發布授劉裕宋公的詔書,此年無閏十二月,顏延之不可能在兩天內從建康趕到洛陽。第二,義熙十二年冬,劉裕一直留在彭城,直到義熙十三年正月方離開彭城東進,三月才抵達洛陽。顏延之義熙十二年冬“慶殊命”的目的地當是彭城,而非洛陽。這與《北使洛》詩題及詩歌所敘行程不符。《北使洛》所敘出使塗經地甚至未提及彭城。 需要說明的是《北使洛》一處詞句的誤讀。《北使洛》云:“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李善、繆鉞等學者將“暮年”理解爲“歲暮”,這也成爲此詩作於義熙十二年冬的“內證”。先唐文獻中,“暮年”均指老年、晚年,常含身體、精神衰弱頹廢之意,未見有歲暮、歲終之意。例如,曹操《步出夏門行·龜雖壽》云:“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又如,《宋書·范泰傳》載:“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因此,《北使洛》中的“暮年”並非指歲暮、歲終,而是指老年、晚年,此時顏延之只有三十四歲,因而暮年非實指年齡,而主要是身體、精神衰弱頹廢之意。 由上可知,顏延之《北使洛》作於義熙十三年二月左右,這一時間能與相關材料相容自洽,而義熙十二年冬則與現有材料存在明顯矛盾,難以成立。 【考辨】 一、詩歌“今事”“今情”發微 從藝術手法、語言特色等來看,顏延之《北使洛》與陸機《赴洛道中作》類似,卽景抒情,內蘊感傷,文辭工致繁複。《宋書》本傳載此詩“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當時文士關注的焦點是《北使洛》的文辭。單純的模仿難以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北使洛》的題旨有別於《赴洛道中作》。 此詩主要寫顏延之出使洛陽塗中的見聞和感受,反映行役艱辛,因而《文選》卷二十七歸之於“行旅”類。詩歌描寫行役之苦的同時,“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等詩句也滲透黍離之悲。行役之苦與黍離之感的結合形成了詩歌悲涼凝重的感情基調。古代學者已有關注,如沈德潛《古詩源》卷十評此詩云:“黍離之感,行役之悲,情旨暢越。”陳寅恪先生解讀詩歌強調“融古典今事(情)爲一”,下面探討顏延之《北使洛》中行役之苦與黍離之感涉及的“今事”“今情”。 顏延之此次出使洛陽,是爲了慶祝劉裕受封宋公這一“殊命”。劉裕所得到的遠不止是宋公這一封號。義熙十二年十月,北伐軍先鋒收復洛陽;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向朝廷求取九錫;義熙十二年十二月,晉安帝下詔書,正式任命劉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由於北伐尚未完全成功,劉裕當時並未接受九錫,但僅過了一年,卽北伐軍攻佔長安、滅亡後秦後不久,劉裕便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兩年後劉裕卽代晉自立。西漢末至東晉,權臣求九錫、加九錫多爲改朝換代前的準備工作,九錫近似權臣篡逆的代名詞,如王莽、曹操、司馬昭、桓温、桓玄等。劉裕求九錫也不例外,同樣是篡逆的前奏。晉安帝下詔書完全滿足劉裕的要求,這說明晉安帝祗是形式上的最高統治者。當時劉裕掌握軍政大權,有心有力篡逆,改朝換代已成必然之勢。顏延之此次慶“殊命”,正預示東晉王朝卽將滅亡、劉宋王朝卽將誕生。 顏延之的曾祖顏含追隨晉元帝南渡,爲建康顏氏之祖,此後顏氏家族有兩個特徵。一是世代官宦,族人多任東晉官職,如顏延之的曾祖顏含任侍中、國子祭酒等職,顏延之的祖父顏約任零陵太守,顏約的長兄顏髦任黃門郎、侍中、光祿勳,顏約的次兄顏謙任安成太守,顏延之的父親顏顯任護軍司馬等。二是崇儒守禮,“世善《周官》《左氏》”(《北齊書·顏之推傳》,顏之推爲顏延之的五世族孫),如顏延之的曾祖顏含以儒學立身,“少有操行,以孝聞”“儒素篤行”(《晉書·顏含傳》)。顏含重禮制,當時王導名位隆盛,有百官爲其降節行禮之議,顏含堅持君臣之禮,明確表達了反對意見,“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晉書·顏含傳》)。受家學淵源影響,顏延之服膺儒家思想,作有《逆降義》《論語說》等儒學著作。在立身處世上,顏延之也以儒家思想爲規範,如《宋書》本傳載:“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劄,延之醉,投劄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 顏延之熟知儒家經典,少時“好讀書,無所不覽”,作爲慶“殊命”的使者,他顯然知道劉裕加九錫的政治寓意。顏延之崇儒守禮,而劉裕加九錫之舉已是篡逆前兆,這不符合儒家君臣尊卑之義。顏延之與劉裕集團有聯繫,其妹嫁給劉裕心腹劉穆之的兒子(《宋書》本傳載“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然而《宋書·劉穆之傳》載劉穆之“三子”爲劉慮之、劉式之、劉貞之,《宋書》本傳中“劉憲之”可能爲“劉慮之”之誤)。顏延之時任劉裕世子劉義符的屬官,爲中軍行參軍。從家族情感、個人思想而言,顏延之的內心很難毫無保留地支持劉裕的篡逆之舉。當時劉裕掌握軍政大權,晉宋易代已是大勢所趨,作爲剛出仕不久的一介文士,顏延之自然無力改變這一形勢,只能目睹卽將到來的改朝換代的發生。 《北使洛》中大量詩句描寫行役之苦,如“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等。這不僅是客觀天氣、環境原因(“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等),更重要的是顏延之服膺儒家思想,對卽將滅亡的東晉有一定感情,很難完全認同劉裕的篡逆之舉,其內心深處對此次北上慶“殊命”、預示改朝換代之行有一定排斥感。《北使洛》“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等詩句表面上寫西晉故都洛陽的淒涼場景,感慨百年前西晉的覆亡,背後悲歎的則是卽將滅亡的東晉王朝,因而洛陽雖然收復,顏延之卻無多少喜意。這些構成了顏延之《北使洛》詩中行役之苦與黍離之感涉及的“今事”“今情”,加深了該詩悲涼凝重的感情基調。 前言 顏延之(三八四—四五六),字延年,元嘉三大家之一,當時與謝靈運並稱“顏謝”,是南北朝時期較有影響的文學家,也是晉宋之間文學“轉關”的樞紐人物之一。《宋書·顏延之傳》載:“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隋書·經籍志四》載:“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顏延之的作品凝練規整,用典豐贍,辭藻富麗,此爲古今學者的共識。鍾嶸《詩品》云:“(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嫻靜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 目前與顏延之集整理相關的硏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顏延之作品的輯佚、辨僞,如張燮《七十二家集·顏光祿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顏光祿集》、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等。目前這方面的成果較多,但存在不少缺漏、舛誤,有必要加以補充、訂正。二是顏延之作品的校勘、注釋。目前所知,祗有兩部著作對顏延之少部分作品進行了校勘或注釋,卽六臣注《文選》關於入選顏延之作品的注釋、李佳《顏延之詩文選注》(黃山書社二〇一二年版)對顏延之部分作品的校注。目前這方面的成果很少,亟需充實、完善。三是顏延之作品的繫年,如繆鉞《顏延之年譜》(《中國文化硏究彙刊》一九四八年第八卷)、李之亮《顏延之行實及〈文選〉所收詩文繫年》(《鄭州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石磊《顏延之行實與詩文作年新考》(《古籍整理硏究學刊》二〇〇八年第六期)等。目前顏延之大部分作品尚未繫年或繫年有異議,需要進一步考訂、釐清。四是其他可資參考的關於顏延之及作品的硏究,如黃水雲《顏延之及其詩文硏究》(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楊曉斌《顏延之生平與著述考》(西北師範大學二〇〇五年博士論文)、諶東飆《顏延之硏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總體而言,目前顏延之作品的輯錄尚不全面,無完整的校注本,編年亦不齊備,作品分析有待深入。本書在前人硏究的基礎上,結合現有資料,通過充分挖掘作品內外信息,完成顏延之集編年箋注工作,具體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輯佚、辨僞。從文獻資料中輯錄顏延之作品共七十六篇,其中佚文七篇六十五則,另有存目作品十七篇(部),僞作十四篇。二是校勘、注釋。選擇成書年代較早且內容較完整的善本爲底本,參照諸校本,從文本出發,對顏延之現存作品進行文字校勘,並結合文本及創作背景,對疑難字句加以注釋,標明典故出處,注重考察古典在作品中的現實意蘊。三是編年考訂。結合相關材料,對顏延之四十四篇尚未繫年的作品進行探討,對顏延之已繫年而有異議的十七篇作品進行再考察,對顏延之已繫年而無異議的十五篇作品進行補證。四是箋疏、考辨。從具體作品出發,對注釋中不能或不便展開的內容加以考論,包括易誤難解名物考辨、作品相關人物關係說明、作品相關時事背景分析、作品文學或文化意義闡發等。 本書的撰寫注重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考據和批評相結合,通過文學本位、歷史背景、文化學視角的結合來硏究作品,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把版本校勘、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於考據學方法的硏究,與文學批評,卽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結合起來。二是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與寫作的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批評結合起來。三是在注釋、繫年、考辨中,綜合運用歷史、地理、天文、曆法、宗教等學科的知識,以更好地解釋詞句含義、考訂創作時間、探討作品意蘊。 由硏究現狀和主要內容出發,本書具有以下價值和意義:一是文獻價值。本書首次全面、系統地對顏延之作品進行輯佚、辨僞、校勘、注釋、編年、考辨,具有原創意義。二是文學價值。通過注釋、考辨,本書能夠加深對顏延之作品的理解,對解讀相關文學作品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三是文化價值。本書對顏延之硏究有深化意義,硏究者可以據此了解顏延之創作的全貌,促成與顏延之相關的儒學、佛學、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硏究更好地展開。 顏延之的作品散佚嚴重,詩文“喜用古事”“情喻淵深”“一字一句,皆致意焉”(鍾嶸《詩品》),因而對其進行編年箋注是頗有難度而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受自己學識水平的限制,本書可能還存在一些不足或錯誤,懇請讀者給予批評指正,以俟修改完善。 凡例 一、本書所引顏延之作品,主要輯錄自宋代之前成書的早期文獻,共計十七種:(一)《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刻本)。(二)《初學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紹興十七年余十三郎宅刻本)。(三)《藝文類聚》(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紹興刻本)。(四)《弘明集》(中華大藏經本,其底本爲金藏廣勝寺本,殘缺字句補以高麗藏本)。(五)李善注《文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六)《太平御覽》(四部叢刊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七)《周禮注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八行本)。(八)《北堂書鈔》(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影宋刊本)。(九)《樂府詩集》(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十)《宋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元明三朝遞修本)。(十一)劉勰《文心雕龍》(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五年刻本)。(十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十三)吳均《續齊諧記》(明嘉靖《顧氏文房小說》本)。(十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末毛氏汲古閣覆刻本)。(十五)皇侃《論語義疏》(清乾隆五十三年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十六)《景定建康志》(清嘉慶六年金陵孫忠愍祠本)。(十七)《倭名類聚抄》(明治二十九年楊守敬刊本)。上述古籍在文中出現時,一般祗標書名,不注版本;若有同名古籍的其他版本,則另注版本以區分。 二、本書所用參校本,多爲明代之後成書的類書、總集或輯佚本,常用者有三十一種:(一)《六臣注文選》(四部叢刊影印南宋中期福建路刻本)。(二)《南史》(商務印書館影印元大德刻本)。(三)《藝文類聚》(明正德十年錫山華堅蘭雪堂銅活字本、日本東洋文庫藏朝鮮活字印本、明嘉靖九年宗文堂刊本)。(四)《古詩紀》(重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甄敬刻本)。(五)《初學記》(明嘉靖安國桂坡館刻本)。(六)《通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校本、明王德溢、吳鵬嘉靖刻本)。(七)葉廷珪《海錄碎事》(西安博物院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劉鳳刻本)。(八)張燮《七十二家集·顏光祿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張燮刻本,省稱“張燮《顏集》”)。(九)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顏光祿集》(深圳圖書館藏明末婁東張氏刻本,省稱“張溥《顏集》”)。(十)《古今歲時雜詠》(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十一)《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稿本)。(十二)《玉臺新詠》(四部叢刊影印明無錫孫氏活字本)。(十三)《册府元龜》(中華書局影印明末崇禎本)。(十四)《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磧砂藏本、四部叢刊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日本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十五)《宋書》(明北監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十六)《北堂書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十七)任椿小鉤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汪廷珍刻本)。(十八)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九年長沙嫏嬛館刊本)。(十九)顧震福《小學鉤沉續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刻本)。(二十)曹元忠《南菁劄記》(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江陰使署刻本)。(二十一)龍璋《小學搜佚》(民國十八年攸水龍氏鉛印本)。(二十二)黃奭《黃氏逸書考》(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二十三)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二十四)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上述古籍在文中出現時,一般祗標書名,不注版本;若有同名古籍的其他版本,則另注版本以區分。 三、本書校勘基本原則:(一)凡底本誤、脫、衍字而更正者,均出校記予以說明;底本正確而他本錯誤者,則校記從簡。(二)底本、他本兩可者,一般從底本,錄他本於校記。(三)底本所用俗字、古今字、異體字等,一般改作通行繁體字,如慙、慚統一作慚。不出校記。(四)底本所用通假字,一般保留原字不變,用“通”示之,如辨與辯、茲與滋。 四、正文中顏延之作品的編年箋注,一般先引作品篇名及內容,而後依次進行校、注、繫年(創作時間考)、考辨(對注釋中不能或不便展開的內容加以補充論證,如顏延之生平行事考訂、易誤難解名物考辨、作品涉及人物關係說明、作品時事背景分析等)。 五、作爲補充,本文附錄主要包括輯佚、辨僞、存目作品考、顏延之出仕考、顏延之年譜新編、顏延之評論資料彙編六個方面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