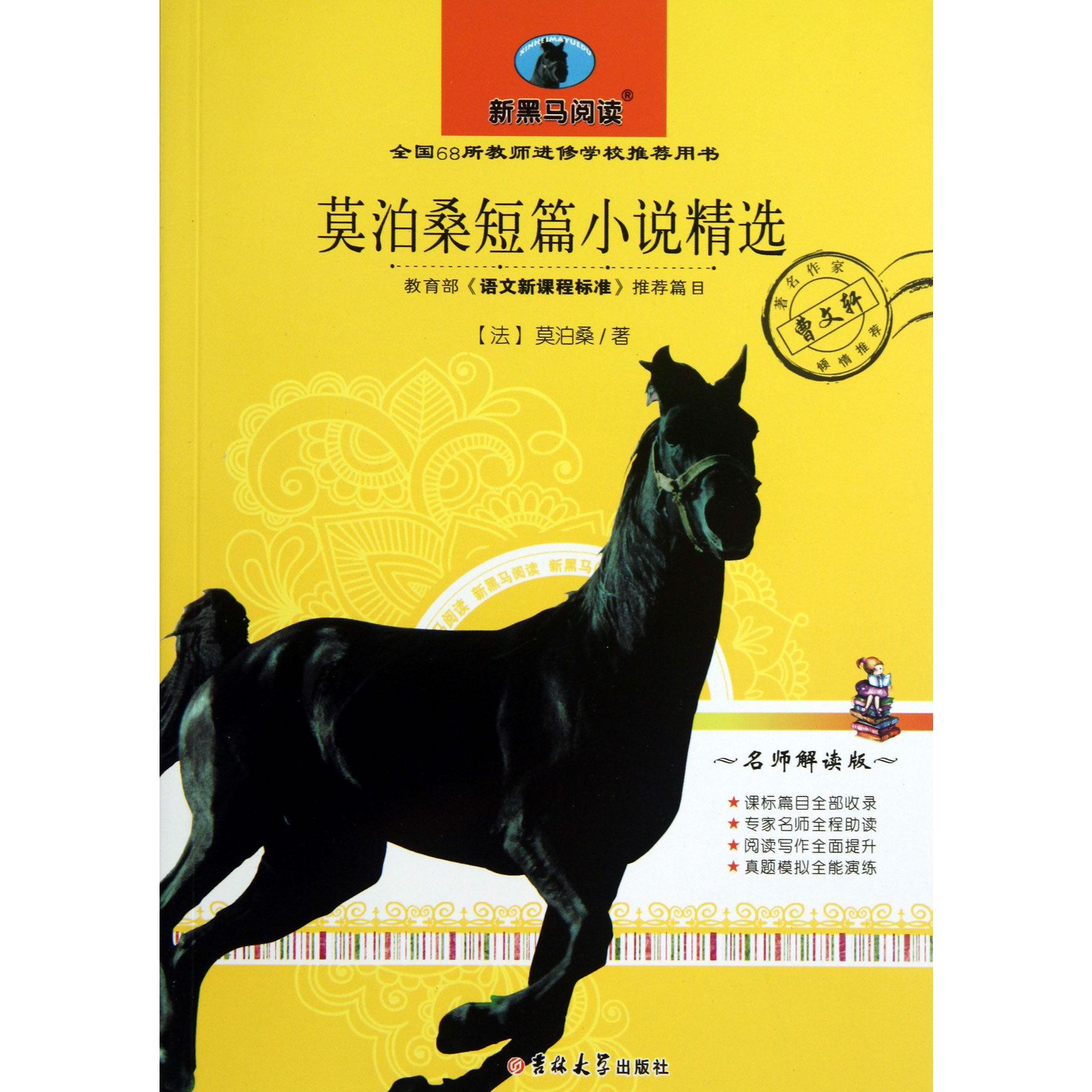
出版社: 吉林大学
原售价: 18.80
折扣价: 15.10
折扣购买: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名师解读版)/新黑马阅读
ISBN: 9787560199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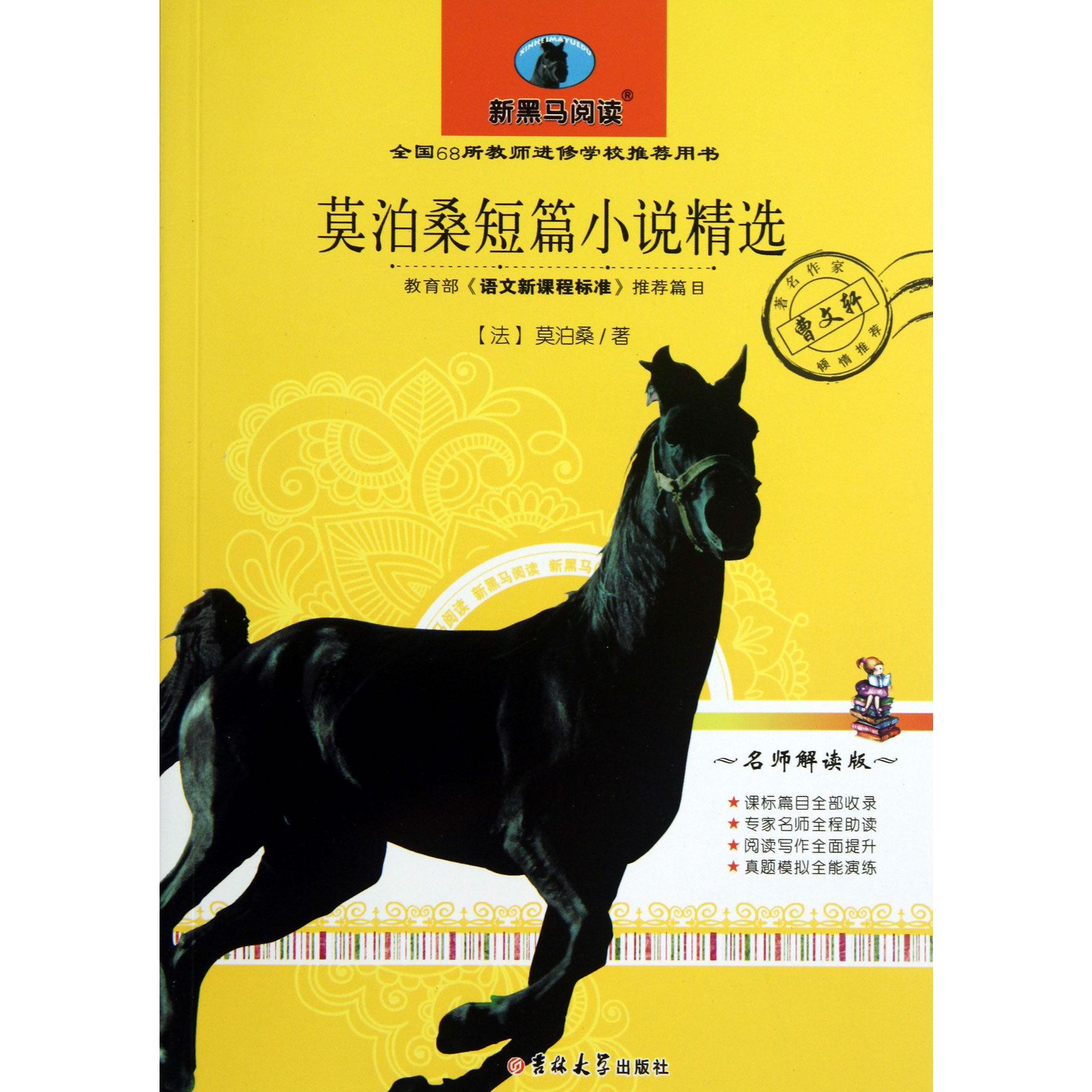
羊脂球 接连好几天,溃败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 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 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 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 的制服, 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 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 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 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 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 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 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 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 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 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 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 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 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 ;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 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 亮晶晶钢盔的轻骑兵,他拖着 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 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 “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 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 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 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 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 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 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 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是靠了他们这 群大言不惭 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 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 些亡命之徒,勇猛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 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 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 枪打死自己的哨兵;即使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 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可 是现在他们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 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到奥特玛桥 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 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将, 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竞遭遇了这 样的大溃败,英勇昭著的民族 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 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沉闷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 悄悄的惊慌不安的等待状态。 许多做生意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 待着战胜者,他们战 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 烤肉的铁钎或厨下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 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 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点 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 几个轻骑兵,很快地穿城而 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 来了黑乎乎一大片人,同时在 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 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 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 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 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步伐沉重且整齐。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 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②的口 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 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 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是财产和生 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 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 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 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 因为,每逢事物的IH秩序遭遇 毁灭,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 的一切东西都得听凭一种凶残 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 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 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 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 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 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 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祗( 地神)表示谢意;所有 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 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 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 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 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 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 _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 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 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 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 ,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 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 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 衍(做事不负责或待人不肯切,只做表面上的应付) 好了,也许可以少负 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 ,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 办的话,也无非显得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 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 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 卫城池的时代了。①最后他们又 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 由,那就是只要不在公共场所 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是被允许的 。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 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说说笑笑,而住在 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 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一 慢慢地城市本身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 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 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 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 在街上走来走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 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 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种难于捉摸的 、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 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 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 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种 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 做客的感觉。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