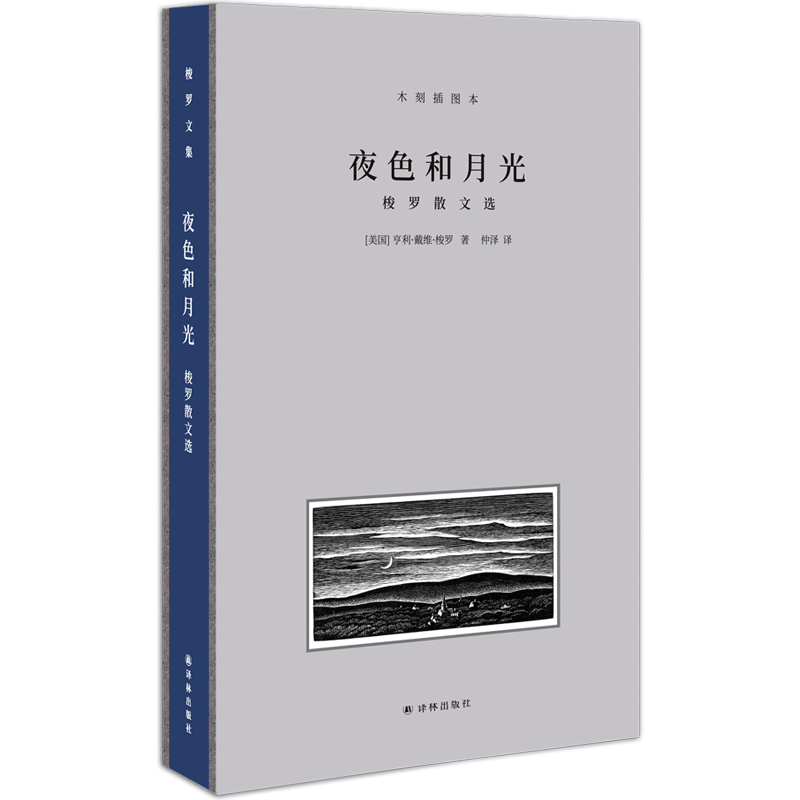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46.50
折扣购买: 梭罗文集·夜色和月光:梭罗散文选(木刻插图本)
ISBN: 9787544772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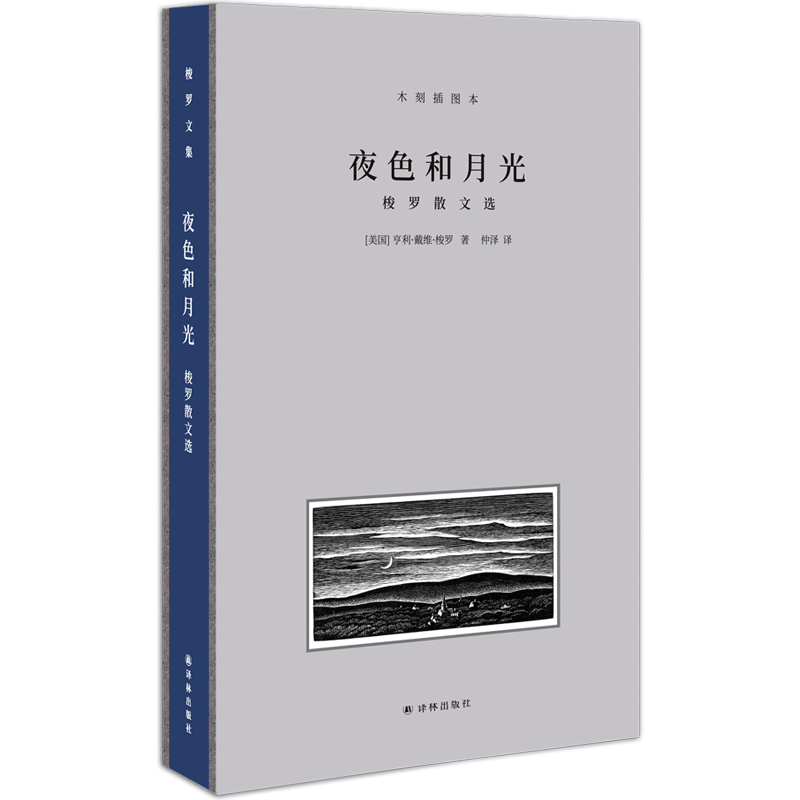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哲学家。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1843年后转为写作。曾协助爱默生编辑评论季刊《日晷》,一生支持废奴运动。他选择了心灵的自由和闲适,强调亲近自然,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提倡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著作包括《瓦尔登湖》《非暴力抵制》《河上一周》等。 仲泽,甘肃武威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从事语言教学研究及翻译。译有梭罗作品《瓦尔登湖》《四季之歌》《夜色和月光》,正在进行英国古典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译工作。
野苹果 苹果树的历史 苹果树跟人类的历史联系居然如此紧密,真让人不可思议。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包括苹果、真禾本科与唇形科(即薄荷科)在内的蔷薇目植物,出现于地球的时间比人类早不了多少。 近期在瑞士的湖底发现了早期人类的遗迹,据推测,他们的活动时间比罗马建城还早,因为他们连金属工具都没有掌握。他们的窖藏中有一枚完好无损、干瘪发黑的沙果,可见这些人的食物中似乎就有苹果。 塔西佗提到古日耳曼人的时候说,他们充饥的食物里就有野苹果(agrestia poma)。 尼布尔发现,“有关农耕与和平生活的词汇,诸如房屋、田地、耕犁、耕作、果酒、油料、牛奶、绵羊、苹果等等,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完全一致,而拉丁语跟战争或猎捕相关的词汇却跟希腊语判然不同”。因此,以苹果树为和平的象征应该毫不亚于橄榄枝。 苹果很早就相当重要,并且分布很广,所以,追溯其语源可以发现,它在好多语言里通常都表示果实。比如,希腊词语Μη?λον除了指苹果,也兼指其他水果,此外它还表示牛羊这类家畜,而最终又成了财富的统称。 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歌颂过苹果树。有人认为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就曾受到苹果的诱惑。在神话里,女神争抢过苹果,巨龙曾应命守护,勇士则受雇采摘。 《旧约》至少有三个地方提到苹果树,提到苹果的地方也有两三处。所罗门唱道:“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再如,“给我葡萄予我力量,给我苹果畅快我心。”人类最尊贵器官的最尊贵部分也因苹果而得名:眼中的苹果。 荷马跟希罗多德也曾提到苹果树,在阿尔喀诺俄斯的美丽果园里,尤利西斯就看到“诱人的梨子、石榴和苹果(ai mhleai aglaokarpoi)挂在枝头”。据荷马所述,苹果也是坦塔罗斯摘不到的果子,他只要伸手过去,风就会把树枝吹向别处。泰奥弗拉斯特知道苹果树并像植物学家那样做过描述。 据《埃达》所述,“伊丢娜在箱子里替诸神存了若干苹果,一旦感到暮年将至,他们只需尝上一口便可以重返韶华,这样,在拉戈纳罗(诸神的毁灭)来临之前就能永葆青春”。 我在劳登的作品中读到,“古威尔士诗人赛歌取胜便会获赐苹果嫩枝作为奖励”,而“苏格兰高地的拉蒙特家族则以苹果树作为族徽图案”。 苹果树(Pyrus malus)主要分布在北温带。劳登说,“苹果树天然分布在欧洲除寒带以外的所有地区,而在西亚、中国和日本也广泛分布”。我们北美也有两三种本土的品种,培植的品种则由最早的那批移民引入,人们觉得它在这里不比别处差,甚至还要更好。现在种植的好些品种可能是由罗马人最先引入英国的。 普林尼袭用了泰奥弗拉斯特的树种分类,他说,“有些树木完全野生,有些则是栽培的结果”。泰氏将苹果树归为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树的人工培植程度确实最高。它温良如鸽子,漂亮似玫瑰,并且像牛羊那般重要。苹果的栽培历史最长,因此“人化”的程度也最高。谁能料到,它最终会像家犬那样无法追溯原生始祖?它随人搬迁,就像家犬和牛马。最初或许是从希腊到意大利,接着到英国,然后到了美洲。而我们西迁的运动还在稳步推进,搬迁者或是口袋里装着苹果种子,或是行李中裹着苹果幼苗。与往年的情况相比,今年至少又有数以百万的苹果树栽到了更西的地方。可以想见,芬芳的果花会像安息日那样,每年都在大草原上扩大地盘。因为人们搬家时,不仅会带上家禽、家畜、鸟虫、蔬菜,以及刀剑,也会把果园搬走。 很多家畜,比如牛马、绵羊和山羊,都喜欢吃苹果树叶子和嫩枝,而猪和牛还喜欢吃果子,所以,从一开始,苹果树就跟这些动物存在天然的联系。“法国树林里的沙果”据说是“野猪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欢迎苹果树移植到美洲的不只是印第安人,还有昆虫、鸟雀和走兽。苹果树的嫩枝刚刚发芽,天幕毛虫就会在上面产卵,从此便开始跟洋樱桃分享来自果树的呵护,大批的尺蠖也放弃了榆树来这里觅食。因为苹果树长得很快,蓝知更鸟、知更鸟、雪松太平鸟和食蜂鹟便迫不及待地前来筑巢,蹲在枝干上唱歌,于是成了果园之鸟,并且数量激增,前所未有。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就属于它们。山上的啄木鸟发现树皮下藏着美味,所以会绕着树干啄上一圈方始离去,据我所知,此前它从来不会有这种举动。山鹑也很快发现苹果树嫩芽极其可口,所以秋末冬初就从树林里飞来采食,后来成了习惯,延续至今而让农夫苦恼不堪。兔子尝到嫩枝和树皮的滋味也不算晚。一旦果子成熟,松鼠会连滚带搬地运进洞里。连麝鼠也会在夜晚摸上岸来饱餐一顿,频频来去,最后在草皮上留下了一条小路。等到冻苹果消解后,乌鸦和松鸦偶尔会来享受一番。猫头鹰摸进了第一棵长空的果树,兴奋得大呼小叫,因为它发现那是供它专享的空间。从此在那里安身,再也没有换过地方。 尽管本文的主题是野苹果,但我打算先将培植苹果每年生长的各个时段扫上一眼,然后言归正传。 苹果花可能是最美的树花,花团锦簇又芬芳馥郁。果花绽放到三分之二更是美丽无比,常常惹得路人频频回顾,流连徘徊,不忍离去。相较之下,梨花就大为逊色,它既无悦目的色彩,又少怡人的芳香。 到了七月中旬,青苹果已经很大,让人担心它会随时掉下而需要呵护,也提醒我们秋天行将来临。树下的草地上常常会有尚未成熟就掉落的小小青果,大自然好像在替我们裁汰挑选。罗马作家帕拉狄乌斯说,“如果苹果尚未成熟就要掉落,在根部的枝丫上放块石头便能起预防作用”。类似的观念至今还有市场,所以,当我们看到果树枝丫上越来越多的石头,或许就能明白原因所在。英国的萨福克有这么一句农谚: 米迦勒节前后, 半个苹果熟透。 早在八月一日左右,苹果就开始成熟,不过我觉得,这时候有些果子很好闻,却没有一个好吃。一枚果子就能让手帕余香悠悠,这种效果店里售卖的任何香水都无法比拟。有些苹果芬芳馥郁,兼有花香,让人难忘。我在路上捡到过几枚糙皮苹果,其味沁人心脾,让我想起了果神的所有财富,思绪不觉飘到果园,飘进酒坊,那里小山累累,满眼鲜红,一片金黄。 一两个星期后,当你走过果园或花园,尤其在夜晚,成熟苹果弥漫的香气就会把你包围,你可以尽情享受而无需付费,也不会让任何人蒙受损失。 所有的天然产品都有某种飘忽迷离、稍纵即逝的魅力,那正是它们的无上价值,跟尘俗无缘,休想买进卖出。凡夫无缘享受果实的天香,只有圣人才能品尝这种美味。因为精纯的香气是人间果品唯一可取的品质,而我们呆笨的腭叶却无法消受,正如我们占据了诸神的天国而浑然不觉。某些无比卑琐的人会满载一车早熟苹果的美丽和芳香前往市场,我看到这一情境,眼前总会出现较劲的场面,一边是那人和他的马匹,一边是车上的苹果。在我看来,获胜的总是苹果。普林尼说,苹果是最沉的东西,满载苹果的车子只消让牛来上一眼就会冒汗。天地间最美的地方才与苹果般配,绝不能将它送到并不相宜的地方,车夫只要萌生此念,当刻就会蒙受整车的损失。虽然他会屡屡下车,不停地摸摸,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但我看到那飘渺纤弱的美质逸出了车子,飘进了邈远的天国,而送往市场的仅仅是些果肉、果皮和果核。那不是苹果,那是果渣。难道那还是伊丢娜的存储,那只需一口就能让诸神永葆青春的果子?你且想想,他们在皱纹满面、鬓发苍苍之时,难道会让洛基和特亚西将这东西抢到约坦海姆那里?不,当然不会,因为拉戈纳罗,即诸神的毁灭,尚未降临。 大自然还要来一次精选,通常是在八月底或九月,这时地上到处是风吹落的果子,这种情况在雨后疾风发作时尤其明显。如果是在果园,四分之三的苹果都会落地,树干四周就会铺满硬硬的青果,如果树在山坡,则会远远地滚到山下。不过,凡事皆有利弊,风刮得再不合时宜,也未必一无是处。这时候,到处都有人在捡拾吹落的果子,这样,早早地做苹果饼就不会成本过高。 到了十月,苹果树开始落叶,树上的果子分外醒目。记得有一年,附近镇子上有些树缀满果实,状况之盛,前所未见。小小的苹果悬在大路上方,一片金黄,树枝沉沉垂下,姿态优雅,像是丛聚的小檗,让整棵树气象一新。向上看去,就连最高的枝条也不再挺立,或是斜逸侧出,或是弯下腰身,下面的枝条则撑了好多杆子,像是画中的榕树。正如一部英国古书所言,“树上果子越多,越会向人弯腰致意”。 在果实的世界,苹果绝对尊贵无比。就让最卓越最睿智的人拥有它吧,这才是苹果的“时”价。 十月五日到二十日之间,树下会摆满下果的桶子。我看到有人为了一份订单在精挑细选,于是便在想象中跟他交谈一番。他拿起一枚有疤的果子反复摩挲,然后丢到一边。如果要我谈自己心里的想法,我就会说,果子只要经他摩挲便会生疤,因为他擦去了果霜,那飘渺纤弱的美质便不复存在。夜晚天气清凉,农夫在抓紧时间干活,果园里只剩梯子靠在树上,随处可见。 如果我们满怀欣悦又心存感激地接受这些馈赠,同时也不觉得给果树培上一车粪土就算完事,这种表现就相当合适。至少某些英国古俗值得借鉴,这些信息大多载于布兰德的《古风》,主要做法为:“圣诞前夕,德文郡的农夫会同家人盛上一大碗果酒,其中浸有面包,然后非常庄重地端进果园。他们会通过多种仪式向致谢,希求它来年丰产。”这些仪式包括“给树根泼上果酒,给树枝献上小块面包”,然后“围在园子里最丰产的树边,祝酒致辞,三巡而毕”: 向你致敬,我的苹果树, 愿你发芽,愿你开花, 愿你多多把果挂! 帽子装满,头巾装满! 蒲式耳装满,再装满,麻袋装满! 我的口袋,也装满!哈啦! 英国好多郡县在元旦前夕都要举行所谓“苹果吼”的活动,一群孩子会来到各式各样的果园,围在果树边,反复吼叫: 牢扎根,多结果! 老天给我们大收获: 所有小枝苹果大, 所有大枝苹果多! “他们齐声呐喊,由一个孩子吹牛角应和。其间他们会拿棍子敲打树干。”他们将此举称作为苹果“祝酒”,有人认为这是“野蛮人为果神献祭的遗风”。 赫里克如此吟咏: 向果树祈求,向果树祝酒, 但愿李子和梨子如愿而收。 因为,只要你有这种祈愿, 它多少会叫你如愿所求。 今天,我们的诗人不但要为葡萄酒吟咏,更有理由因苹果酒放歌。但是,他们理应唱得比英国人feilipu 斯更加优美动听,要不,他们的缪斯就会因之蒙羞。 野苹果 人工培植的苹果树(urbaniores,如普林尼所称)就说到这里。一年四季任何时候,我更乐意去未经嫁接的老苹果园里走上一会儿。这里的树栽得极不规则,不时会有两棵树靠得很近,园子里也几乎没有行列可言,让人不由觉得它们生长的时候主人在睡觉,而且栽植的时候此人也在梦游。我喜欢来这里徜徉,嫁接的果园整齐划一,我丝毫提不起兴趣。但是,多么可惜,它们早已蒙受蹂躏!此刻我在据记忆讲述,并非凭新近的体会而论! 在有些土里,比如我们周边一个叫伊斯特布鲁克乡的地方,那一带是大片砂土,果树无需任何照料也会长得更好,或者,如果栽到那种每年只翻一次的土里,也比精耕细作的地方长得要好。业主承认,那种土质确实最适合果树生长,但因为土中石头太多,他们实在没有耐心开垦,加之离得太远,所以一直没有经营。那里有个毁掉不久的园子,面积很大,树木长得杂乱无序。不,那压根就不算什么园子,有松树、桦树、枫树和橡树,果树野生其间,果实繁多。我常常惊喜地发现苹果树浑圆的树冠从林子里冒出,缀满了鲜红或金黄的果子,流光溢彩,跟林中秋色相映成趣。 十一月一日,攀上一处悬崖后,我看到了一棵小苹果树。它为鸟雀或黄牛所种,蹿出林际与岩间,茁壮挺拔。这时栽植的苹果已经收完,这棵树上却果实累累,没有遭霜。这棵野树生机蓬勃,依然绿叶满枝,密密实实,好似荆棘。树上的果子坚硬青翠,在冬日却是秀色诱人的美味。有些果子悬在细嫩的枝头,多半或埋在树下湿漉漉的叶子里面,或远远地滚在山下的岩石之间。这块地的主人对此却一无所知。除了山雀,没人知道它何时绽开了第一朵花蕾,也没人知道它何时结上了第一枚青果。树下的草地上不曾有献给它的舞蹈,此时也无人摘取它的果实(我发现只有松鼠会前来品尝)。这棵树有两重任务:结出自己的果实,也让每一条嫩枝向空中伸出一英尺。且看这果子,显然比不少浆果大出好多,如果带回家里,在次年春天依旧会完好如初,鲜美可口。有它在手,我会在乎什么伊丢娜的苹果? 当我行经这棵深冬犹荣、坚韧耐寒的小树,看到挂在枝头的果子时,我不由心生敬意,尽管无法品尝这美味,却也对上苍的慷慨馈赠满怀感激。就在这草木丛生、坎坷崎岖的山边,却有这么一株果树,不曾有人种植,也看不出有过果园的痕迹,它完全野生,如同松树与橡树。可是,我们赞美并食用的好多果实,却完全离不开我们的照料看护。诸如五谷、杂粮、土豆、桃子,以及甜瓜等等,完全由人种植,而果树却在跟人类的自立能力和进取精神争胜抗衡。如我先前所言,它不仅仅被动地为人类移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人类一样,主动迁徙到了这块新大陆,甚至所到之处,都会在周围的原生树木中拼出一条生路,好似某些走失的牛马和犬只完全依靠自我维持。 有一种苹果生在环境无比恶劣的地方,味道极酸,刺激口舌,即便是它,也在印证如是观念:苹果,如此高贵。 沙 果 然而,这里的野苹果仅仅如我一般具有野性。它并非本地的土生品种,却经由嫁接而混入了林木世界。我曾提到更有野性的苹果,那就是沙果(Malus coronaria)。它长在本国其他地方,土生土长,野性如初,“不曾因栽培而改变天性”。从纽约以西到明尼苏达,以及南边的地方,都能发现它的身影。米肖说它一般高达“十五至十八英尺,个别会在二十五到三十英尺之间”,而大树则“跟常见的苹果树相似无异”。“其花白里透红,为伞状花序”,因芬芳迷人而知名。据米肖说,沙果直径约一英寸半,奇酸无比,却能做精品蜜饯,也可以酿酒。他最后说,“即使栽植,沙果依然如故,不会成为什么美味,但至少因为花色娇艳,花香芬芳而招人喜爱”。 一八六一年五月之前我从未见过沙果,只是通过米肖的描述有所耳闻,但是,据我所知,当代植物学家却认为它无足轻重,所以,我对这种树木的了解限于道听途说。我曾谋划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葛莱兹朝圣,据说那里的沙果堪称完美。我也曾打算前往苗圃探个究竟,但又拿不准那里是否有这种树,或者,即便有也可能跟欧洲的品种混在一起。我最终得间前往明尼苏达,火车刚进密执安,我就发现窗外有一种树,色如玫瑰,相当漂亮。我起初认为那是一种荆棘,然而很快就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我心仪既久的沙果树?当时大概五月中旬,窗外望去,这种灌木,或曰树木,鲜花怒放,芬芳满枝。但是火车根本不曾在树前停下,我被送到了密西西比的腹地而无缘碰它一下,算是体验了一番坦塔罗斯的命运。到圣安东尼瀑布后,我无比遗憾,因为得知此地已距沙果北去甚遥。不过,我最终在瀑布以西大约八英里之处如愿以偿,亲手抚摸并享受芳香,还采得一朵作为标本。这里肯定接近它生长的北限了。 野苹果如何生长 尽管沙果跟印第安人一样属于土生品类,然而,跟苹果树中的那些边鄙蛮民相比,它是否更加坚韧强毅却不好说。那些树虽然也有栽培的前身,却长在辽远的森林和荒野,那里的土地更适合它们。我不知道跟它们相比,还有什么树会面临更多的挑战,要更为刚健地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说一说它们的际遇,情况通常如此: 五月将至,就像在我们伊斯特布鲁克乡的砂地,或者在萨德伯里的纳波斯科特山顶一样,牛群早已在草场上显身,但见一丛丛小小的果苗在草地上刚刚破土。开始,或许有那么一两株会逃过干旱和其他变故,并且因为长对了地方,也会免于野草的侵凌及其他风险。 两年过去,它已经 长得跟岩石齐平, 但愿世界日渐辽阔, 又何惧头顶的飞禽。 尽管它年纪轻轻, 然而苦难却已逼近。 走来一头吃草的公牛, 啃去了一拃之长的幼茎。 公牛这次可能没有看到草里的果苗,但是,等来年果苗长得粗壮,它便会认出这位从故乡迁来的同伴,那叶子和嫩枝的味道它再熟悉不过。它迟疑片刻以示欢迎,惊讶之余,知道了根由:“你来这里的原因跟我一样”,虽然如此,它或许想起自己曾有的某种权力,于是又来了一口。 出头的幼芽每年都被这样啃去,可它并不灰心,反倒在断茎上冒出两条小枝,贴着地皮在坑洼或岩石罅隙中伸展。这样,它长得越发茁壮,越发葱茏,虽然最终长不成树身,却如一丛锥形灌木,硬挺、茂密,几乎像岩石那样牢实坚硬。就经见所及,这是最密最牢的灌木丛,因为棘刺遍布,更兼枝条浓密硬挺,所以最终成了低矮的野苹果树丛。它们颇似低矮的冷杉和云杉,你有时会踩踏而过,有时会穿行其间,由于长在山顶,寒冷的气候成了它们最大的敌人。难怪它们最终长出棘刺,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跟强敌斗争。不过,这些棘刺无毒,仅仅微有果酸。 前文提到的那块砂土草场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这种树丛(它们在多石的地上长得最好),让人想起坚硬的灰色苔藓或者地衣,其间数千小树挺身而出,上面还挑着种子。 树丛四周每年都会被牛定期修剪一番,好似大剪刀打理过的树篱,常常呈为规则的锥状或金字塔形,高在一到四英尺之间,几乎都有锥尖,好似园丁的手笔。在纳波斯科特山间草场及尖坡之上,每逢太阳西斜,它们就会投下优美的阴影。好多小鸟在其间筑巢栖息,因而觅得躲避老鹰的理想去处。夜间,群鸟都会来这里栖身。有个树丛直径六英尺,我发现里面有三个知更鸟的窝。 若从种子入土之日算起,它们毫无疑问算是老树,若考虑生长状况和来日尚多的前景,则它们还算幼株。有几株高仅一尺,宽亦同此,数过年轮后得知树龄约为十二年,却茁壮挺拔,生机蓬勃!它们很低,甚至到了被行人忽视的地步,而它们的园中同类却早已挂上了硕大的果实。不过,生在园中可谓得之时而失之力,亦即,丧失了树木的元气。这就是它们金字塔式的生长情况。 牛还会这样啃上二十年甚至更久,致使树丛很低,只好横向生长,最后长得很宽而成了自己的一道围篱。如此一来,里边的幼芽便使敌人可望难及,由于它依旧铭记高处的召唤,因而满怀欢欣地向上猛长,并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而最终获胜。 它最终击败呆笨对手的策略如上所述。如果目睹了某一植株的生长过程,现在你就会明白,那简单的锥状或塔形外观不会保持多久,锥尖上将会长出一两根嫩枝,可能比在果园里长得还要滋润,因为植株已将遭到压抑的所有能量都释放在了顶端。这些嫩枝不久便会长成小树,于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就会出现在原有金字塔的顶部,整棵树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漏。下方横铺的基座既已完成使命,所以会最终消失。牛群至此无法施害,因此获允靠近,在树荫里纳凉,在树干上蹭痒,让红色的牛毛沾上一度遭它威胁的树干,乃至尝上几口果实,当然,也会替它传播种子。 牛群借此为自己创造了树荫和食物,而果树,也似乎因为沙漏倒置,随着时光倒流而获得了新生。 今天,好多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果树该修剪得跟鼻子齐平,还是跟双眼等高?牛的修剪止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我想,这应该是恰当的标准。 这种灌木毫不起眼,唯一的垂青来自小鸟,因为这是躲避老鹰的庇身之所。它们虽然面对往复不已的牛群,虽然身处逆境,但终究拥有自己的花期,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收成,尽管所获有限,却也实实在在。 我在观察树丛中央的那些枝条时想,它们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忘了自己的使命。于是,十月将终,它们叶子落尽的时候,我便屡屡前往查看。但见枝头挂着第一批收成,小巧的果子或为翠绿,或呈金黄,或是显出玫瑰的光色,因密实多刺的围篱阻隔而没有被牛群掠去,我便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这无可名状的全新品种。我们都听说凡·蒙斯和奈特培育了为数不少的水果品种,眼前的培育方法却属于凡·母牛,它创造的品种不但远较两人为多,也让人格外难以忘怀。 历经多少艰辛它才能培育出这枚香醇的果子!这种野果虽然略小,但是,若论滋味,纵使不比园中的果子好吃,至少也跟它不相上下;若虑及它经历的磨难,这小小的果子自然更加香甜,更加甘美。这枚野果由母牛和鸟雀偶然所植,生于砂石遍布而不为人知的荒远山坡,谁又敢说它不会成为果中极品,不会传进域外君王的耳朵,不会让皇家学会为了推广而四处寻访,而粗鄙卑下的砂地主人尽管不为人知,其名声却不会借以越出他那个小镇?鲍特和鲍尔温这两种果子就经历了这种培育过程。 所以,每一丛野果树都会让我们心怀缅想,这多少有点野孩子激起我们期待的意味。它或许就是一位乔装的王子。人类何尝不然?秉受生命的极致,意欲成就仙品,却为命运所噬。多么惨痛的教训!唯有坚忍不拔、强悍无比的天才才能保全自我,获得成功,最终向天空伸出一条嫩枝,而后让精美的果子落向忘恩负义的大地。诗人、圣哲和政治家也是如此,他们从乡间的草野奋身而起,卓尔不群,赢得美名。 求知之道亦复如此。所有仙果,金苹果园中的那些果子,永远都由不曾入睡的百头之龙看护,因此,付出赫拉克勒斯的艰辛方能采摘到手。 这是野苹果的一条衍生之道,也是最为卓越的一种方式,不过,它通常在林间和沼泽的宽敞空地,以及大路的两旁破土,而且长得更快,因为那里的泥土于它更为相宜。它若生在密林,则会又细又高,我常常能从这些树上采得味道极淡的果子。诚如帕拉狄乌斯所说,“Et injussu consternitur ubere mali”:果树不为所喜,因而烂果满地。 人们认为,假如这些野树结不了好吃的果子,就可以充作理想的砧木,如此,其他水果的精纯品质就能借以传之子孙。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不过,我无意寻找砧木,我找的就是野苹果本身,它那尖利的气味容不得任何“改良”。 培植香柠檬 非我意中求 果实及风味 野苹果的节令在十月和十一月之交,这时的果子才鲜美可口,因为它们成熟得较晚,这个时候恐怕仍旧美丽如常。我对这些果子尤为珍视,农夫却认为不值得采集。这是缪斯的野味,活泼奔腾,让人激动。农夫觉得他桶里的才是好东西,但他错了,如果他有行人的胃口和期望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 这是纯天然的果子,可在十一月一日前都没人理会,我想可能是主人无意采摘的缘故。它属于跟自己一样野性未泯的孩童(那些我认识的活跃孩子);属于身在野外、眼神粗野的妇人,她在全世界拾荒,任何东西在她眼中都没有缺陷;此外,它还属于我们行人,途中相遇便归所有。这是行使既久的权利,在好多古朴的乡村已经沉淀为习俗,果子知道在这里该怎么生长。我听说“一种叫戈兰搏的风俗,这种风俗或许也可以称作‘捡苹果’,在今天或昔日的赫里福郡颇为流行。正式的采集结束后,会给孩子们在每棵树上留几枚果子,这些果子就叫戈兰搏,由他们带着爬杆和口袋去摘”。 还在我小的时候,有些树就行将死去,不过直到现在依旧活着。主人不抱什么指望,已将它们扔掉,因此懒得去树下看看,只有啄木鸟和松鼠会前来光顾。它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果树,在我眼中,我来这里采摘的是野果。从稍远的地方看去,树上除了挂满地衣别无所有,可是,你若心存期望则必然会得到报偿,因为树下就有鲜美的果子。有些果子留有松鼠的齿痕,它可能是想搬进洞里,有些里面有一两只蟋蟀在悄悄地享用,而有些里面则是没有壳儿的蜗牛,碰上阴湿的天气更是如此。树上依旧垒放着棍棒和石头,你会明白这里的果子有多香醇,人们当年对它是何等地热衷。 我在《美洲水果和果树志》里没有看到对这种果子的交代,然而,与嫁接的果品相比,它更是我的钟爱。经过十月和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到次年一月,甚至二月到三月,它的味道略有缓和,却依旧不失鲜活泼辣的美洲风味。邻家一位老农的说法总是恰如其分:这种果子味道特别,爽利如箭。 用以嫁接的苹果常因其味绵甜,个头甚大,产果丰足而选,非因味道爽烈而取,人们看重的是精纯不二的美质,而非一无瑕疵的漂亮。我对栽培专家遴选的名录实在没有信心。所谓“精品”、“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品种,我经栽植后发现,其味寡淡无比,让人意趣索然。这种果子吃起来毫无感觉,没有那种正宗的烈性和劲道。 如果某些野果味道刺鼻,让人皱眉,难道不因为它们仍旧属于对人类温情满怀、一腔赤忱的果神?将它们送往酒坊更让我愤愤不平,它们或许尚未彻底成熟。 难怪人们觉得上品果酒该用色彩浓艳的小苹果加工。劳登援引《赫里福德郡公报》说“:在品质相当的情况下,小苹果比大苹果更得青睐,因为果皮和果核占的比重更大,而它们恰好可以提供最甜的果汁。”他接着说:“赫里福德的西蒙兹博士为了验证此说,大概在一八〇〇年酿了两大桶酒,一种完全用果皮跟果核,另一种只用果肉,结果证明前者异常爽烈强劲,后者却绵甜平淡。” 伊夫林说“红斑苹果”在他们那时是酿酒的首选,他引用某位纽伯格博士的话:“我听说在泽西流传这种说法,果皮越红,越适合酿酒,酿酒桶里的白皮苹果都会被剔除。”这种看法至今盛行。 所有的苹果到了十一月都会很好。有些果子会因为在市场滞销或买主觉得味道欠佳而被农夫冷落,对行人而言,那却是果中珍品。有些野苹果在野外或林中吃来,真可谓爽口带劲,可是,一旦带回家里,味道往往酸涩不堪。漫游者的苹果连他本人都不会在家里享用。上颚在家里会拒绝这种东西,正如它会排斥山楂和橡子,因为在这里它需要平和的感觉。究其原因,乃是家里少了十一月的空气,它恰好是享用野果的佐料。所以说,提蒂卢斯看到日影西斜,邀请麦里布斯到家做客时,曾许以绵甜的苹果和嫩嫩的栗子,mitia poma, castaneoe molles。我常常采摘野苹果,其味泼辣强劲,我不禁想,园艺师都不会从这种树上选取嫩枝,不过我却没有忘了装满口袋回家。然而,我从桌子里拿出一枚到卧室品尝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味道竟然浓烈无比—酸得足以使松鼠倒牙而让松鸦失声。 这些果子挂在风霜雨雪之中,最后都吸收了时令与节候的气息,经过这样充分调制后,它那股劲道就会激刺唇舌,螫痛口腔,灼烧喉咙。因此,它们只能在合适的场合,也就是户外食用。 这些十月之果野性十足,味道强劲,要想领略个中滋味,就得呼吸十月或十一月的凛冽空气。户外的空气和行动会给漫步者的上颚赋予特殊的敏感,使他希求深居简出者谓为尖利酸涩的水果。这些果子非得在旷野品尝不可,这时全身因户外活动而生气勃发,手指被风霜冻木,枯枝败叶在寒风中瑟瑟作响,松鸦在四周凄厉地啼鸣。旷野漫步让人心旷神怡,它会将室内的尖酸点化为甘甜。这些苹果该贴上标识:随风品用。 果实的任何风味皆非多余,都为不同的嗜好而备。某些苹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或许一半须在室内享受,而另一半必得户外食用。一七八二年,某位叫彼得·惠特尼的人在诺斯伯勒为《波士顿学会公报》撰文,他说该地有棵果树会“结截然相反的果子,同一个苹果往往一半酸而一半甜”,或者有些苹果酸,而有些苹果甜,整棵树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镇里的纳肖图科特山上有一棵野果树,它为我提供了无比怡悦的粗犷美味,吃完大半个果子才能领略。那种气味会留在舌尖。咬上一口,就有一股活似缘蝽的气味。品赏这种美味让人觉得很有成就。 我听说普罗旺斯有种李子“称作Prunes sibarelles,因其味极酸,吃后无法吹口哨而得名”。所以如此,恐怕是只在夏日并且室内食用的缘故,不妨在天气恶劣的户外试试,说不定哨音会提高八度,而且格外清亮高亢。 大自然的尖利酸涩唯有身处旷野才能欣赏,恰似樵夫的饭食在阳光和暖的林间空地上吃得最香。时届隆冬,沐浴着正午的阳光,他心满意足地缅想着夏日,而身外的酷寒却会让室内的学生悲戚哀叹。户外干活的人不会觉得冷,感到冷的反倒是那些在室内坐着瑟缩发抖的人。气温如此,气味同理;冷暖如此,酸甜亦然。上颚残障的人会排斥尖利酸涩的气味,而这种天然的活跃因子恰恰是真正的佐料。 将你的佐料存于感官之中。领略野苹果的风味需要强健的官能,让上颚和舌头的突触牢牢地挺耸,不要让它轻易倒伏而萎靡迟钝。 因为对野苹果的如许认识和体会,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好多为文明人所排斥的食品却能得到野蛮人的钟情。野蛮人有户外活动者的上颚,品味野果恰好需要野蛮,或者野性的趣味。 品味生命之果,领略世界之最,又需要何等健康的户外胃口! 好多苹果非我所愿 就算世人交口称赞 长命的果子也不例外 红润的格林尼亦非所盼 伊甸园中的那枚又复如何 女神争抢的金果亦属枉然 不!都不要! 我要的果子系在生命的藤蔓 所以,人在野外是一种想法,在室内又会是另一种感受。但愿我的思想如同野苹果那样成为漫步者的食粮,至于室内品尝是否爽口,我却无从保证。 野苹果之美 几乎所有的野苹果都体面大方,就算节瘤蔽体,锈斑覆身,而使本色漫灭难辨,也不会到不足一观的程度。纵使节瘤遍布,也能为双眼提供某种补偿,你会发现结疤和坑凹里腾跃闪烁着西天的霞彩。夏日若不在它的面颊上留下彩带或花斑,就几乎不容它继续前行。它只要目睹晨曦和晚霞,就会染上红斑以为存照。若是日光隐辉,大雾绵绵,而或空气酝酿着霉变,它的记忆里就会烙下晦暗的锈色疹斑。宽阔的绿色空间辉映着大地的基色,有时甚至翠若绿原,而那些意味着平和风味的黄色板块,若非灿似丰收,则应褐如山峦。 这些苹果,就是我所说的这种苹果,美得难以言状。它是浑然天成的康科德美味,而非杂乱无序的“敌克德”之果。美丽如许,却在荒僻的地方随时可见,卑微的人群尽可以拥有。一经风霜点染,则美轮美奂,异彩纷呈。有的或橙比黄金,或艳似丹彩,或红若胭脂,好像在匀匀地转动脸颊,无所遗漏地接受太阳的光热;有的靥着桃花,微泛绯红;有的棕质褐章,条纹着身,浑若母牛,而那殷红的细线从花蒂这端流向果柄的酒窝,纤细悦目,匀称规则,宛若数千条子午线穿过麦秆蔽野的大地;有的着上微绿的锈斑,如同鲜亮的苔藓,一旦雨水浸身,则见血红的疹斑和洞眼融为一体,烧成了一团火焰;有的则为结疤所覆,在果柄近旁的空白处洒上猩红的亮点,好像那位妆扮秋叶的画师不小心甩出的油彩;还有的果肉泛红,被一重红晕抹成了仙果,美得让人不忍下口—金苹果园之珍,夕照成就的仙品!它若身卧湿漉漉的草丛便分外抢眼,若身处幽谷,在秋色浸染的山林,那枯叶间的亮色会格外醒目,好似海滨的贝壳和卵石。可是,一旦带进屋里便会干瘪委顿,光彩尽失,非复往昔。 取 名 上百种野苹果运进酒坊后聚成了一堆,替它们取个恰当的名字也足以怡情悦性。若不袭用人名而用日常辞藻,要想找到合适的名字,恐怕会让人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了。谁该充当替野苹果施洗命名的那位教父呢?日常辞藻会捉襟见肘,就算拉丁文和希腊文也难胜此任。看来我们只好求助日出、日落、彩虹、秋林、野花、樵夫、紫雀、松鼠、松鸦和蝴蝶,以及十一月的旅人和逃学的顽童了。 一八三六年,在伦敦园艺学会的果园里,名贵品种超过一千四百余种,我们眼前的这些品种却不见于这份名录,遑论由沙果培育的其他品种。 且容我列举几种。但我发现,为使不谙英语的人方便起见,我还是不得不采用拉丁学名,因为拉丁学名似乎已经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简要列举如下:木苹果(Malus sylvatica)、蓝鸦果、林中幽谷果(sylvestrivallis)、草场洼地果(campestrivallis)、废窖口果(Malus cellaris)、草场果、山鹑果、逃学果(cessatoris,孩子们上学路过非要对它动一下手脚,哪怕再迟也不管)、迷路果(迷走好久才能找到它的所在)、艳果(decus aёris)、十二月享用、解冻果(gelato-soluta,冻结消融后才好吃)、康科德果(可能就是Musketaquidensis)、阿萨布果、棕底深斑果、新英格兰之酒果、山雀果、青苹果(Malus viridis,这种果子叫法很多,尚未成熟时叫choleramorbifera aut dysenterifera, puerulis dilectissima)、阿塔兰特驻足所摘果、篱果(Malus sepium)、刺蛾果(limacea)、铁道果(可能因车厢里扔出的一枚果核而生),还有年轻时曾吃过的苹果,不见于任何名录的本地苹果,pedestrium solatium,挂有遗忘镰刀的苹果,此外有伊丢娜的苹果,洛基在林中发现的苹果,等等,还有好多见于我的名录但不烦枚举。所有这些野苹果都相当出色。波迪乌斯谈及苹果时曾经编引维吉尔,那我也要编引他的说法: 就算我多舌多口 嗓音清亮,也难以 列全野苹果的名目 拾 遗 到了十一月中旬,野苹果便不再那么光鲜,并且大部分都会落下。落地后,大多都会烂掉,完好无损则越发可口。在老树间漫步,山雀叫得更加清脆,秋日的蒲公英小伞半拢,毛絮飘飞。这时,人们以为野外的果子早已一颗不剩,但是,只要你是高手,就连栽植的那种苹果都会收拾满满一口袋。我知道沼泽里有一棵布鲁·皮尔曼果树,美得如同野生。切莫看上一眼就觉得那里一个果子都没有,你得顺着枝干寻找才行。有些果子掉在地上露在外面,这时就会颜色变黑而烂掉,但在潮湿的落叶中,偶尔却会露出几个鲜亮的脸颊。而且,我的双眼训练有素,不论是在越橘丛还是光秃秃的桤木间,而或在萎谢的莎草里还是岩石的缝隙中,我都有收获,甚至在地上厚厚的枯败蕨草里,我也能翻出东西来。因为我知道,苹果掉下后便会滚到低处,为树下的落叶所覆而藏身其中,打上了稳妥的包装。树下随处都有它们的藏身之所,被我揪出后,一个个湿漉漉地晶晶闪亮,可能被松鼠咬过,也可能被蟋蟀吃空,有时还沾着一两片树叶,好像修道院阴湿地窖中的柯曾古卷。但它们依旧光艳如初,至少因为已经熟透并且保藏完好,所以,纵然味道不及桶里的苹果,却也爽脆如常,口感极佳。如果这种地方空无一物,我就会在侧生大枝上密密麻麻的吸根间察看,因为不时就有一两颗住在里面,或者就在桤木丛中搜寻,因为它们为树叶所覆,路过的母牛无从发现。布鲁·皮尔曼果子我也接受,所以肚子饿了的时候,我就会装满两边的口袋。风霜前夜我会走出家门到四五英里之外访旧,为了保持左右平衡,一路上我会从两边的口袋交替取食。 格斯纳似乎对阿尔伯图斯服膺备至,我经由他的托普赛译本了解到刺猬搜集苹果并搬运到家的方法。他写道:“刺猬以苹果、虫子和葡萄为食。它在地上发现苹果或葡萄后,就会在上面打滚,待刺上戳满便带回家去,其间用嘴叼的也就不过一颗。如果在路上偶尔掉下一颗,它便会将身上剩下的全部抖落,再打一次滚,将它们全部载到身上。因此,它一路前行,会像车轮辚辚而过。洞里若有幼崽,就会从它的背上卸货,找喜欢的吃,而将剩下的存起来,留待来日享用。” 冻 果 将近十一月之末,有些品相完好的野苹果仍旧果汁饱满,也可能格外好吃,却常常会像树叶那样失去光彩而渐渐上冻。天气滴水成冰,农夫虑事周全,会把整桶的苹果搬进户内,同时也会为你奉上收获的苹果和酿制的果酒。窖藏的时候已经到了。少许野果可能会衬着初雪展示红颜,有些甚至整个冬天埋在雪里而容颜不改,完好如初。不过,它们常常会在入冬后冻硬,虽然不曾腐烂,但很快就会通身发黑,变成烤苹果的模样。 十二月尚未过去,冻果就开始消解。对文明人来说,一个月前,这些果子还酸涩不堪,无法忍受,可是,只要天气转暖,一经太阳解冻(它们对太阳极为敏感),果皮完好便有一包芳醇甘冽的果汁,胜过所知的任何瓶装果汁,较之熟悉的果酒我也了解更多。所有苹果经过这种变化都相当好吃,口腔就是榨汁机。有些则果汁不多,那些果肉却成了甘美异常的食品,我觉得比西印度一带进口的菠萝更加好吃。有些果子,不久前连我都因为咬了一口而为之后悔(因为那时我还处于半开化状态),农夫也任由它们留在树上不闻不问,但我现在欣然发现,它们也跟橡树嫩叶一样自有理由挂在枝头:如此一来,不用瓶子也可以保存果汁了。它们先由风霜冻结,硬得像石头,接着让雨水或温暖的冬日化解,这样,似乎便经由置身其中的空气而吸收了天国的芳馨。有时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它们会在口袋里磕磕碰碰,但是消解后,那冰花就会成为果汁。当然,经过三四番解冻消融,味道就会变得寡淡。 酷寒的北方成就了这些水果,跟它们相比,从灼热的南方进口的那些水果还算什么?我曾拿这些冻果哄骗朋友,“满脸诚意”地怂恿他吃。但现在我们都贪婪地装满了口袋,弯腰享用以免那溢出的汁液弄脏了衣襟,这种美酒让我们相得甚欢。可曾有什么果子在纷披交错的枝叶间长得很高,使我们拿杆子都敲不下来? 我很清楚,这种果子绝不会有人带进市场,它跟市场上的苹果迥然不同,也跟干瘪的果子和果酒判然有别,如此完美的果子,不见得每年冬天都有产出。 野苹果的时代行将落幕,它可能会在新英格兰绝迹。有些种植本地水果的园子相当大,你依旧可以在里面漫步,以前这里的果子绝大部分送进了酒坊,现在它们都腐变霉烂了。我曾经听说,在一个遥远的山脚小镇上,苹果从山上滚下,业主唯恐它们混进榨汁的果子,是筑墙阻拦,使墙下堆积的果子居然有四英尺之厚。我常常会在荒弃的草场见到本土的果树,它们为日渐起身的林木所围,但是,由于气候变迁,也因为改良品种大量涌入,这些果树仍旧无人经营。恐怕一百年之后,有人走过这些荒原时,再也无从领略手执长杆采集野果的乐趣了。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惜,乐趣如许之多,你却无从得知!今天,尽管鲍尔温和鲍特风靡一时,但百年前这里是否也像今日一般建成了好多如许之大的园子,我无从确定。但我知道,那时候,我们镇上为酿酒所建的果园绵绵相望,人们既吃苹果,又喝果汁,给果树的唯一养料就是果渣,因此除了栽植之外无所耗费。当时,人们只需沿着围墙插上果苗,然后便无所用心,由它自己去碰运气。今天,没人会把苹果栽到如此僻远的地方,或是沿着人迹罕至的道路和小巷,或是在林中幽谷的深处。现在,人们既然付出代价获得了改良品种,便在房屋近旁辟出一块地建成林子,然后圈上篱笆。结果只有一个:我们只好去桶里找苹果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如右: “老年人哪,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哪,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么?……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哪,都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有一队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 “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 “农夫阿,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阿,你们要哀号!…… “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 仲泽译本,诗意译笔,古朴雅致,信实优美,还原梭罗其“神” 授权收录新英格兰本土木刻版画艺术家托马斯·内森的10余幅经典黑白插图作品,再现梭罗心灵归处的万物风景 全手工布脊精装典藏本,简约古雅,汉译梭罗文集的珍藏之选 特别收录梭罗学者亨利·赛德尔·坎比的精彩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