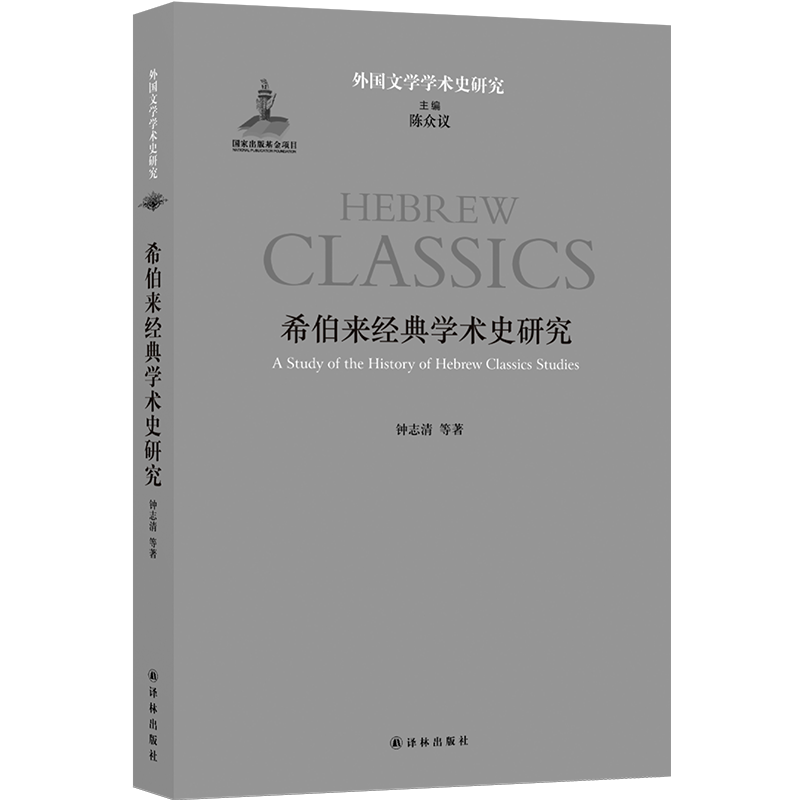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84
折扣购买: 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
ISBN: 9787544780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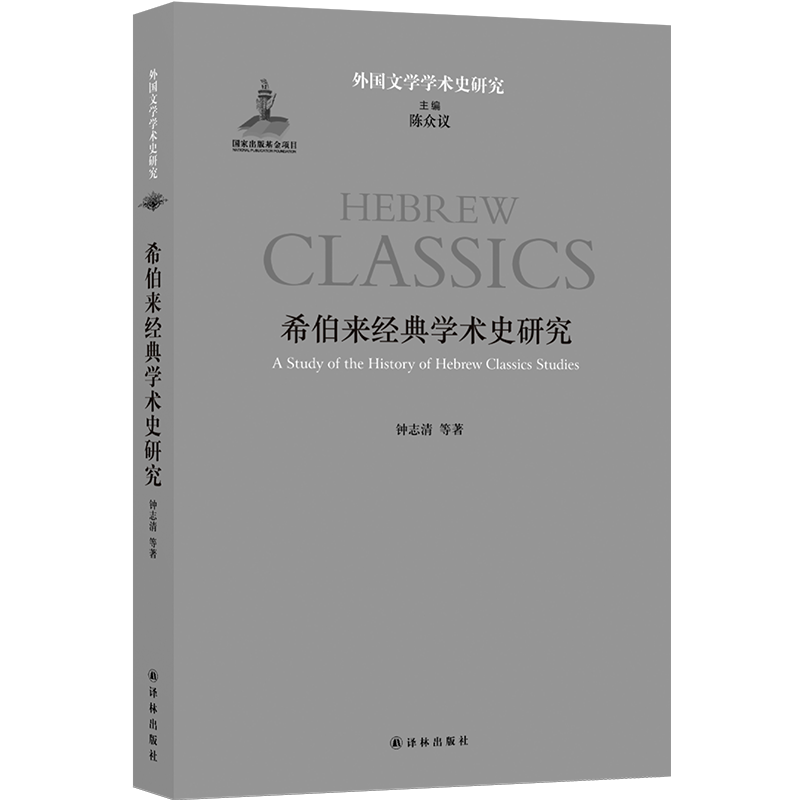
第一编?希伯来经典学术史 第一章?从古代到 17 世纪的圣经阐释 希伯来经典文学研究或阐释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古老的解经学,但是其意义有别于今人所理解的圣经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这是因为,尽管在圣经文本中已经存在神话、故事、历史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类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文学尚未以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单独存在。无论如何,关于圣经阐释的历史明显囊括了解读圣经的不同方式与视角。古代的圣经阐释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寓意法(Allegory)与预表法(Typology),以及来自犹太传统的米德拉西(Midrash)。 寓意法源于古代希腊传统,它假设圣经具有多重层面的含义,在解释圣经时追求字面性(literal)或历史性(historical),寓意性(allegorical)或教义性(doctrinal),道德性(moral)或比喻性(tropological),以及灵意性(anagogical)或末世性(eschatological),与早期犹太拉比寻求字面意义及其之外意义的做法一脉相承。按照当代学者约翰·哈亚斯(John Hayas)的说法,在基督徒当中,追求文本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区分“字母”与“精神”。就像人拥有肉体、灵魂和精神一样,文本也是如此。文本的肉体乃是其直接的意义,灵魂乃其道德感,精神乃其神秘含义或寓意。此方法的来源包括:希腊人对于史诗和神秘物质的寓意追寻,阿里斯托布鲁斯和菲洛(这两人后面有说明)对圣典的哲学—寓意阐释,拉比释经传统,以及来自对文本意义的多重发现。 预表法的主要特征是把《新约》母题 与《旧约》作对比,关注《新约》中的一些人物、事件或者类型在《旧约》中已经出现,或者显露出某种预兆。预表法阅读通常与基督教释经学家把《旧约》当作《新约》的预示相联系,但是预表法也是拉比们所沿用的阐释策略,说的是“父辈行为预示他们的后代会遭遇什么”。最后,差不多任何人、任何事都变成了潜在的预兆:亚当、亚伯、以撒、约瑟、摩西、约书亚,以及《旧约》中的其他人物都代表着耶稣的某个方面。预表法与寓意法都以圣典的“精神认识(感)”著称,与“字面认识(感)”相对。基督教与犹太教不同,在信仰耶稣和使徒事件的描述上差异很大。基督徒认为,这些事件实际上在《旧约》中就已经得到预示,比如在先知以赛亚和大卫的诗篇中曾经出现过。后来又形成一些难以释解的矛盾,比如关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问题的讨论: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上帝为什么会接受儿子被杀这一事实,而未能让他像以撒一样获救?也许这是一种牺牲。一些犹太学者,如库格尔(James Kugel)也认为以撒背柴与耶稣背负十字架具有一种预表关系。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在《上帝之城》中讨论了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亚伯是牧羊人,被弟弟该隐杀害。他可能是耶稣的前身,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中便有“好牧羊人”的说法,而且耶稣也是被谋杀,被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 米德拉西,这里指的是古代犹太权威机构倡导和使用的一种阐释圣经的方式,其主旨是把经文的深一层意思挖掘出来。有些犹太学者认为,早期犹太解经学家鼓励寻求同一文本的不同意义。希伯来词汇中的每一个辅音字母组合(即词根)可在文本中找到四种含义: Peshat(字面意义或者直接的意义)、Remez(隐含、暗示的意义或寓意)、Derash(对经文发挥性阐释)以及Sod(神秘意义)。在犹太传统中,米德拉西也指圣经阐释和阐释注疏,这些含义将在后文出现时逐一予以解释。 一、 拉比之前犹太人的圣经阐释(公元前150—70) 从时间上看,圣经阐释历史久远,经文抄写者和解经学家甚至在《希伯来圣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开始阐释希伯来文作品了。要追溯犹太圣经阐释的起源,就不能忽略犹太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进兵耶路撒冷,犹太城邦沦陷,大批百姓、工匠、祭司与王室人员被掠走,酿成犹太历史上耸人听闻的“巴比伦之囚”事件。这一事件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百姓的被征服和离散。犹太人迁居到了耶路撒冷和犹大两地之外,在半个多世纪里以囚虏身份生活在异乡,因而出现了希伯来语与其他语言并置的局面。数十年后,邻国波斯人攻克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存境况因此发生了转变。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签署赦令,允许犹太人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就像詹姆斯·库格尔所阐释的,巴比伦流亡本身对犹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群体回归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人选择了不回归,已回归者试图重建过去。但祭司与王室人员究竟谁为领袖?究竟是按照波斯人所期待的那样使犹大成为波斯的一个行省,还是等待时机实现政治自治,甚至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过去的目的在于规划未来。那么,带有记录过去性质的古代文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这样一来,带有追述过去色彩的圣经阐释变得重要起来。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了波斯帝国,并逐渐统治西亚南部和埃及,希腊语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希腊文化逐渐影响到犹太社区。在圣经出现之前,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代希腊文学经典就包含了许多神话学叙事,并得到寓意上的解释。 由于接受了希腊式教育和希腊思想,在解经学方面,犹太人借鉴了希腊人的方式,在解经时追求隐藏在字面意思背后的经文含义。这种方法即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寓意释经法,追寻寓意成为后来圣经阐释学中一个重要的范式,尤其在基督教解释者中,这种方法更为流行。在具体实践中,寓意化是一种技巧,把具体文本中的人物、事件或地点解释为某种抽象的存在、观点、美德或邪恶,或某种哲学教义。这一点我们从基督教释经学的现存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基督教释经学》中说,这个学派的一个主要特色,在于其源自柏拉图哲学的寓意解经方法(allegorical method)。但是在拉比解经传统中,犹太人寻求寓意的文本主要是《雅歌》。 拉比之前的释经家,亚历山大的犹太哲学家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约公元前160)便是采用当时流行于希腊学界的寓意法释经的先驱者之一,但他流传下来的著述甚少,只有《摩西著作评注》残篇。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后约两百年,出现了运用寓意法解释圣经的大师,即生于亚历山大城的思想家菲洛(Philo of Alexander,约公元前30—55),他致力于把《希伯来圣经》与柏拉图哲学协调起来。 菲洛有公元1世纪最伟大的犹太作家之称,具有广博的希腊语和犹太文化知识。他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其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希腊文阐释《希伯来圣经》的。他在当时深受尊重,其作品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基督教作家。菲洛的书写反映出1世纪初期地中海地区两种重要的 文化传统的交汇。菲洛相信,犹太圣典作为神性交流的产物,显示出神性智慧。他用寓意法解释了《创世记》前十七章,解释创世的故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大洪水和亚伯拉罕的故事,解释律法书和 《出埃及记》。当代学者库格尔认为,菲洛寓意解经的精华可以用亚伯拉罕离开吾珥故乡(《创世记》11:31)这一例证加以概括。菲洛认为,《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从字面意思上看,讲述的是过去的一个事件,但是从寓意角度阐释,它讲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人的心灵:任何像亚伯拉罕一样寻找上帝的人,都要离开家这个能够“信任”的世界,走向“城市”,即另一种认知方式。 库姆兰社群时期(公元前150—68)的圣经阐释成果,在20世纪中叶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有所体现。库姆兰社群醉心于《先知书》的解释。他们努力搜寻《旧约》中的预言,引用它们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其释经取向为“别沙”(pesher),其希伯来文的含义为“解释”(interpretation)。利用这种解经方式的人认为,圣经的书写有两个层面:表层写给普通读者,深层(隐含的层面)写给专家。该取向具有三种释经技巧:一、释经者为了支持某个解释,可以提议对经文做出改动;二、释经者也会把预言理解为是指向他们那个时代而说的,宣称预言将会在当时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中应验;三、释经者可能采纳一个割裂的释经取向,把经文分割为独立的词组,然后无视上下文,各自解释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