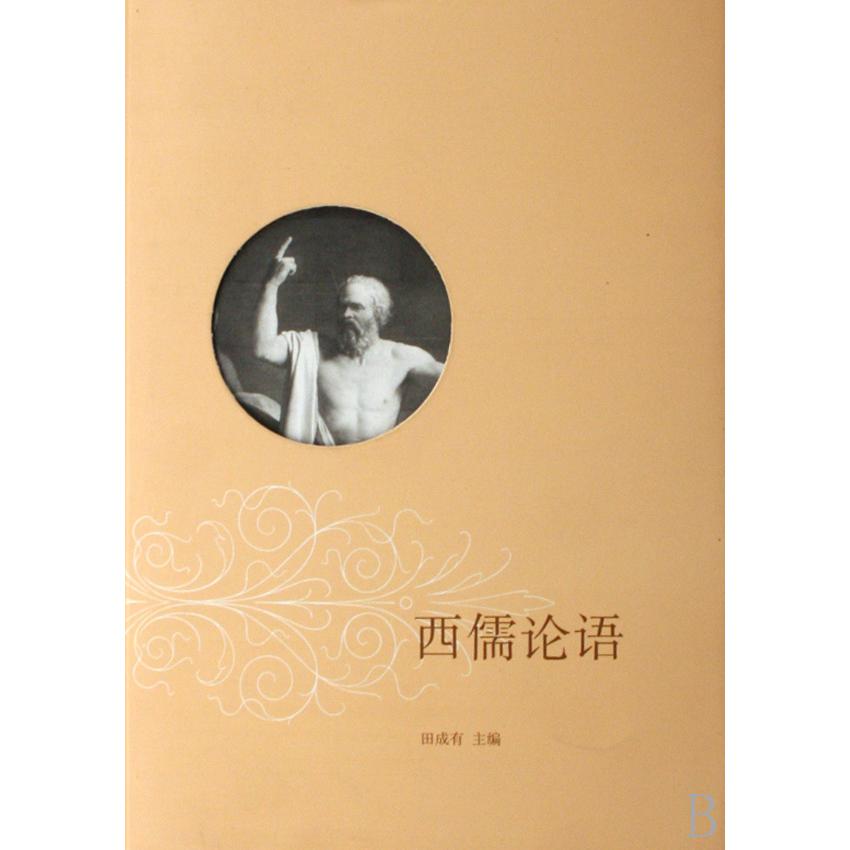
出版社: 法律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6.50
折扣购买: 西儒论语
ISBN: 9787503678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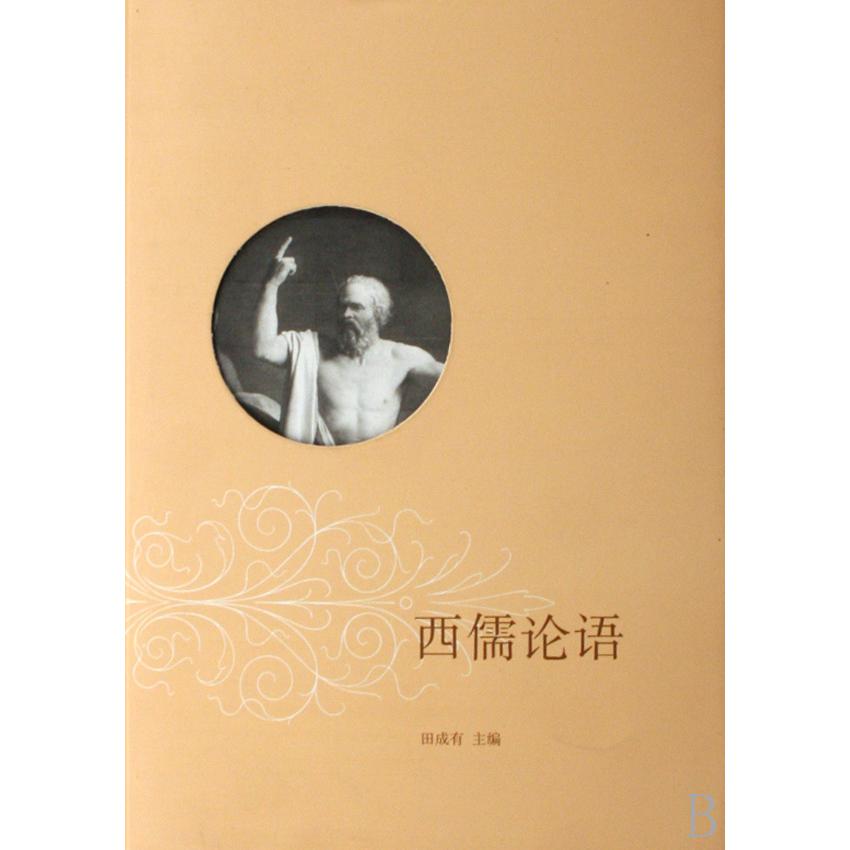
田成有,云南省富源县人。1982—1986年云南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1986—1989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03—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云南省委副主委,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法学博士,教授。 主要成果 已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等国内著名杂志上发表100多篇文章。成文近200万字。 已出版《传统法文化与法治现代化》、《质疑与创新一法学边缘处的深思》、《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官的人生》、《给法官的九百句忠言》、《守护正义一当代中国法官的知与行》等专著。曾获“云南省杰出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秉承“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理念,建肺腑之言,献务实之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精神,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 ——自由。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都还匍匐在暴君专制的淫威下惶 恐不安之时,古希腊人已经走上了自主自治因而自由的道路。在雅典城邦 建立后的数百年间,这座以智慧、勇敢和民主体制著称的城邦虽然经历了 无数的战争和天灾,但却在议会之神和说理女神的荫护下,始终屹立不倒 。然而,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在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了,对手是一位年 届七旬的老人,一位被称为“西方孔子”的哲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 助产婆。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 ,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时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雅典带来 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 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生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 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 图和亚里斯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 罗马时代。 苏格拉底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 ,但也因此得罪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有权势的人。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 “对神不敬”和“腐化雅典青年”,并由此经历了一场浩大的审判。他接 到传票后,一大早就到法院门口等待审判开始,好像在等待他的命运一样 。苏格拉底上了法庭之后,1个人面对501人组成的法官团,当时苏格拉底 已经近70岁,法官中大多数是他的晚辈,原本应该很容易获得同情而被判 无罪。苏格拉底却根本不想为自己辩护,他所说的话让法官团深觉反感, 便以281票对220票判他有罪。法官团问苏格拉底想接受什么惩罚,结果他 说:“对我最大的惩罚就是把我供养在国家英雄馆,不让我在街上与人谈 话!”法官团听到这种回答一怒之下便以更大的比数——36l票对140票— —判了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正好赶上雅典的“圣船”仪式,在 一个月内不准杀人。这一个月中,苏格拉底其实有很多机会逃走,而且一 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就绪,只要苏格拉底同意就可以立刻潜逃。然而苏格拉 底却坚持不逃狱,他说:“我身为雅典公民,一定要遵守法律。法律以不 义的方式判我有罪,但我不能因此而违反法律!”这位在法庭上因为狂妄 而激怒陪审团的人认为必须尊重法庭的判决,审判虽然不公,但却是合法 的,自己跑出去意味着违背法律,而这法律是自己同意遵守的,偷偷跑掉 如同违背自己亲手所订的契约。 对于死亡,苏格拉底有独到的见解,“死亡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死 亡就好像是无梦的安眠,而这是求之不得的!第二,死亡是前往一个过去 的人所去的世界,所以我死后去的这个世界,可以同很多贤哲见面,这很 好啊!”死亡的期限到了,苏格拉底从容地喝下毒酒。苏格拉底将死亡看 作是痊愈,如他所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准备死亡、练习死亡。因 为死亡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消失,而人的灵魂由此摆脱物质世界的牵绊,不 会再有各种欲望妨碍真正的自由了”。“出发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各自 走各自的路吧——我去赴死,你们活着,哪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这就 是他的临终之语。 苏格拉底拒绝逃狱从容就死的理由很明确,那就是他对法律的信仰与 服从。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 ,他不能违背。虽然不必遵从城邦不公正的法律,但是如果你违反了城邦 的法律,就必须服从惩罚。城邦的法律,即“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 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既然你是这个城邦的公民,且没有 因为不满这个城邦的法律而远走他乡,你就有义务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 虽然法律不是神意,而是人意,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有修改的必要,但 是,绝不能因此轻视它的价值,只有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执行法律,才 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 根本保证,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 最初体现为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 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 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 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 意志。 不仅如此,苏格拉底更认为,相信神并信仰神是行善的先决条件,一 个人只有信神,才能有德,才能求善,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这个意义 上说,信仰神和服从自然法是绝对的,是正义的体现。由此,苏格拉底的 结论就是,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人定法,人们都应该坚决地服从,“守法 即正义”,他说,在各个国家中。那些最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 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一个国家的公民遵守法律,他在和平时期就幸福, 在战争时期就紧密。具体来说,对法律绝对服从和遵守的依据是:其一, 为了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其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和义不容辞的责 任;其三,服从法律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准和正义意识。按照苏 格拉底的看法,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只有 这样,才最符合正义的要求。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 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 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 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 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 。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 的精神。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希腊哲学 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苏格拉底之死仿佛是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 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他的死仿佛是道德 与法律的合谋。他的名字与雅典政制一起永垂史册,并激励后代人像他一 样超越个人的荣辱毁誉甚至生命,重公义、重法律,自觉遵守心中的道德 律令和法律准则,古希腊法治的精神也正由此可见。 有趣的是,差不多与苏格拉底同时期,在中国黄河流域繁荣昌盛的秦 国,一个曾经立过不朽功勋的法学家也被判死刑,他就是使秦国统一法制 、富国强兵的商鞅。他为了活命先后逃到魏国和商邑,举兵伐秦兵败后被 杀。我们可以看到,同是面对死神,商鞅没有苏格拉底那样从容,为了逃 生,他不惜几次规避或违反法律。两个法学家对待死亡的态度迥然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法律信仰的差异。 时至今日,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瓶颈,仍是民众法律信仰的普 遍缺失。法律信仰缺失直接造成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 ,那么,我们对此应有怎样的认识呢? 严格地说,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是法律信任的危机,而不是法律 信仰的危机。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乃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大规模的法律移 植运动而得出的产物。制度移植并不代表文化必定发生同步的移植,正如 梁治平先生所言: 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 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 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 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 ?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 一段话道尽了在我国树立与西方相同的法律信仰必然遭遇的障碍。换 句话说,在我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建立起与西方同质的法律信仰。既然并未 建立法律信仰何来“危机”之说? 那么在中国法律信仰的树立难道真的不具有可能性吗?并非如此,事 实上,在我国对法律的自发信仰已经萌芽,只是这种信仰不同于西方传统 的法律信仰,而且尚未转化成自觉信仰,是一种不完全的信仰。 因而在我国树立法律信仰必然与西方选择不同的道路,但这并不能构 成我们悲观消极的理由。我们要做的是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而不是 望洋兴叹抑或愤懑不平。中国人能树立什么样的法律信仰?怎样才能完成 从外在的强制规则到自觉的法律信仰的转变?这是法律信仰探讨者们无法 回避的问题,亦是这一论题的核心意义所在。 在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仰处于萌芽状态,自觉的法律信仰是伴随着我 国法治建设的进行而展开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我们可以做出最大的 努力使得这个过程能够顺利展开。笔者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立信,取信 于民,然后才能谈得上树立民众的信仰,抑或说促使民众的法律信仰从自 发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转变顺利进行。 法治秩序的实现,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看能否在民众中间培育出 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精神或理念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苏格拉底这样的 “殉道者”,也没有出现过像苏格拉底这样以身捍卫法庭判决的壮举,但 我们大可不必盲目悲观,只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和把 握我国法治建设中的自身特点,坚定地向提升和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这个 目标迈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必然会因为获得信仰的支撑而被插上腾飞 的翅膀!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