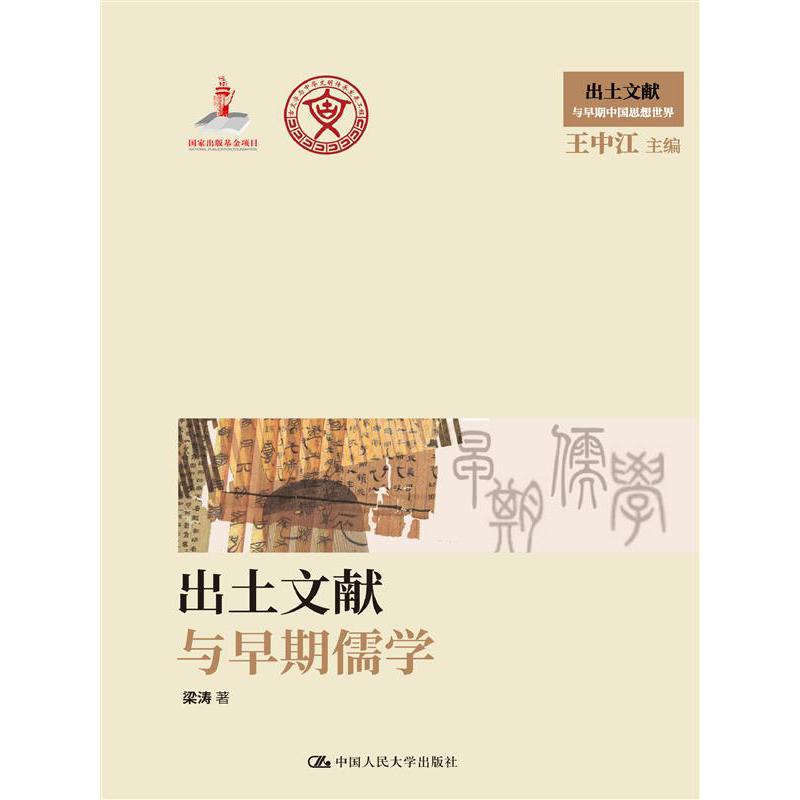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原售价: 99.00
折扣价: 66.40
折扣购买: 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
ISBN: 9787300320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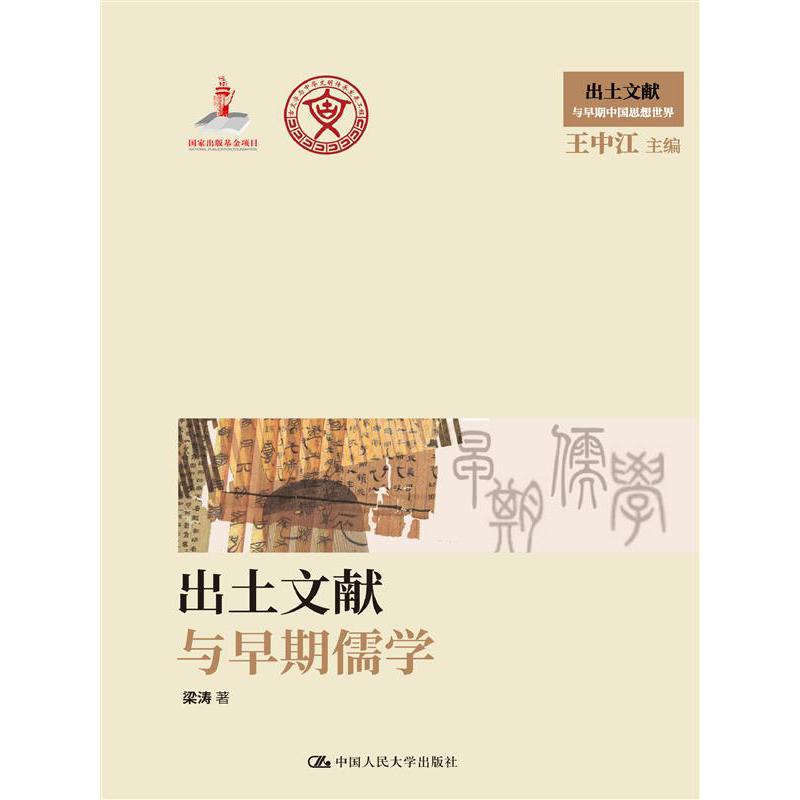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专著,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回到“子思”去,从文化的承继来看,则是要处理前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文化的关系,具体讲,也就是五经与四书的关系。五经本乃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累,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其进行了整理、诠释,并用于教学之中,使其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则是孔、曾、思、孟的个人言行记录或著述,是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主张,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子思等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不是抛开六艺或五经等基本经典,而是对其进行自由、开放的诠释,视其为思想的源头活水,通过引述《诗》《书》,为自己的观念、学说寻找合理性的说明,在思想突破、创造的同时,并没有割断与前轴心时代的联系,使儒学具有了强大生命力。在早期儒学那里,既存在着子学这样一条主线,也存在着早期经学或六艺之学这样一条辅线。汉代以后推重经学,实发展了孔子的六艺之学,而把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看作经学的附庸或者传记,故是以五经看孔子,视孔子为五经的整理者或“微言大义”的阐发者。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则是回到孔子所创立的社会人生之学或子学,但是又升“子”为“经”,提高了《论语》《孟子》等书的地位,故特重四书,以此为儒家的基本经典,同时又承认五经的地位。从儒学的发展、演变来看,宋明理学可能更接近早期儒学的形态,其吸收、借鉴佛老理论思维,对儒学进行重新诠释,也使儒家的心性义理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宋明儒推重四书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所谓四书未必能涵盖、反映早期儒学的精神内涵,而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其道统说,对早期儒学的一种“损益”而已。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立足于狭隘、“一线单传”的道统观,而是视道统为根源的文化生命,为生生不息、历久常新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则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生命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其中《论语》《孟子》《荀子》分别是孔、孟、荀精神文化生命的记录与反映,而《礼记》是汉代学者对所搜集、发现的七十二子及其后学(包括曾子、子游、子思等)的部分作品,以及讨论礼节仪式文字的编订、整理,故郭店、上博竹简中的有关内容也可归入其中。这样《论》《记》《孟》《荀》实涵盖了早期儒学的文化生命与精神内涵,可合称“新四书”。对于《论》《记》《孟》《荀》,我们也不是视其为“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而是儒家文化生命生生不息,成长、发展,乃至曲折、回转的过程。所以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无力独自承担儒家道统,面对儒家道统,面对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他们都存在着“所失”或“所偏”,只有统合孟、荀,相互补充,才能重建道统,恢复儒学的精神生命与活力。孟、荀思想中的某些对立与分歧,恰使其相互融合与补充成为必要,故读《孟子》需兼《荀子》,读《荀子》需归于《孟子》(尤其在人性论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
如果说当年宋明儒者是以回到早期儒学、回到孔孟为目标,以借鉴、学习佛老的形而上思维和理论成果为手段,“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广义的)”,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而完成了一次儒学的伟大复兴的话,那么,郭店简及上博简的发现,则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孔子到孟、荀的思想发展,感受到早期儒学文化生命的脉动,重新发现、挖掘早期儒学的思想资源。故学习宋儒的做法,重新出入西学(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罗尔斯等)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复兴与重建,便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职责与使命。一方面,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另一方面,“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又被带入六经中,是谓“我注六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是孔、曾、游、思、孟、荀精神之所在,也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