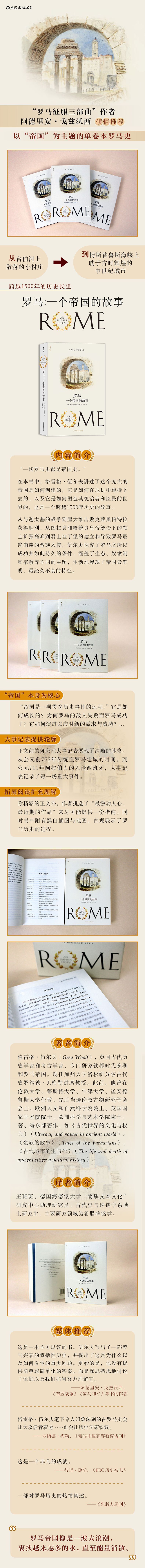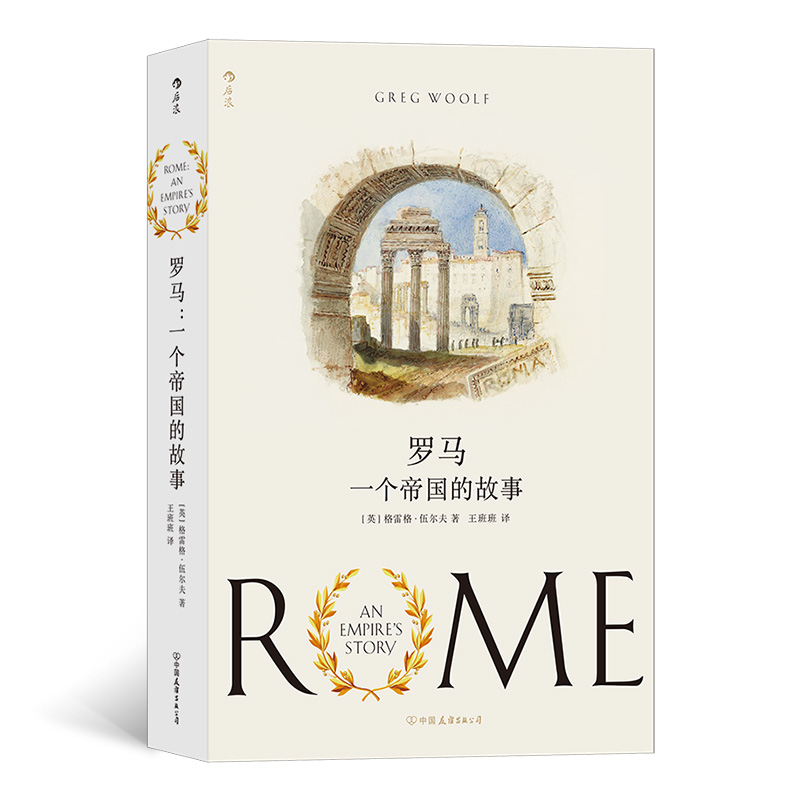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39.70
折扣购买: 罗马 一个帝国的故事
ISBN: 9787505754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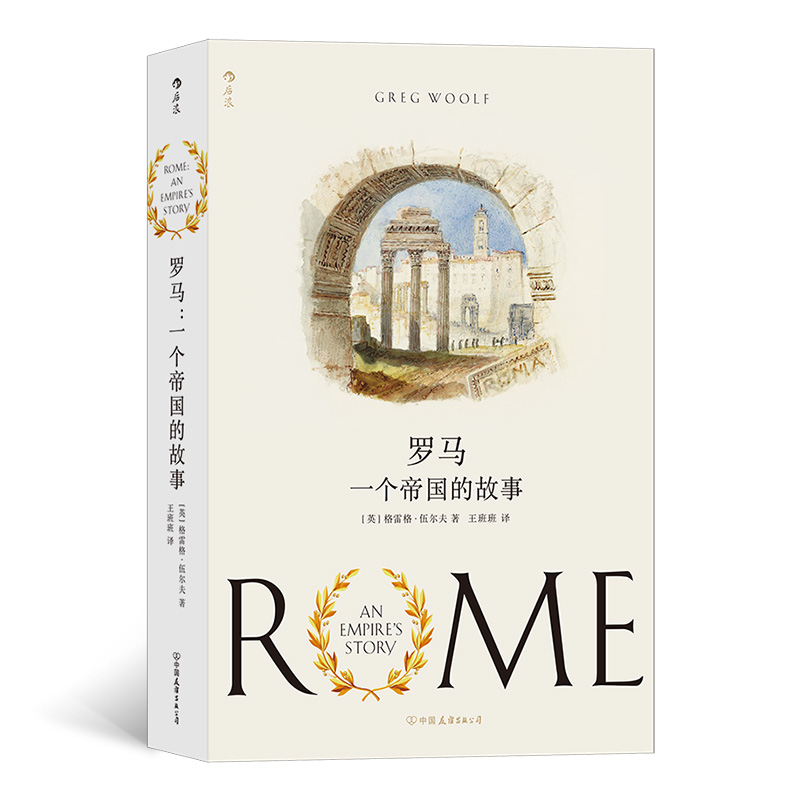
著者简介 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英国古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专门研究铁器时代晚期和罗马帝国。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古代史罗纳德·J. 梅勒讲席教授。此前,他曾在伦敦大学、莱斯特大学、牛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先后当选伦敦古物研究学会会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著、编多部著作,如《古代世界的文化与权力》(Literacy and power in ancient world)、《蛮族的故事》(Tales of the barbarians)、《古代城市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ancient cities: a natural history)。 译者简介 王班班,德国海德堡大学“物质文本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古代史与碑铭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希腊碑铭学。
君主制的回归 在有皇帝前,罗马就有了一个帝国。本书的前一半已经讲述了它如何诞生的故事。一座与其他城市竞争的城市,先是奋力控制意大利,再是西方,最后是整个地中海盆地及更多地方。或者一如罗马人自己更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民族赢得了对人居世界其他民族的领导权(imperium,arche, hegemonia)。罗马人将其想成一个集体之功:元老院与人民,罗马及其盟友,城邦的人与神协力成功。直到最后阶段,个人领袖们才从西庇阿、法比、梅泰利、埃米里·保利及其他大家族中涌现出来。苏拉、庞培以及恺撒的当权,从事后来看,似乎就是君主制的征兆。[ Elizabeth Rawson, ‘Caesar’s Heritage: 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5 (1975).] 大将军们提供了帝国急需的资源与政策协调。皇帝们在这件事上做得更好,而且他们还带来了和平。在公元2世纪初(亚克兴战后约一个半世纪)写作的元老阶层史学家塔西佗,讽刺地把共和政府表现为在罗马君主制的宏大叙述中的一段短暂偏离。但无论是他还是他同时代的其他元老们,都没有实际反对诸恺撒统治的迹象。皇帝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必要一环。 本章讲述罗马人是如何不再担忧,并开始热爱他们的新王的,即使这些新王从来未能让罗马人以“王”的名义称呼他们。这一权变对身居罗马城的罗马人最为关键。希腊人乐于使用basileus(王)一词,埃及人把他们当作pharaoh(法老),各地的外省人都把家姓“恺撒”以及元老院于公元前27年授予屋大维的特别头衔“奥古斯都”作为君主的同义词。第一个皇帝明白,不宜进行公开革命,但帝国最初的三个世纪中,君主制逐渐从暗处来到明面。我们仍将早期帝国称为元首制时期,因为皇帝们在此期间仍使用princeps(元首)之称。不过,君主制的所有要素从一开始就已完备,这点已成共识。这些要素包括:宠臣、顾问、秘书与卿相组成的核心圈;宫廷密谋(因为决策皆出宫中);中央对信息的集中与对资源的掌控;以宫廷为中心的恩庇关系网;世袭继承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在一段时间后方得认可)。 一如所有君主政体,罗马帝政的历史也是一部宫廷争权夺势的历史、一部代际冲突的历史、一部性与政治纠缠冲突的历史、一部实际上的与疑似中的密谋的历史,但也是一部稳定性非凡的历史。虽说“皇帝不崩于榻”(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大体不差,但对许多皇帝个人的谋杀似乎也确实鲜少撼动体系本身。正是因此,本章的大量篇幅都关涉这发展中的制度,而非身居宝座之上那些着实多彩有趣的人物。本章的叙述和第13章有所交叠,那里将考察帝国的外在层面,尤其是战争与外交。那段故事将是谨慎稳固统治和有限前进扩张的两个世纪,而随后3世纪的危机全然出乎皇帝们的意料,帝国经过一世代还多的时间才从中恢复。帝国在来自欧洲北方的入侵与和重整旗鼓又怀攻略之心的波斯帝国的战争带来的双重压力中几近崩溃。而幸存下来的事实上已是一个新的帝国。它的故事将在第15和第17章中讲述。不过,凡此种种转型期间,皇帝其人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而从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皇帝开始当然是合适的。 奥古斯都 公元前30年8月,屋大维正身处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将近18年前几近相同的地方:在亚历山大里亚,敌人尸首之中,他沉思着胜利。但罗马的世界在法尔萨卢斯战后已经大变。回首公元前48年,恺撒还曾为庞培被杀而哀悼,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本想放他生路。或许他真的会如此,一如他在战胜庞培后放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一条生路。将近20年后的新赢家则全然不同。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均自裁殒命。但克莱奥帕特拉宣称自己为恺撒生下的男孩恺撒里昂(Caesarion),正是在屋大维的命令下被处死的。在与安东尼为恺撒党领导权而苦战之后,屋大维不会容许恺撒的任何其他后嗣。他也控制了埃及,将最后一个希腊化大王国吞并入自己的帝国。为安顿他和安东尼的士兵,他需要托勒密王朝的资金府库。屋大维吸取了他人的教训。他不会像苏拉一样依赖恫吓与立法来稳定国家,他不会模仿庞培公元前62年的举动遣散自己的军团,他不会像恺撒一样宽宏大量,他不会获取独裁官头衔而闲坐于罗马城等待刺杀者的匕首。他意在统治帝国。 讨论屋大维为何免于恺撒命运这一问题的著作已经浩如烟海。他是狡猾还是幸运?在亚克兴战后他当然也有敌人,而且或许也有密谋。但他真的面临同样的挑战吗?他回去统治的罗马和他化为盟友的统治阶层有什么不同呢?此时的罗马是否已经如此疲于内战,到了可以接受任何替代选择的程度?元老院是否已因格杀勿论令和内战的恐吓而不敢作声?人民真的终于相信他是拯救国家的神祇吗?回答这些问题并没有证据缺乏的困难:屋大维或曰奥古斯都漫长的统治期(自亚克兴战役至他死亡共计45年)在罗马史上是文献最丰富的时期之一。问题在于,屋大维及其盟友功将他们的版本的历史表现成了主流叙事。在诸神支持下的更新、道德重塑以及复苏,这些主题在普罗佩提乌斯、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歌中,在罗马及一些行省主要城市的纪念性重建物中,在和平祭坛(Ara Pacis)、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广场以及由第一位皇帝着手兴建的玛尔斯、阿波罗及其他神祇的神庙里精美的图像系组之中产生了共鸣。这一成功叙事也通过表演展现。我们难以想象观看公元前29年那场为庆祝他在巴尔干、亚克兴之战和在埃及的胜利而举行的三重凯旋式的体验。但观者都知道,这意味着内战的结束。这也同样适用于公元前17年宏伟的百年大祭(ludi saeculares),它表面上恢复了一个古老的节日,但奥古斯都则把它当作另一种表明一个时代结束与下一时代开始的方法。有些演出则更为微妙。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屋大维逐渐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放弃权力的过程中重塑了自己的形象,每一次放弃权力都伴随着元老院新授权衔。关键点发生在公元前27年1月的两场会议,他带着“奥古斯都”头衔、一个幅员辽阔的行省(本质上是驻有军队的帝国半壁江山)的十年统治权,以及通过差遣官进行治理的权利走出会场。公元前23年,他终于辞任数任中的最后一任执政官,并获授“更高治权”,这种权力曾使庞培及其他人得以身居行省长官之上。事实上,屋大维在几乎所有的头衔和权力中都更多继承了庞培而非恺撒。仅有的平民派元素,则是保民官的权力与不可侵犯地位。人民享有节日—俗话所说的“面包和马戏”(panis et circenses),[ 尤维纳利斯《讽诗集》10.81。Paul Veyne 的学术名作也以此命名:Le pain et le cirqu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 pluralisme politique (Paris: Seuil,1976)。——译者注]1 但人民大会选择政务官或通过法律的实际权力则衰落了。奥古斯都借由元老院通过自己的立法,指派元老掌握所有主要军事和政治管区、骑士掌握次一级的管区,选任一些政务官,并保有否决他人任命、决定最关键祭司选举的权利。虽从未创立皇帝这样一个正式的政制地位,他仍凭借影响力、游说、大笔财富与压倒性的军力威慑,在国家中积累奠定了一个决定性地位。在他死时,其全部权力以及几乎全部头衔都交给了他的继承人。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他的死亡当然为时尚早,不过频繁染疾也意味着无人能指望他长保健康。但这也给他很长时间来发展皇帝的角色功能。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是关乎存续、军队复员、巡视和稳定行省、与元老院建立一种精巧共治的10年。在这10年中的很长时间里与罗马保持物理上的距离或许很有帮助。公元前22年的一场密谋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危机,但到了公元前17年和百年大祭之时,他就已极尽安全了。在统治中期,他发动了大规模征服战争。公元前20年他与帕提亚人讲和,克拉苏的军旗得以归还,而在东部稳定之时,他即能投入资源来征服欧洲。他的养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率领大军跨越莱茵河,征战多瑙河上下。征服世界几乎可以肯定是为解决国内关于“皇帝做了什么?”这一问题而设计的。直到公元9年于日耳曼一场灾难性的惨败之前,对此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是:皇帝领导罗马实现其历史使命。奥古斯都时期的艺术与诗歌充满了世界征服的图像,并且自信地预告了印度、不列颠与北斯基泰的臣服。海外的胜利转移了对国内因争夺奥古斯都继承人之位而产生的丑闻的关注。最终胜利者是提比略。而其他人都未能幸免于难或是名誉无损。 在奥古斯都死时,提比略就已经分有了他的大部分正式权力,但他仍必须忍耐他的前任留下的最终安排。一座皇家陵寝在战神广场距离台伯河不远之处建立起来。自从于公元前28年竣工后,它已积累了许多奥古斯都曾期待的继承人的遗骨,尤其是他的女婿马尔凯路斯(Marcellus)和阿格里帕(Agrippa),以及外孙盖尤斯(Gaius)和路奇乌斯(Lucius)。只有受他钟爱的才被接纳到这里:他的女儿尤利娅被禁止与丈夫和儿子葬在一起,他的外孙女也被禁止安葬于此,[ 指尤利娅的长女小尤利娅(Julia the Younger),事参苏维托尼乌斯《圣奥古斯都纪》第101节。——译者注]而在奥古斯都死讯已出、确保提比略在家族中再无可能敌手之后,他的小外孙旋遭杀害,传言还是奥古斯都下令处死的。[ 指尤利娅的幼子,“遗腹子”阿格里帕(Agrippa Postumus)。下令处死他的究竟是谁,罗马史家也观点不一,参见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57卷第3章第5—6节;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6章;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纪》第22节。——译者注]冷血无情的屋大维活在了宽宏仁慈的奥古斯都形象之下。在这一陵寝中奥古斯都的骨灰将得安置。但首先是送别式。奥古斯都死讯传来时,维斯塔贞女们即出示了由她们保管的奥古斯都遗嘱。[ 苏维托尼乌斯《圣奥古斯都纪》第101节。]提比略及其母、奥古斯都之妻李维娅被指为他那大笔私产的主要继承人,前者得三分之二,后者得三分之一。遗嘱也详述了罗马贵族惯常赠予亲眷、朋友与门客的遗产。但这些人的规模已今非昔比。奥古斯都把遗产分给了每一个罗马公民,以及罗马军队中的每一位士兵。遗嘱附有三份附记文书。其中一份是整个帝国的资产负债表。它详细记载了士兵们驻扎在何处、每个小队有多少士兵、公库中有多少资金、尚有多少欠缴赋税,并附有能提供更多细节的奥古斯都奴隶和被释奴的名单。它无声地宣告了,在伽比尼乌斯首次提出授予庞培打击海盗的特别治权后的近90年间,帝国的协调共治已有了多大进步。它也展示了奥古斯都如何通过私人家户,依赖他个人的僚属而非公共奴隶、元老或骑士来管理帝国。除此以外,从未有过其他账目。但这份文献是在展示其开放性,而非邀请元老院接掌大权。奥古斯都的奴隶和门客是提比略所继承遗产的一部分;而后者早已掌握“更高治权”以及所有其他要紧的权力。 第二份附记收录了关于奥古斯都葬礼的指令。将有一场贯穿罗马城的大规模游行,所有阶层都将与他的家庭成员一同参与其中。葬礼队伍将走向在战神广场上的一个特制的火葬堆。其上有一座塔,塔顶将在点火之时放出一只鹰。这只鹰将会带着奥古斯都的灵魂飞向天国。奥古斯都将像此前的尤利乌斯·恺撒一样成为神祇。 第三份附记是奥古斯都给自己的行状,这并非一份回忆录或自传,而是用于立碑纪念的文字。它将被刻在陵墓外的两块铜板之上。这两块铜板早已无存,但其复制品遍布整个帝国。今存的最佳例证来自土耳其中部安卡拉的一座皇帝崇拜神庙。其希腊文开头如下: 移译镌刻神奥古斯都之功业与赠礼如下,他遗存的记述刻于罗马城两块铜板之上。 这句话准确描述了35个短章的内容,其中不厌其详地列举了被征服的民族、在罗马城内建立的纪念物,以及赠予各色人等的礼物。它也提供了一份对奥古斯都在内战中角色的颇有偏向的叙述。标题的拉丁原文有更多微妙之处。奥古斯都被描述为divus——“神化的”,而非径直以神相称,他的成就被饰作使全世界臣服于罗马人民之意志的进程,而他的赠礼则被解释为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的全部。他是救世者、征服者、施恩者、庇护人,以及一位胜过其所有同代人和先辈们的罗马人。这是一份比苏拉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更长的墓碣文,但二者或许大同小异。 诸王朝 提比略在公元14年顺利继位,此事业已计划良久,且资地雄厚。在奥古斯都独享的个人魅力与地位被制度化成为皇帝角色一部分的诸多关键步骤之中,这是第一步。提比略统治帝国直到公元37年,他注重效率、为人审慎,但生性疏离且不受欢迎。在位后期的多数时间中,他都远离罗马,通过他的禁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统治这座城市。虽然曾有过危机,但他都平安渡过难关。公元41年表明,在历经一场刺杀,即提比略的继任者卡里古拉遇刺之后,王朝依然可以存续下去。卡里古拉死后,据说元老院曾讨论过回归共和政体:在禁军将克劳狄推上宝座之时,论辩仍在进行着。据我们所知,这一议题再未被严肃提起。公元68年自杀的尼禄并未留下明确继承人,随后发生了一场短期内战。这是一个世纪期间的第一场内战,但持续不超过两年。高卢和西班牙的地方长官首先反抗尼禄,在后者死后就将伽尔巴(Galba)推为继任者。但伽尔巴未能说服罗马或其他军队,并在公元69年1月15日被杀,这一年也被记作四帝之年。禁军支持奥托(Otho),日耳曼军团支持维特里乌斯(Vitellius),而多瑙河、叙利亚军队与埃及长官则支持韦伯芗。但在韦伯芗党胜利后,帝国的制度却旋即回到正轨,一切似乎都在继续原来的路。就像是元老院、骑士、人民、军队与行省,都感到有必要由一人居于核心。一块铜板记载了公元69年12月通过并可能不久后就由人民大会正式准可的一份元老院决议,决议授予韦伯芗一系列特权,并援引曾授予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克劳狄的权力与权利作为前例。[ 即所谓《韦伯芗治权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CIL VI 930),今存罗马卡皮托博物馆。基本讨论参见P. A. Brunt,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7 (1977), 95–116。——译者注]在它颁布之时韦伯芗已无真正的敌手,而元老院与人民亦无切实的选择,但决议仍表达了各方对恢复内战前原状的愿望。 公元69年的事件显示了皇帝其人作为象征性的核心,作为仪式与世界权威中心的重要性。毕竟,韦伯芗当选是由上天支持的。囚室中的一位犹太反抗领袖约瑟夫斯(Josephus)预言了此事;[ 约瑟夫斯《犹太战记》第3 卷第8 章第9 节。——译者注]韦伯芗在亚历山大里亚居留时施行了疗愈神迹;[ 塔西佗《编年史》第4卷第81章第1节;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65卷第8章第1节。——译者注]女神伊西斯也支持他的事业。[ 塔西佗《编年史》第4卷第84章第1节。——译者注]皇位空悬时,卡皮托陷于火海,又有德鲁伊诅咒的传言横行。世界确实看似要分崩离析。日耳曼的辅军和高卢反抗者梦想着在莱茵河建立一个新帝国。而全新的弗拉维王朝(韦伯芗的全名是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帕芗努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定鼎,旋即恢复了世界的秩序。 后嗣是最紧要事。王的头衔在罗马仍被避免使用。但毫无疑问,从一开始罗马帝国就已经是家族事务。奥古斯都不仅宣扬自己为神祇(即神化的尤利乌斯·恺撒)之子,而且让整个城市布满了由家族成员及其配偶名字命名的纪念建筑。李维娅、屋大维娅和尤利娅的柱廊以及马尔凯路斯剧场和阿格里帕浴场,加入了尤利乌斯和奥古斯都广场的行列。这种纪念风格被他的继承者们保持下来。继承人从他的家族中指定,而他孙辈的成人礼规模则一时无两。诗人们和行省城市很快就明白过来:一个个皇家公子获得了过度的荣誉。一支驻扎在波斯边境的小股军队的日历[ 即发现于古城杜拉·欧罗坡斯的《杜拉节庆历》(Feriale Duranum, P. Dura 54 = TM 44772),公元225—235年间某年巴尔米拉第二十军团一支辅军营的仪式及节日记录。——译者注]显示,许多为他们设置的节庆在200年后仍被庆祝。对那些暗弱皇帝的支持显明了对这一世袭原则的认可。在被禁军推上皇座之时,克劳狄的全部可取之处只有名字和家系。许多人拒绝相信尼禄已死,并且至少有三个冒充者宣称自己是尼禄。[ 分别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8—9章;苏维托尼乌斯《尼禄纪》第57节;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66卷第19章。]当韦伯芗赢得东方和多瑙河军队对他竞逐大位的支持时,显然他的一大优势就是有着两位成年儿子作为潜在继承人,即提图斯和图密善。纵使缺少家系的关联,韦伯芗的正式皇帝称号仍是英白拉多·恺撒·韦斯帕芗努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而“恺撒”的头衔则被创新地用于指明图密善为继承人。[ 原文如此,事实上图密善之兄提图斯也获得了“恺撒”头衔。——译者注] 皇室女性也会参与王朝形象的展示。皇帝的妻子是公众人物,会出席庆典,接受元老院、人民和军队的荣誉,也经常被赋予宗教角色。[ Nicholas Purcell, ‘Livia and the Womanhood of Rome’,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32 (1986).]奥古斯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系列潜在继承人。皇后们也是潜在未来皇帝的母亲。在失宠之前,克劳狄年轻美丽的妻子梅萨利娜(Messalina)抱着孩子不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的塑像,宣扬了王朝的后嗣。卡里古拉的姊妹在他的铸币与塑像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与枢德(cardinal virtues)联系起来。[ Susan Wood, ‘Messalina, Wife of Claudius: Propaganda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his Reig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5 (1992); Susan Wood‘, Diva Drusilla Panthea and the Sisters of Caligul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9/3 (1995).]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Younger)则被尊为军营之母。[ 即克劳狄的第四任妻子,日耳曼尼库斯和大阿格里皮娜侄女,尼禄的母亲。——译者注]李维娅在生前死后都获得了元老院尊荣。皇室女性或能享受奢华的葬礼并在死后被尊为女神,与被神化的皇帝相当。行省城市也常为在世皇后设置女祭司。[ 对此的研究参见Emily Hemelrijk, ‘Local Empresses: priestesses of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cities of the Latin West’, Phoenix 61/3– 4 (2007)。——译者注] 后嗣的力量并不会出人意料。贵族家族自共和国初年就开始经营罗马,家族也始终居于罗马社会秩序的中心。任何其他形式的君主制都会更难得到解释。弗拉维王朝持续至公元96年图密善被刺杀之时。而皇帝秩序又一次迅速归于原位,这一次甚至没有发生内战,涅尔瓦(Nerva)就登上了皇位。他并不是一位成功的皇帝,但他收养了活跃的将军图拉真,使权力得以平稳交接。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都没有儿子,故而必须因势利导,在较远的亲属和人际关系中选择继承人。但选任继承人总是伴随收养的,因此如果去解读皇帝的官方名字与头衔,这些麻烦的过渡就显得十分费解。故而图拉真统治时名叫英白拉多·恺撒·涅尔瓦·图拉雅努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Nerva Traianus Augustus),哈德良则叫英白拉多·恺撒·图拉雅努斯·哈德里雅努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等等。养嗣无论如何都是贵族家族自我延续的一种传统方法。波里比阿的朋友、公元前146年攻陷迦太基、公元前133年在努曼提亚大捷的“征阿非利加者”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本是皮德纳之战的胜利者卢基乌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的亲生子,但从小就被过继给“征阿非利加者”科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以保证后者能有后嗣。屋大维(出生时名为盖尤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则是通过遗嘱收养成为其舅公尤利乌斯·恺撒之子。奥古斯都曾正式收养他的继子提比略,而提比略则收养了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皇室肖像相当标准化,显示出一种要让尤利-克劳狄家族诸公子的家族长相显得极近的关切。[ R. R. R. Smith, ‘The Imperial Reliefs from the Sebasteion at Aphrodisia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7 (1987).]收养表达了对家族和王朝继承的一种持续信念。因此,在马可·奥勒留确实有一个儿子康茂德的情况下,后者意料之中的即位并不惊人。康茂德在公元192年被刺却并未导向一场有序的更迭。在几次失败的开始之后,又一场短暂的内战在大军团将军之间展开。战争几乎是公元69年事件的重演,在罗马元老院和禁军未能扶持当地继承人之后,不同的军队支持各自的候选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最终胜出,并建立了一个当权到公元235年的王朝。缀名[ 拉丁文agnomen,是附丽全名上用于区别同名者的称号。——译者注]卡拉卡拉的塞维鲁之子出生时名为卢基乌斯·塞普提米乌斯·巴斯阿努斯(Lucius Septimius Bassianus),但最终掌权后则称英白拉多·恺撒·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塞维鲁斯·安东尼努斯·皮乌斯·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Marcus Aurelius Severus Antoninus Pius Augustus)。这些对延续性的过分呈现不仅掩盖了王朝之间的断裂,而且在频繁的刺杀中也维护了秩序的稳定。卡拉卡拉本人在杀害了共治皇帝、弟弟盖塔(Geta)之后六年,即217年被杀,实际上,刺杀鲜少引发内战,而且是典型的短期事件。从行省居民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收养还是谋杀造成的皇帝更迭可能都无关轻重。无论皇帝的位子看上去如何不稳,其制度都十分稳定,并且使整个帝国稳定为一体。 专业学者写就的单卷本罗马史。 兼具趣味性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