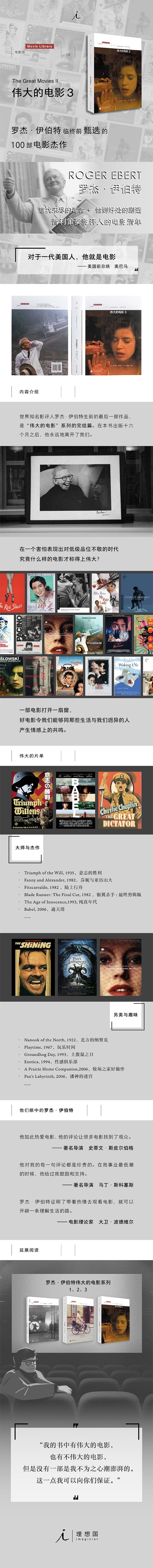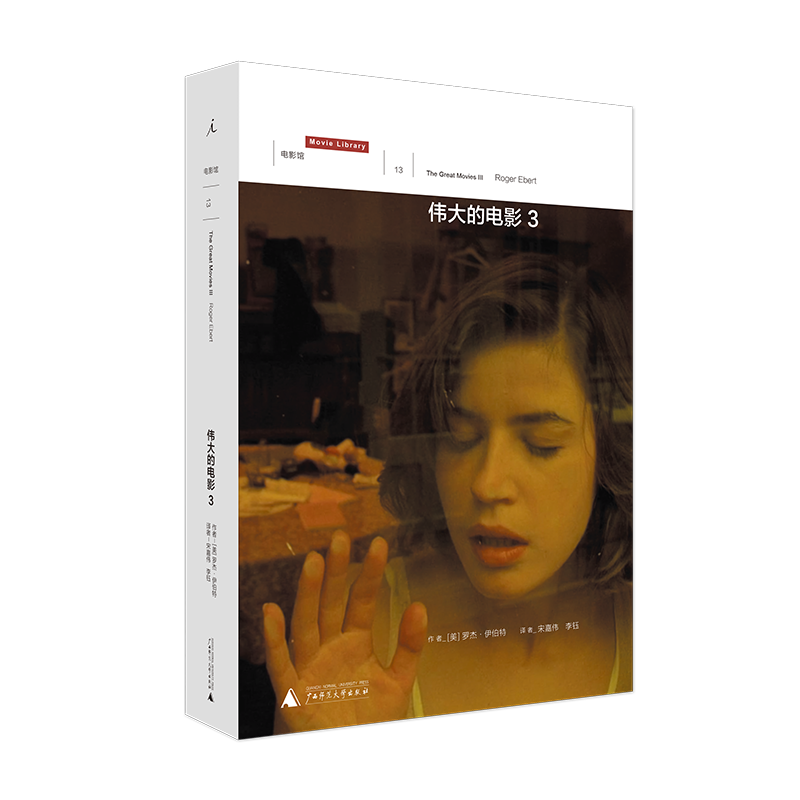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95.00
折扣价: 59.90
折扣购买: 伟大的电影3
ISBN: 9787559836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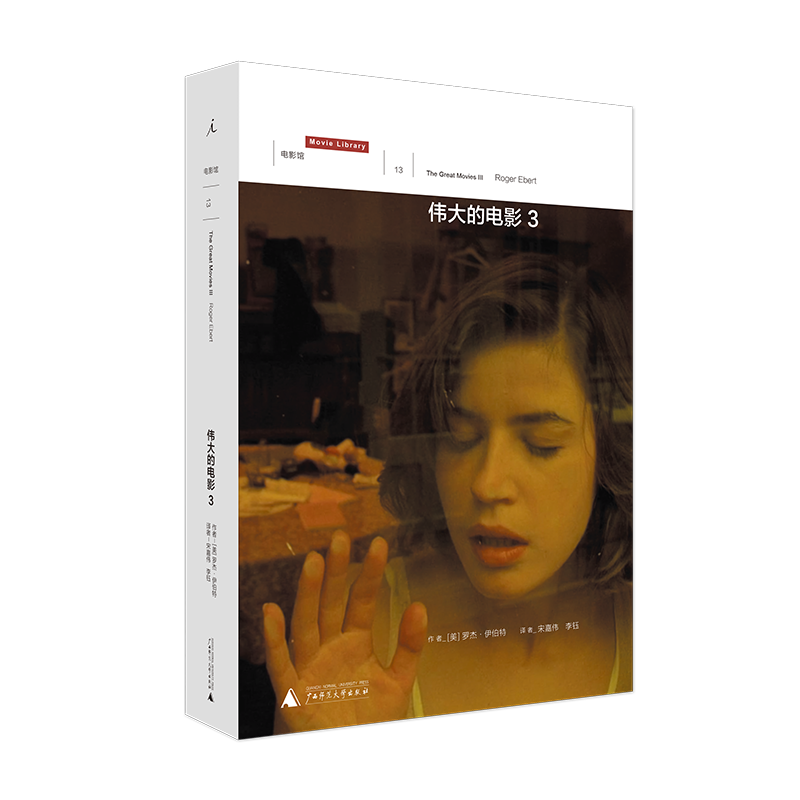
罗杰 伊伯特(Roger Ebert,1942—2013) 生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Urbana),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开普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主修英语,1967 年成为《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影评人,1975 年成为第一位因撰写影评获得普利策艺术评论奖的作者。同年,他开始与吉恩?西斯科尔(Gene Siskel)长期合作,在电视上主持电影评论类节目“Siskel & Ebert”。1999 年西斯科尔辞世后,他改与理查德?勒佩尔(Richard Roeper)合作,节目亦更名为“Ebert & Roeper”。 自1969 年起,伊伯特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艺术课程的电影课讲师,同时任伊利诺伊大学电影与媒体学兼职教授。其间,他获得科罗拉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三十余载,他每年都在该大学的世界事务会议(Conference on World Affairs)上逐镜分析一部电影。1999 年,伊伯特在伊利诺伊大学创立“沧海遗珠电影节”(Overlooked Films Festival),专门推介被忽略的佳片,每年都吸引许多观众和影人参与。 2002年,罗杰 伊伯特不幸患上癌症。2006年,病情开始恶化,仍笔耕不辍,直至2013年4月4日去世。作者生前与爱妻查兹?哈梅尔史密斯?伊伯特(Chaz Hammelsmith Ebert,一位律师)生活在芝加哥。
前言(节选)——自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 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位影评人像罗杰·伊伯特一样拥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他的忠实读者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你只消访问他个人博客的评论区,就会知道他已经吸引了来自各个年龄段能言善辩、思想深刻的读者们。他们发现他的写作—不仅仅是他的电影评论,还包括他的散文随笔,都是那么幽默风趣、技艺精湛、充满灵性—而且几乎从不缺乏启迪人心的力量。 单是他的坚韧不拔便可以为我们献上勇敢的一课。尽管有着足以令大多数人退休的健康问题,他却总是跃跃欲试,全情投入。除了常规的影评之外,他还参加电影节和电影研讨会,负责协调一个一年一度的电影节,而且还满世界飞。即使是年轻人,这些事情都足以令其身心俱疲。他还将关于影史经典的又一批评论结集成册—这就是《伟大的电影 3》。 数量并不代表一切。你可以说,自从伊伯特身患重疾之后,他的写作反而变得更为松弛、平易与高明了。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者。然而,是什么造就了他那种令人难忘的魅力呢?我会说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一位从电影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作家”(man of letters)。 …… 三卷本中的评论堪称纯文学著作。一部特定的电影即刻成为一种被阐释的艺术、一段在纸面上被唤醒的体验。作者将银幕上的关键画面同历史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并以清晰易懂的文字将它们描述出来,让人感到醍醐灌顶。这是令人赞不绝口、大呼过瘾的绝佳影评。当阅读其中的某篇文章,你就马上想去看一遍文中谈到的电影,哪怕你以前已经看过它很多遍了。 在评论分析层面,伊伯特可以用一句话唤出一个场景。他耳聪目明,能够注意到画面背景处的细节,可以举例说明一位导演的创作策略。(我们其他人得逐格分析才能做到。)只消引用一段台词,他便能直切一部电影的核心。大家都还记得《无因的反叛》中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向他父母抗议的那个镜头:“你们把我说得一文不值!”但是我们之所以记得它,仅仅因为它是陈词滥调了。伊伯特则提醒我们关注接下来那句更为古怪的台词:“你一言,他一语,每个人又都故态复萌了。”这句台词反映出了吉姆(Jim)青春期的困惑。这种细节令伊伯特陷入如下深思:这个场景以及其他类似场景,是如何由1950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化的不适,向更深层的心神不安发展,还瞥见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疑惑:生命本身意味着一切。 这种虚无缥缈的不确定性,产生出一部以其(可能并不是故意的)分裂感而引人注目的电影。就好像其男主角一样,《无因的反叛》拼命想要发出声音,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如果它知道的话,那它的魅力便会消失殆尽。伊伯特能够察觉到这种紧张感,而且他在《红一纵队》《红菱艳》《放荡的女皇》等其他经典电影中也同样发现了。伊伯特不仅赞美艺术炉火纯青的完美形式,而且也认为那些野心勃勃的电影经常释放出它们难以抑制的冲动。这种冲动要求我们对观看画面的隐含之意多作思考。 通过一次又一次对银幕世界所进行的探索,伊伯特产生出一些强有力的见解。他认为一部伟大的电影会以直截了当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于爱、信任、道德承诺与死亡等问题的永恒关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将终极问题置于其电影中心的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了。伯格曼的电影折磨着伊伯特,使他写出了一些他最为雄辩的文字:“《芬妮与亚历山大》中的事件可以透过孩子们记忆的棱镜来观看,于是似懂非懂和印象模糊的事件被重组,成为一则用来解释他们生活的全新寓言。 …… 伊伯特知道,电影已经成为我们的通用语,我们的视窗、测距仪和显微镜。他研精苦思,向我们展示了来自影像的欢愉与挑战,如何为我们打开智慧的窗口。伟大的电影既让我们受教,又令我们愉悦,每一部都把我们牢牢地固定在它的坐标之上,使得我们能够将纷扰嘈杂的现实世界,暂时变得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怀着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思想的挚爱,伊伯特“伟大的电影”系列的每一篇,都实现了不同风格的纯文学创作。它们以看上去最微小的努力引发了最意想不到的思考。入木三分的惊鸿一瞥(aper?us)带来了更深的愉悦和更大的反思:如果艺术作品的创作前提是完全普适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对于电影评论来说,这种要求可能有点高,但是我认为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不卑不亢并且情真意切的影评完全有能力做到。罗杰·伊伯特证明了带着热情去观看电影,就可以开辟一条理解生活的路。 在一个害怕表现出对低级品位不敬的时代,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称得上伟大?《伟大的电影3》中100部佳作,选自罗杰·伊伯特生命即将画上句点之时,这是情真意切的推荐,不卑不亢的批评。 一句话唤出一个场景, 一部电影打开一扇窗。好的电影使人明智,能够让人跟那些与自己生活迥异的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伟大的电影3》是伊伯特留给每一位电影爱好者的遗赠,因为他对每一位读者都有所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