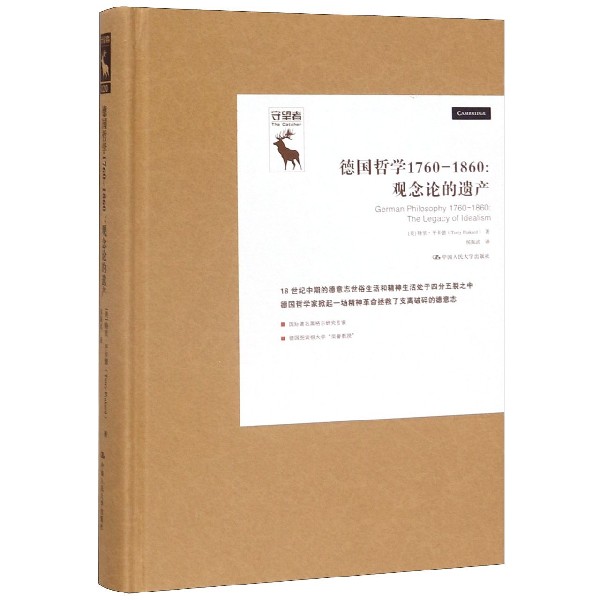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4.70
折扣购买: 德国哲学1760-1860--观念论的遗产(精)
ISBN: 9787300274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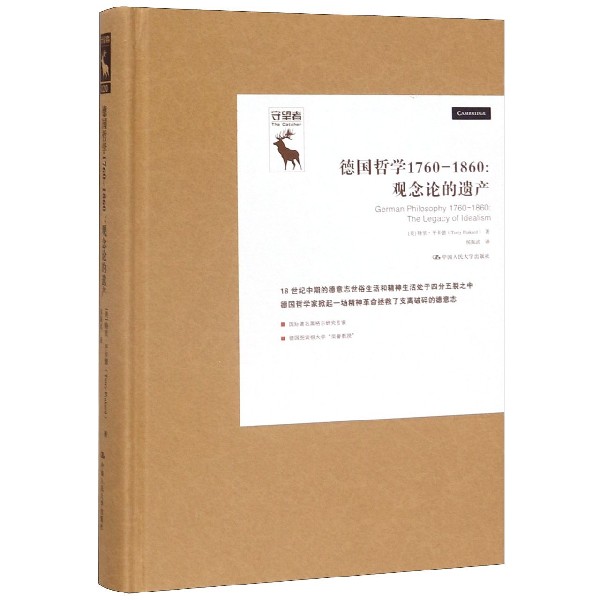
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黑格尔研究专家,美国乔治敦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荣誉教授”和“荣誉教师”,德国《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会顾问。学术兴趣在于从康德到现时的德国哲学,尤其是这个期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出版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可能性的解释》(1988)、《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理性的社会性》(1994)、《德国哲学(1760—1860):唯心主义的遗产》(2002)等。
书籍目录
目录
导言:“德意志”与德国哲学
部分康德与哲学革命
章哲学革命(一):人类自发性与自然秩序
自由与批判
判断
纯粹直观
概念与直观:先验演绎
概念与直观:几点结论
概念与直观:问题与图型
“理念”、自在之物和自由
第二章哲学革命(二):自律与道德秩序
从自发性到自由
从自由到自律
从自律到道德原则
自由与政治共同体:自律与美德
自律、宗教与伦理联邦
第三章哲学革命(三):审美鉴赏、目的论和世界秩序
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
规范性与审美判断
规范性与目的论的判断
第二部分继续的革命:后康德派
导言:观念论与法国大革命的现实
第四章18世纪80年代:直接的后康德反应:雅可比与莱因霍尔德
康德的地位和耶拿的崛起
指向康德的理性批判:雅可比
莱因霍尔德、“新大学”与对康德主义的捍卫
第五章18世纪90年代:费希特
第六章费希特之后的18世纪90年代:浪漫派对康德的接受(一):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施莱格尔
自我意识问题和后康德浪漫主义
自我意识问题:荷尔德林
自我意识问题:诺瓦利斯
施莱尔马赫:浪漫宗教与个体性的不可化约性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片断化生活的讽刺
共和主义的含糊之处
第七章1795—1809:浪漫派对康德的接受(二):谢林
谢林、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的思想
自然哲学
先验观念论
历史、“同一性”和艺术
重估自由
第八章1801—1807:另一位后康德派: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和非浪漫派的情感主义
道德与政治思想:重新定义康德
第三部分完成的革命?黑格尔
导言:后革命时代的德意志
第九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新脉络中的后康德主义
黑格尔的旅行
《精神现象学》
意识
自我意识
从征服到服从理性
现代生活的历史起源
宗教和知识
第十章黑格尔对理智和世界的分析:《逻辑学》
存在学说:超越荷尔德林
有限、无限和“观念论”
现代怀疑论和本质的世界
概念和推理
主体、客体和三段论
理念
第十一章自然与精神:黑格尔的体系
自然
精神概念
自由
制度与实现:客观精神
成为人意义为何:精神
第四部分反思中的革命
导言:疲惫与顺从,1830—1855
第十二章谢林的恢复企图:审查中的观念论
谢林1809年后的发展:中期
晚期哲学:谢林的柏林时期和“启示哲学”
第十三章“康德悖论”与现代的绝望: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
叔本华的后康德主义观念论:浪漫的悲观主义
克尔凯郭尔:后谢林的黑格尔主义?
结语:观念论的遗产
参考文献
索引
试读内容
763年,作为“次世界战争”称谓竞争者之一1的“七年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法国除了因战争而遭受巨大的财政损失之外,还被英国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并且再也没能恢复其领土——但奇怪的是,这场战争开始于并主要是在“德意志”境内进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果是,德意志的普鲁士国家转变为(或者可以说仅仅是被确认为)欧洲列强之一。不过,很难说这对于“德意志”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在那时,“德国”尚不存在,所谓的“德意志”不过是逐渐衰落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中讲德语的那部分的简称。至18世纪,曾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商贸中心的“德意志”(简称意义上的),已经变成欧洲舞台上的一个小角色。随着发现欧洲人所称的“新大陆”的航海活动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积极殖民,贸易转移到北大西洋,“德意志”早已大大丧失其经济活力。在三十年(1618—1648年)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后,按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德意志”被分割为一系列的诸侯邦国,它们有的相对大些,有的则和村庄一样小。这些诸侯邦国只是因名义上属于并受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与法律保护而聚合在一起,而后者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笑话,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因此它不是一个国家、联盟或条约组织,而完全是一个我们今天的政治术语难以描述的、完全自成一类的政治实体。从其早期现代历史来看,“德意志”很大程度上甚至并不是指一个文化整体;恰恰相反,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宗教上分裂为新教地区与天主教地区,所有的战争和对抗都源自这一分裂。2无论是新教的“德意志”人还是天主教的“德意志”人,都不认为他们共享一种共同文化;他们至多共享了一种(各式各样的)语言,并且只是偶然地在地理上相邻。
因此,在那一时期,“德意志”必然会被置于引号当中,因为那时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德国”。“德意志”变成德国只是后来的事。
然而,自1781年开始,德国哲学在一段时期内统治着欧洲哲学,它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甚至实际上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关于自身、自然、宗教、人类历史、知识本质、政治以及一般人类理智结构的理解。德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备受争议的,它总是难以被理解,并且几乎总是被称为德意志的——比如1816年威廉·哈兹里特在评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著作时,一开篇就写道:“这本书是德意志的”——并且清楚的是,“德意志的”这个词,有时候用于意指深层含义,有时候仅用于意指表面含义,而有时候则用于指责作者试图通过将某种“深层含义”掩藏在反启蒙主义语言中,以华而不实的方式将这种含义赋予自己的作品[1]
。不过,“德国”在当时并不存在的事实表明,几乎不可能诉诸它是“德意志的”(its being“German”)来做解释,似乎“是德意志的”(being“German”)这一点不能独立地解释这一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含义,那么在这一时期,被视作“德意志的”东西就是那种人人随意可用的东西,是由作家、政治家、宣传员,当然还有哲学家所发展和争辩的东西。
但是,“德意志的”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自己所必须面对的。在此期间,我们在如何讨论这些问题方面也许已经变得更有经验,已经更为清楚地知道对他们的问题的何种重复或回答又带来了新问题。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的问题,因此,德国哲学依然是现代哲学的本质部分。那么,德国哲学与“德意志”的关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