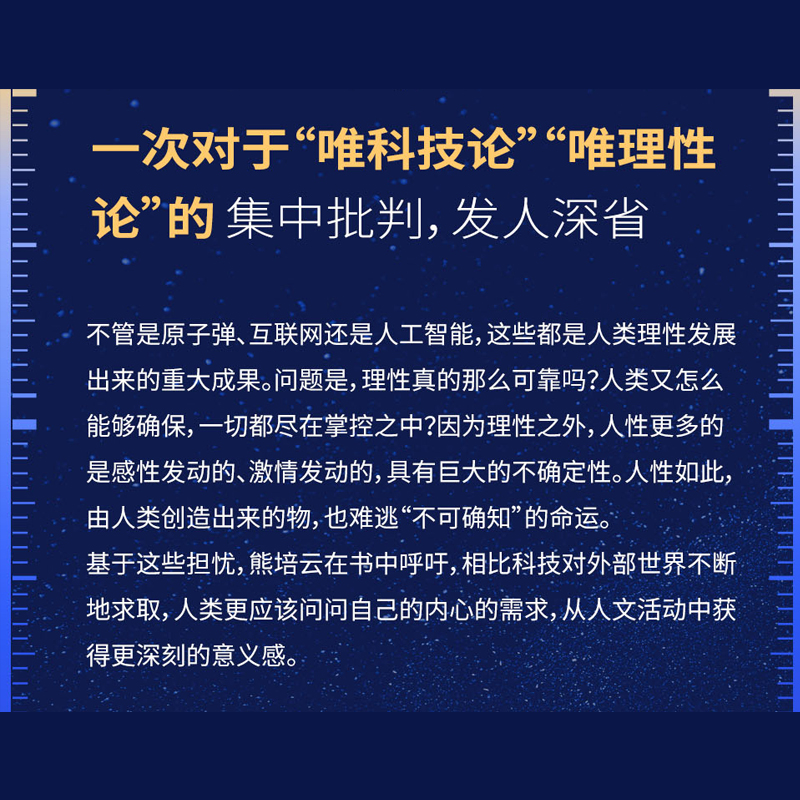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ISBN: 9787213117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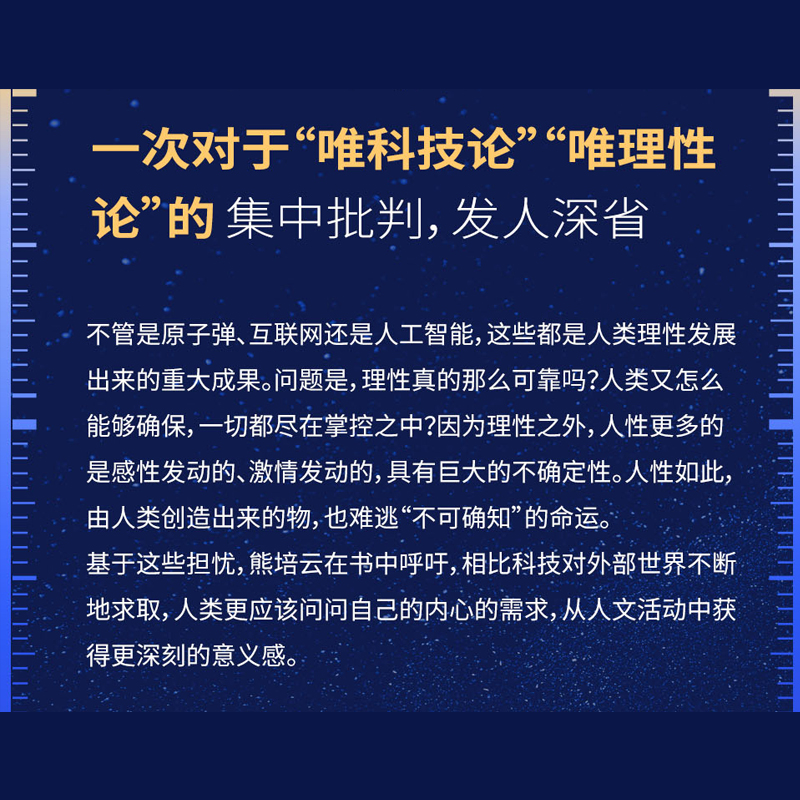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香港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之一。现执教于南开大学。
开篇 两根井绳 在我的记忆里收藏着两根井绳,它提醒我人的观念里有毒蛇。 第一根井绳是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份解密报告,那是在 2015 年。该报告介绍了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SAC)所制定的最高机密《1959 年原子弹需求研究》(Atomic Weapons Requirements Study For 1959)。据说这份需求研究总计达 800 多页,罗列了从柏林东部到中国全境的 1200 多个重要城市,美国计划使用数千枚原子弹对这些城市进行毁灭式打击,进而摧毁苏联的战争能力以保证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无 论中国是否与苏联并肩作战,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都将其视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并将中国的机场和城市列入目标名单。 而在诸多目标中有 117 条对应中国的城市,包括离我老家村庄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十公里的南昌。 看到这则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真假难辨”。显然在潜意识里我不太相信人类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同类。然而当我打开谷歌并且进入发布该解密报告的华盛顿大学下属国家安全档案馆(https://nsarchive.gwu.edu/)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一切都是真的,美国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此事。虽然悲剧没有发生,但当我看到如此充满恶意的计划,还是后背发凉了许久。 在诸多原始资料中,我特别找到了其中有南昌的一页,并且将它截屏保存下来。这是发生在我出生以前的事,也算是历史的走向之一,我都无法说我是幸存者。而就在此前一年的 2014 年,我刚刚出了一本名为《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的诗集。只能说,幸好当年命运之神没有把人类历史交到那帮战争狂人手里,否则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都不会来到这世上。 其实疯狂的年代出现什么样的战争狂人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无论如何,理智战胜了疯癫,传说中的这个末日计划没有得到实施,这是人类的幸运。而且,一旦度过黑暗岁月还会否极泰来。譬如,谁也没料到的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人类迎来了互联网,这个几近分崩离析的物种突然在虚拟世界走到了一起。至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初尝到了这种梦境一般的荣光。刚开始,世界各地的网民主要用 ICQ 软件,伴随着“I seek you”(我寻找你)的精神内涵与最新信息飘来时发出的清脆铃声,我偶然也认识一些外国的朋友。我喜欢敞开的世界。当然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发生日后的严重踩踏与质变,遗憾的是那些曾经密切联系过的朋友因为社交软件的迭代最后都不知所踪。防性战争”。 的确,如果梳理罗素的一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以怎样的手段消除极权主义罪恶方面也曾进退两难。罗素是和平主义者,他曾经反对英国参与“一战”而被罚款并且丢掉了三一学院的教职,之后又因反战被判刑 6 个月。“二战”爆发前,罗素支持英国的绥靖政策,直至终于意识到纳粹的危险时转而又拥护战争。“二战”结束后,信奉“死亡也比赤化好”的罗素甚至主张用核武器彻底摧毁苏联。有些历史不堪回首,有些现实不敢展望,诸多后怕让人毛骨悚然。罗素有一句话是极其诚恳的,那就是:“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1961 年,年近九十高龄的罗素因参与核裁军游行被拘禁 7 天。在此之前的 1955 年,罗素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该宣言最初称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由罗素起草。宣言签字者除了罗素是数学家、哲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外,其他十位著名科学家多数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这一切似乎印证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不过有理由怀疑,若非此时苏联已经有核武器,实现了所谓的“恐怖平衡”,或许罗素还不会加入核裁军的游行队伍中去。毕竟如果只是美国单方面保持核优势,这种优势对于维护罗素本人的爱憎是有益的。 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核战争”的说法在罗素生命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对于我们旁观人性以及人类的理性却是极好的例子。从逻辑上说,类似战争理由可以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虽然若干年后罗素为自己的言论做了辩解甚至予以否认后来又不得不承认,但这一切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人在某种恐惧或者憎恨(即使是罗素所说的“出于理智的憎恨”)的条件下,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或许,以理性自居的罗素也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内心深处还住了一个格瓦拉。是的,相较于坚持以审慎原则处理国际政治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此时的罗素可谓“恨令智昏”,完全把现代国家的世界道义和故乡伦理抛到一边了。 换句话说,参与编织前面提到的第一根井绳的人里面就有罗素。在类似逻辑下,我的家乡遭受核武器的打击是完全可能的。 这件事情让我消化了许久,它更让我相信了人性在善恶之间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也是这样,人性在欲望与恐惧之间摆荡,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人之行事,无论出于何种高尚或卑鄙的目的,本质上也只是基于人的欲望或者恐惧而已。其变幻无穷,如二进制原理衍生了复杂多变的数字文明。而人类所造就的罪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利益驱使,而且的确有部分人因此获益。 重要的是,如玛丽·雪莱所揭示的那样,人们作恶往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邪恶,而是因为他错把邪恶当作自己所要追求的幸福,甚至神圣的事业。吊诡的是,一个人不能理解他人的罪恶,却总是能理解自己的所有立场,哪怕他正在犯下滔天罪恶。 此其一。 另外,物性同样不可琢磨。这里的物性既是指物质的本质属性,也包括哲学意义上的内涵。 科学层面,物性指的是物质不需要经过物理、化学变化就表现出来的性质,如颜色、气味、密度、可溶性等。对于原初的物质,科学家借助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有了初步探查,比如了解水的构成,火何以出现或者熄灭。稍微复杂一些的,如电子、原子、夸克甚至量子纠缠等客观物质,人类也有所发现,彰显着科学的力量。 哲学层面,物性则可指物质在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作用、价值、善恶等伦理或道德属性。 具体而言,物亦可以分为两种,一为自然之物,二为人造之物。从前,人类通常会相信自己对人造之物的了解甚于自然之物。比如,人对一个凳子的了解多于树木本身。然而当人力与人心深层次介入到物,物性则可能变得深不可测。时至今日,尤其有了人工智能之后,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没有人的参与,物性更多决定于其物理属性。而在人类生活中的物,其物性还决定于人性,即人对物的使用。所谓“此之蜜糖,彼之砒霜”,鸦片既可以是药品,也可以是毒品;核聚变既可作能源,亦可作炸弹。如上所述,既然人性与物性皆有不可知的幽暗之地,人类就有可能一直行进于黎明之前的巨大沼泽之中。每一项重大发明的背后都安排了浩大的庆典。然而无论是好是坏,人类只能照单全收,包括随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异化。如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批评过的,我们甚至可以在自我毁灭中获得审美的快感。 物质的自然属性通常恒定不变,能给人某种现世安稳的感觉。就像山坡上的树,可能会遇到泥石流,但不会变成妖怪。而由人类创造并参与其中的原子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却随时在变化。这种流动的物性完全可能超出人的控制。 早在几十年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宇宙进化出一个“有良知的物种”是宇宙的成就,现在这个物种制造出了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有没有良知都令人畏惧。倘使人工智能真有觉醒的一天,开始从主观上决定自己的物性,甚至接近于变幻莫测的人性,这种接近又有什么不同? 人类同时经受着来自人性与物性的前所未有的考验。真正可怕的是,人类不仅有针对人类自身的古老的敌意,还有先发制人的冲动。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往往都伴随着你追我赶的武器化。由于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核裂变、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都有武器化的一支。 简而言之,人性与物性和我们正在迎接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正是本书思考与忧虑之起点。 文津图书奖得主熊培云重磅新作,构思十余年,终于面世。 不论是堪称人类之光的互联网,还是近年来你追我赶般投入研发的人工智能,如果说它们只有光明的一面,则未免偏颇,事实上,它们的负面性都已经显现。 本书中,熊培云先生从原子弹的研发投放与著名哲学家罗素讲起,这一事、一人分别反映了物性与人性的不可捉摸,继而展开了全书对于互联网、精英群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议题的探讨,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对于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诸多新型科技的发展,进行了一场脍炙人口的人文主义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