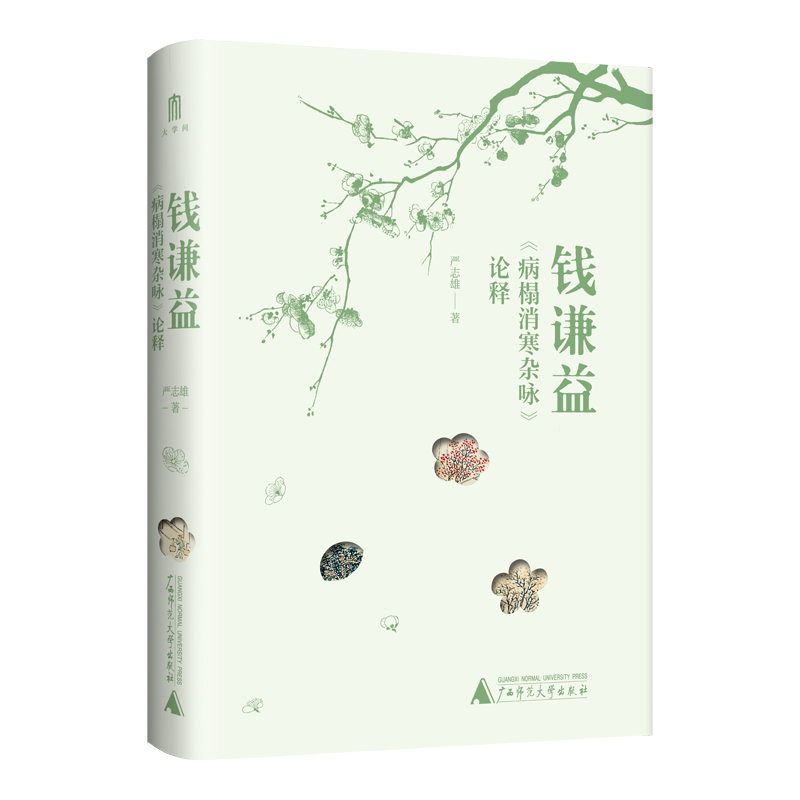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1.60
折扣购买: 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
ISBN: 978755987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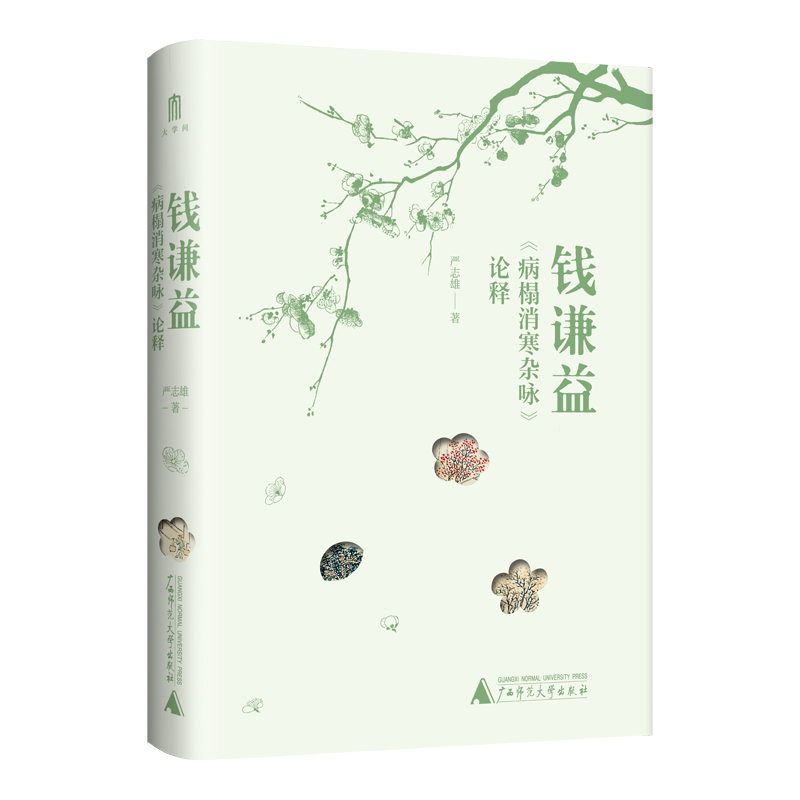
严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专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等;编有《千山诗集》、《落木菴诗集辑笺》、《瞿式耜未刊书牍》等。 (简要介绍:严志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
《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序笺释 牧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序曰: 癸卯(1663)冬,苦上气疾。卧榻无聊,时时蘸药汁写诗,都无伦次。升平之日,长安冬至后,内家戚里,竞传《九九消寒图》。取以铭诗,志《梦华》之感焉。亦名三体诗者,一为中麓体,章丘李伯华少卿罢官后,好为俚诗,嘲谑杂出,今所传《闲居集》是也;其二为少微体,里中许老秀才好即事即席为诗,杯盘梨枣,坐客赵、李,胪列八句中,李本宁叙其诗,殊似其为人;其三为怡荆体,怡荆者,江村刘老,庄家翁不识字,冲口哦诗,供人册笑,间有可为抚掌者。有诗一册,自谓诗无他长,但韵脚熟耳。余诗上不能寄托如中麓,下亦不能绝倒如刘老,揆诸季孟之间,庶几似少微体,惜无本宁描画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恶诗,何不近取佳者如归玄恭为四体耶?余冁然笑曰:有是哉!并识其语于后。腊月廿八日,东涧老人戏题。 【笺释】 牧斋诗序后署“东涧老人”。“东涧老人”或“东涧遗老”,牧斋别号,牧斋于顺治十二年(1655)始用之。牧斋于《题吉州施氏先世遗册》(1662)曾释此号之由来,曰:“乙未(1655)岁,(施)伟长游临海,谒先庙,拜武肃、忠懿、文僖画像,获观铁券及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东涧’二字。以周公卜宅时,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故有此款识也。谦益老耄昏庸,不克粪除先人之光烈,尚将策杖渡江,洒扫墓祠,拂拭宗器,以无忘忠孝刻文,乃自号东涧遗老,所以志也。”(《有学集》卷49) 牧斋诗序透露,《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写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冬。其时,牧斋八十二岁。诗序落款日期为“腊月廿八日”。癸卯年十二月廿八日为公元1664年1月25日,而牧斋殁于康熙三年甲辰五月二十四日,公元为1664年6月17日。由此可知,自《病榻消寒杂咏》组诗辍简至牧斋撒手人寰,相距仅四月余而已。牧斋一生诗作以此压轴,《有学集》所收牧斋诗亦止于本题。牧斋病榻缠绵,赋诗“消寒”,一咏再咏而至四十六章,可云富矣。(组诗最后二章,牧斋自注云:“元旦二首。”知系写于牧斋序诗后数日之甲辰年元旦。) 《病榻消寒杂咏》诗序语调诙谐幽默,似即兴而发,信手拈来。然牧斋诗题“消寒”一语,实有沉痛寓意。画《九九消寒图》,富贵人家“升平之日”事也,而牧斋撮其语“以铭诗”,却为寄托“《梦华》之感”,则追忆往昔升平岁月、心伤国变沧桑乃其弦外之音矣。《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生长北宋末年,长住汴京,北宋覆亡后南逃,晚年追忆旧京繁华模样,乃有《梦华录》之作。于此,不妨借古喻今,以孟元老序《梦华录》之语,转喻牧斋今日之怀抱。孟氏云:“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收入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第7册) “三体诗”云云,牧斋杜撰之词耳。“中麓体”,李开先(1502—1568)四十岁罢官后所制《闲居集》之风貌,“嘲谑杂出”之“俚诗”。牧斋《列朝诗集小传》称李“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丁集上“李少卿开先”)言下之意,不无讥弹。今考明嘉靖间,唐顺之(1507—1560)等出而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复古主义。李开先为诗文词曲,反模拟蹈袭,与唐等互通声气,颇为密切。于此一端,牧斋颇为赞赏。虽然,犹以其作“多流俗琐碎”为憾。此处则谓李诗有“寄托”,为己所“不能”。则其“寄托”者何?牧斋《初学集》中有《跋一笑散》一文,谓“其自序以谓无他长,独长于词,远交王渼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资而忘世,乐而忘老。……又曰: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呜呼!其尤可感也!”(《初学集》卷85)观此则牧斋或自谦不如李开先之能以文字游戏人生、消遣岁月,文酒词曲自乐而“老豪杰”于诙谐调笑之俚语中。则牧斋此“不能”,乃人生情调之抉择、个人情性之不同,非谓己之制作不如中麓体嘲谑杂出之鄙俚也。 “少微体”,老秀才“即事即席”之作,“近取诸身”,眼前寻常物事,身边张三李四,亦可入诗,演成八句一律。与“少微体”创作机制相近者“怡荆体”,庄家翁刘老不识字,冲口吟哦,诙谐滑稽,偶有天趣。牧斋谓己作“不能绝倒如刘老”,纯系戏语,可勿论。三体相较,牧斋自揣“庶几似少微体”,又谓“李本宁叙其诗,殊似其为人”。则“少微体”率性自在,以能显露个人性情面貌,而又不失为艺事为胜矣。牧斋颇以“无本宁描画”,叙己之诗为憾。本宁者,明季名臣李维桢(1547—1626)是也。李负文名于当世,唯牧斋对李诗文之“品格”不无微词。《列朝诗集小传》评李维桢云:“自词林左迁,海内谒文者如市,洪裁艳词,援笔挥洒,又能骫骳曲随,以属厌求者之意。其诗文声价腾涌,而品格渐下。余志其墓云:‘公之文章固已崇重于当代矣,后世当有知而论之者。’亦微词也。”(丁集上“李尚书维桢”)然则牧斋又缘何于诗序中抒发欲得李氏为己叙诗之愿望?除写活少微体许老秀才之面目外,对牧斋而言,李维桢复象征一业已消逝而教人怀缅之世代。数载以前,牧斋曾于《邵潜夫诗集序》(1660?)中云:“通州邵潜夫,以诗名万历中,为云杜李本宁,梁溪邹彦吉所推许。乙卯(1615)之秋,潜夫挟彦吉书谒余,不遇而去。迨今四十五年,潜夫附书渡江,以诗集见贻。……当鸿朗盛世,本宁以词林宿素,自南都来访彦吉及余,参会金昌、惠山之间。彦吉山居好客,园林歌舞,清妍妙丽,宾从皆一时胜流,觞咏杂沓。由今思之,则已为东都之燕喜、西园之宴游,灰沉梦断,迢然不可复即矣。……潜夫诗和平婉丽,规摹风雅,自以七叶为儒,行歌采薇,而绝无嘲啁噍杀之音。读潜夫之集,追思本宁、彦吉,升平士大夫,儒雅风流,仿佛在眼。于乎!其可感也!余每过彦吉园亭,回首昔游,天均之堂,塔光之榭,往者传杯度曲,移日分夜之处,胥化为黑灰红土。与旧客云间徐叟,杖藜指点,凄然别去。”(《有学集》卷19)牧斋之思怀李维桢,以李能唤起一“鸿朗盛世”“升平士大夫”文酒风流之年代。李诗文“品格”之高下与否,已不复至关重要之考虑矣。追溯李维桢身影,牧斋能回首来时路,重认己之风华岁月与夫天崩地坼前之“鸿朗盛世”。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明清之际,钱谦益为文坛一代宗师,黄宗羲形容他“四海宗盟五十年”。然而因乾隆皇帝的“斧钺之诛”,钱谦益长期以来被视作“贰臣”,研究者也因此对其政治行为做泛历史、泛道德论的阐释。但是,政治行为批评、道德批评不能等同于文学批评,钱谦益赖以不朽的是其诗文。 《病榻消寒杂咏》是钱谦益生前最后一次的情感、思想袒露,里面不仅有大量老、病、寒的基调,也咏及其生平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大事,同时这也是钱谦益高超诗学技艺的体现。严志雄教授循着文本的形式、意象、修辞、寓意等细致体会,为我们再现了牧斋的性格、情感与内心底蕴。钱谦益《复遵王书》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此话本是钱谦益对钱曾的期许,若将此语移许本书作者,想必他亦会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