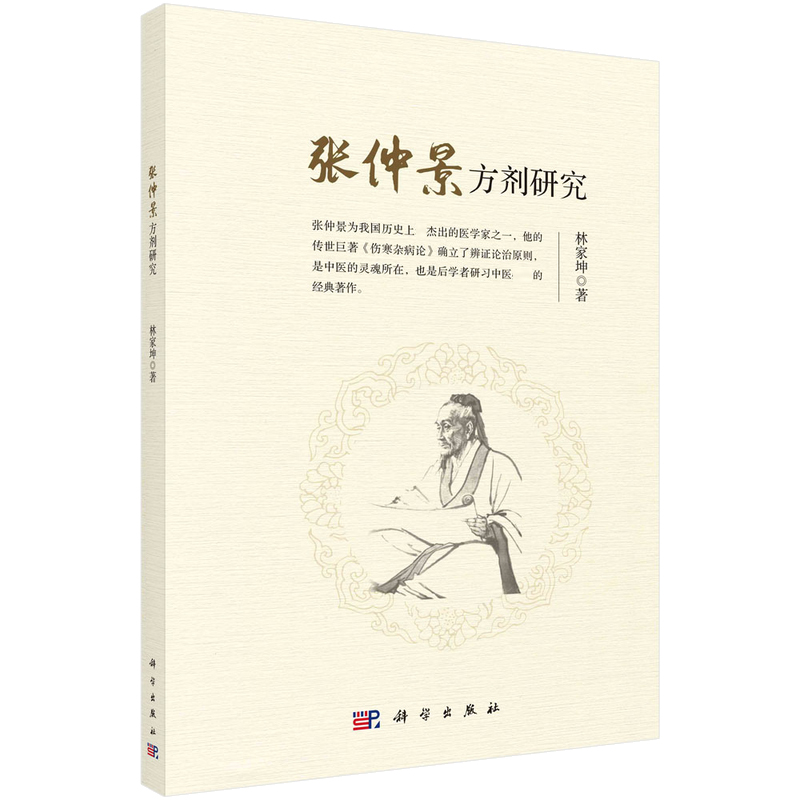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53.72
折扣购买: 张仲景方剂研究
ISBN: 9787030689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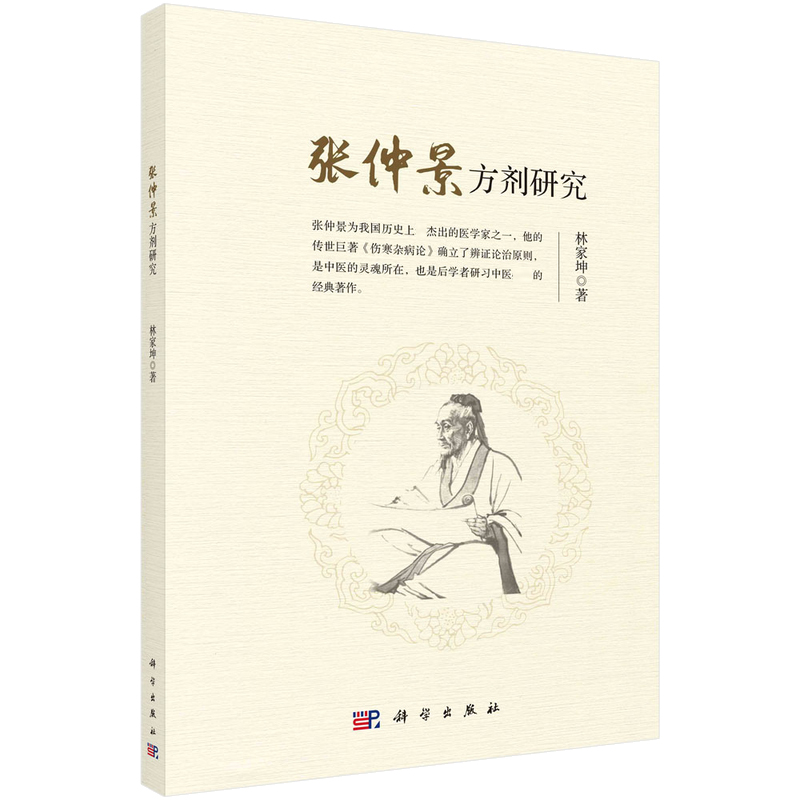
1 张仲景是方剂学的鼻祖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二书除缺方和重复方外,总共有360余方,其中使用药物达214种之多。书中不少有名方剂千百年来一直被历代医家沿用,以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且有较高的疗效。故后世医家把《伤寒杂病论》赞誉为“方书之祖”,其对后世方剂等发展影响甚大。
在药物剂型方面,《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中的剂型就有十余种。除以汤剂为主外,还有丸剂(抵当丸)、散剂(蜀漆散)、酒剂(红蓝药酒)、洗剂(狼牙汤、苦参汤)、熏剂(雄黄熏方)、坐药(蛇床子散)、肛门栓剂(蜜煎导)、阴道栓剂(矾石丸)、灌肠剂(猪胆汁导)等。不但在数量上比《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有所增加,而且在制剂方面也有很多充实和发展。如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所见丸剂的制作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丸法;一类是加料丸法。散剂也有两类制作方法:一是直接将药物研磨为散;一是将药物经煅烧炮制后再研成散。此成为后世药剂发展的先声。
张仲景对汤剂的煎煮方法、服药方法等均很重视,记载颇详。煎煮方法有先煎、后下、分煎、去渣再煎、沸水渍泡等。煎药的用水也各有所异,如清水、甘澜水、麻沸水、清浆水、潦水、泉水、井花水、醋水合煎、水酒合煎等。在服药方法上,如服桂枝汤要“啜热稀粥,以助药力”,应“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告诉我们服解表药要恰到好处。既要发汗又不可大汗,以达祛邪而不伤正之功。又如用大乌头煎时,在方后注明“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等语,示人以峻剂逐邪必须慎重,要视患者体质强弱而增减剂量,避免因逐邪太过而损伤正气,以致病未去而正气已伤,治疗就比较困难。
方剂学还包括了治疗方法的内容,中医治法虽多,但一般可以“八法”概言之,虽然八法内容早在《内经》中就已提出,而《伤寒杂病论》方剂中,却处处体现出八法的灵活运用,如麻黄汤、桂枝汤之汗法,瓜蒂散之吐法,承气汤之下法,小柴胡汤之和法,理中汤、四逆汤之温法,白虎汤之清法,鳖甲煎丸之消法,黄芪建中汤、肾气丸之补法,充实了中医治法的内容。
正因为张仲景制方法度严谨,简练精当,疗效显著,在方剂学方面,历来医家都给予仲景极高的评价。如南北朝时陶弘景说:“惟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清代喻嘉言说他是“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所以,张仲景是方剂学的鼻祖。
2 《伤寒论》制方用药研究
有关制方用药的记述,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典型代表性的方书莫过于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张仲景撰此书,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方药知识和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临床心得,提出了依证立法、依法立方、依方立药的原则,从而打开了脉证并治、有法有方的新局面,为后世临床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历代医家推崇为“众方之祖”。
任应秋教授谓书中所列方剂:“药味无多,配合得宜,经历二千余年历代医家的临床验证,疗效均甚确切,只要辨证准而用之无不如响斯应,实为方剂学中无出其右的典型。”因此,研究仲景制方用药特点,深有必要。
(一)《伤寒论》对方剂的命名规律
1. 以君药命名
《伤寒论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这是仲师为太阳伤寒表实证而设。既为风寒外束、营阴郁遏,则治当发汗解表宣肺。方中:麻黄辛苦而温,功能发汗散寒,宣肺平喘;桂枝解肌发表;杏仁宣肺止咳;甘草调和诸药。综观全方,当以麻黄为主药,正因为麻黄一味就具备了整方的功能,故方以麻黄命名而为“麻黄汤”。其他如乌梅丸、茵陈蒿汤、桂枝汤、葛根汤、黄芩汤、白头翁汤、麻子仁丸、猪苓汤等,皆准此。
2. 以方剂的全部药物命名
“伤寒若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伤寒误用吐下,损伤脾胃,中气一亏,转运失职,致水液停聚为饮,水气上逆,而成诸证,治当健脾利湿、化气行水。方用桂枝温阳化气,平冲降逆;苓桂相配,以通阳行气、淡渗利水,使治节之令行而水饮之邪去;白术健脾燥湿,则土壮水退,与苓桂相伍,同治中焦,化气利水;甘草调和诸药,与桂枝相合,辛甘化阳,消退阴翳。全方共奏温脾化饮之功,配伍精当,为温化水饮方之冠。正由于此,仲师以全部药物命名之,其他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苓甘五味姜辛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等,均此类也。
3. 以方剂的作用命名
此类方剂的命名在仲景方中见之亦较多,使人观方而能知疾病之机。如《伤寒论》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从文中可以看出,大承气汤乃为急下所设。方名“承气”,承乃承顺,气乃胃肠之气而言。因阳明燥实,壅塞胃肠,腑气不通,故治当以攻下燥屎,使胃气承顺,浊者得降,壅者得通,此正“承气”与“急下之”为一义也。正如柯琴谓“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于气之不顺,故攻积之剂必用行气以主之,亢则害,承乃制,此承气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气不伤,此承气之义也”。其他如大、小建中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排脓散,理中汤,抵当汤等,不一而足。
4. 以病机命名
所谓“辨证论治”就是随证而治,证之要点,在于审查病机。方剂以病机命名,使人一目了然,若疾病列于眼前,如大、小陷胸汤之类。成无己云:“结胸为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结胸曰陷胸汤。”正是由于此方有疗水饮热结居于胸中之功,故以陷胸名之,可谓精当之至。
5. 以主症命名
这类命名方法是以疾病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要症状而命名的。《伤寒论》318条云:“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首以“四逆”言之,不难看出,“四逆”乃证之主症,基于此,而以“四逆”命名之,其他如四逆汤等亦是。
6. 据药物或功效结合症状命名
这是以药物在方剂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或方剂之功效与其病证的主要症状结合的命名方法。《伤寒论》151条云:“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本证乃由血虚感寒,寒凝血滞,四肢失温所致。治当温经散寒,养血通脉,故君以当归辛温,血中气药以散内寒而温血。因为有“手足厥寒”,故亦予“四逆”命名之,实为药、症合而命名的代表。
《伤寒论》337条又云:“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 通脉四逆汤主之。”此为阴盛格阳之证,从“通脉四逆主之”来看,可知本方既能回阳救逆,又可疗因阴寒充斥、气血凝滞、阳气大虚、阴液内竭之“脉绝不通”。
7. 据古代哲学名词而命名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受古代哲学思想熏陶,在方剂命名上亦历历可见。如小青龙汤,名青龙者,“青”为东方木,主春,“龙”能兴云布雨,故以“青龙”名之,即所谓能使阳化气升、水布津散之意,正合该方解表化饮之功。实际上也是按方剂功效命名的一种。正如喻嘉言云:“名曰小青龙汤,盖取其翻波逐浪以归江海,不欲其兴云升天,而为云雨之意也。”其他如大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等,不再赘述。
(二)《伤寒论》制方用药中“药引”的玄奥
“药引”是方剂中特殊组成部分,《伤寒论》制方素有立法严谨、组方精细、遣药干练准确、丝丝入扣等特点,故其所引“药引”每每与主方浑然一体,具有画龙点睛之功,给人以精妙而无玄幽、灵活而不杂乱之感。《伤寒论》方中凡充“药引”者有三十余种之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①如生姜(生姜汁)、大枣(枣膏)、甘草、香豉、葱、新绛、桔梗、猪胆汁等,此类“药引”在方中或为药,或为引,视其地位而定;如甘草,在“炙甘草汤”、“甘草泻心汤”等方中作为主药而用,在“半夏泻心汤”中则为“药引”。②如热粥、粳米、鸡子黄、煮饼、胶饴、小麦、白饮、大麦粥、米粉、猪脂等物,皆为家常食物,性质十分平和,作为“药引”多能助药力,护胃气,有益无害。③如酒(清酒)、苦酒、蜜、盐等,多是些常用的炮制辅料,虽然其入药形式有别于他药,但作为“药引”以增效、抑毒、引行药势之意不变。④如浆水、泉水、井花水、甘澜水、暖水、马通汁、人尿、煅灶下灰等,入方为引常能增强方药的功效,故为仲景所习用,但此类“药引”在目前临床上的应用已经十分罕见了。
总之,经方所用“药引”多是些不易保存,或药店不备,需病家自理之品,一般都具有来源丰富、质地新鲜、简便易得、作用确切等特点,其实用性很明显,可见,仲景设置“药引”意于平淡中建奇效,绝非一些惯于故弄玄虚、滥用偏僻的江湖术士可比。
张仲景之方配置“药引”十分灵活,或于方中,或置方外,或佐,或使,每每与方融为一体,主意甚为明确,作用十分广泛,往往用一引而兼得数效。
如桂枝汤(《伤寒论》太阳病篇),以热稀粥为引,此方证本由营卫失调,复感风邪所致,症见汗出恶风。此时若以峻汗之品发之,必然导致“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反伤正气。故仲景仅以桂枝缓汗解肌为君,芍药敛阴和营为臣。意在得微汗即止之效,但终因桂枝力缓,又兼为芍药所制,尤恐药力不逮,特于方后嘱曰:“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许,以助药力。”此与发汗峻剂麻黄汤之“不须啜粥”相较,其意更明。诚如柯韵伯所言:“而精义又在啜稀热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则邪不复入,而啜粥以继药之后,则余邪不复留,复方之妙用又如此。”又如三物白散(《伤寒论》太阳病篇),以桔梗为引,此方为治寒实结胸之主方,是证病在上焦,《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思其治法应以吐为要。然世人皆曰其为峻下之剂,殊不知,方中巴豆虽为泻下峻品,而其涌吐之功亦不可没”,何以见得是方意在取吐呢?其妙在设桔梗为引,借其载药之功,导巴豆至上而取吐,故仲景特嘱曰:“病在膈上必吐。”如若邪壅上焦之证,治以下法,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
如白通加猪胆汁汤(《伤寒论》少阴病篇)为治阳微欲绝、阴邪肆虐猖獗之方,方中君以附子、干姜等辛热回阳之品尚嫌不急,何能反配寒凉之味?是证阳微阴盛已成格拒之势,欲急用热药拯危救难,反被拒之门外,故设人尿、猪胆汁等寒凉之品为引,意在取其同气相随、以破格拒、导阳入阴之效,药入少阴方可奏回阳之功。正如钱天来所云:“用咸寒下走之人尿,苦寒滑下之猪胆,以反从其阴寒之性,导姜附之辛热下行,为反佐入门之导行。”
综上所述,仲景制方遣药之妙在于精确简练,绝不滥用堆砌,故凡于细微之外即用“药引”补之,所设“药引”虽较平常,但用之即得增效、抑毒、调和药性、引药归经、反佐导药之功,且多以一物而兼得数效,毋庸置疑,若弃之不用,经方疗效即会受到影响。
(三)去性取用是《伤寒论》的制方特色
仲景制方严谨而灵巧,药之“去性取用”是其一大特色,为后人所尊崇。丹波元简谓方药有“性”、“用”之别,凡药物寒热温凉谓之性,补泻汗吐谓之用。但用凉泻或用温补即为性用兼取。又攻补同用,而治虚实相错,寒温并行,而治冷热不调,亦为性用兼取,有病但冷但热(“但”作“只”、“仅”解),而用药寒温并行者,是一取其性,一取其用,性用适用,自成一种方剂。中医临证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病情需要借助某种药物的显著作用,而此种药物的药性又与病证不相符合,甚至根本相反,因此必须加入制其药物的其他药物,以发挥方剂的最大效能,达到治病之目的,这样药物的“去性取用”,互相配伍的关系,散见于仲景的一些方剂之中,如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伤寒论》曰:“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其药物组成:麻黄四两,杏仁五十个,甘草二两,生石膏半斤,用于治疗热邪壅肺之咳喘。本方乃由麻黄汤去桂枝加石膏而成,是取其麻黄之用而去其麻黄之性,因方中辛甘大寒之石膏用量大于麻黄,监制麻黄辛温之性,而保留其平喘之功。由于本方采用“去性取用”的制方之法,而麻黄汤仅改一味药物,就使原为发汗辛温之峻剂,变为清肺定喘之大辛凉剂,后世医家多采用其药之配伍精良,而治疗多种疾病,如姜佐景用本方加减出入治一烂喉痧之危证。医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