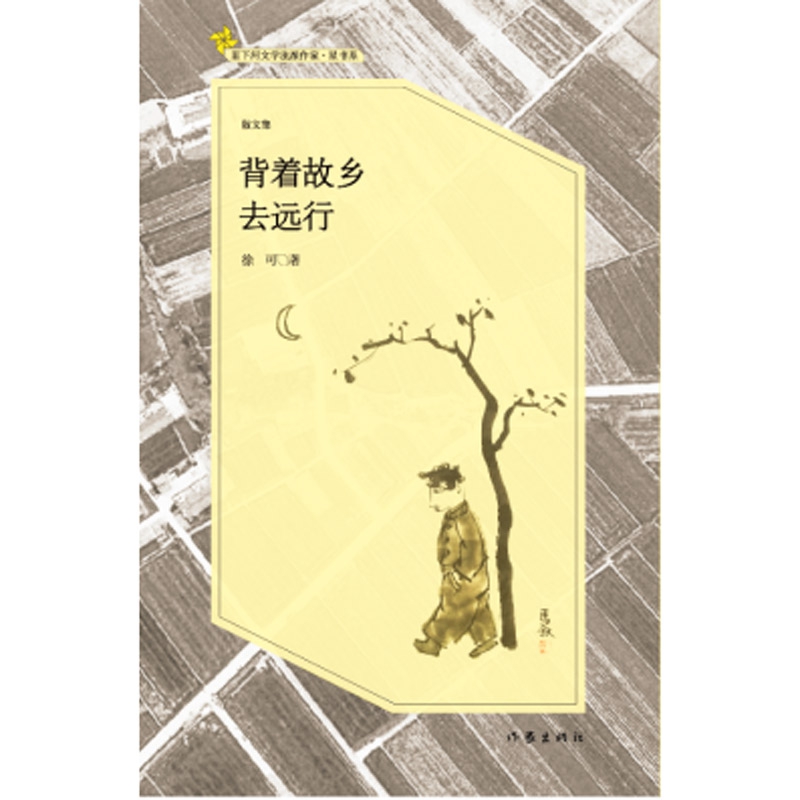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背着故乡去远行/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
ISBN: 978752120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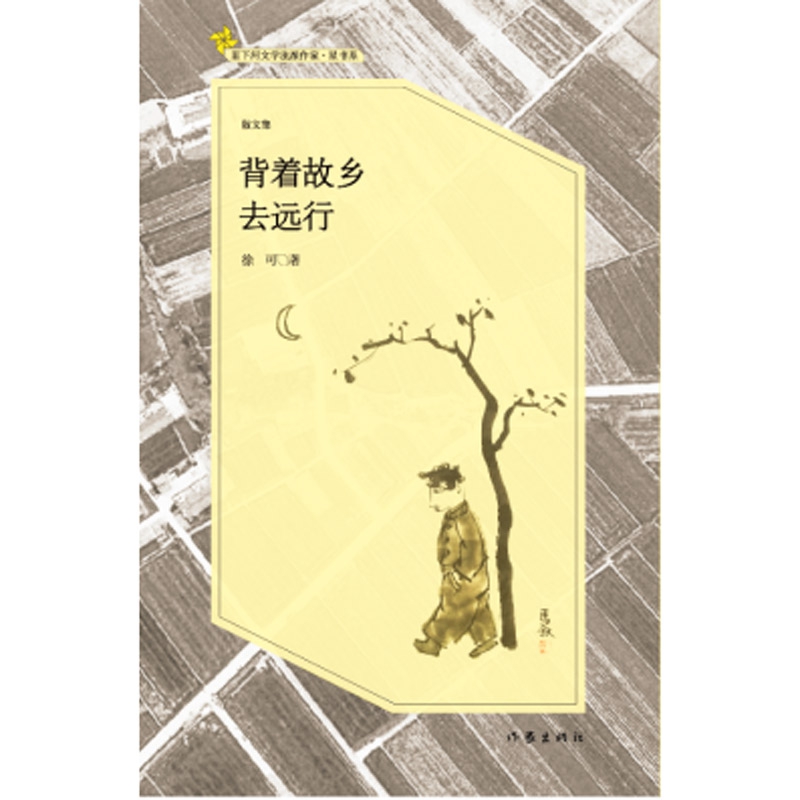
徐可,江苏如皋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启功研究会理事,**编辑。 致力于散文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主张真情写作,提倡弘扬中华美学传统。 著译有《三*有梦书当枕(之一、之二)》《三读启功》《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等。 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其中一些被选入各种选本及中小学语文课本。曾获中国新闻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海洋文学奖等。
**辑 故乡十忆 家乡,是我的 精神避难所 无论出走多年 不管走得多远 永远在那里 静静守候 家乡的刺槐树 ——故乡杂忆之二 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 一 在我心灵的海洋上,常常有绿色的波涛滚滚流过。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在我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有铮铮的乐声悠悠扬起。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是我的心里回荡着你绿色的进行曲?还是你超凡的生命力攫取了我的心?家乡的刺槐树,你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 二 刺槐树,是我的家乡的树。 在我的家乡,刺槐是随处可见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路边河畔,到处站满了刺槐坚实而腼腆的身影。一出门,如果看见树,那十有**就是刺槐。它是太平凡了,谁会注意它呢? 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不能不惊叹于刺槐的美。挺拔的树干,粗糙的皮肤,尖利的小刺,繁茂的树冠。这是一种阳刚之美,一种野性之美,一种奋发向上、充满勃勃生机的美。 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内,我看见过一株奇特的古树——严格地说,是两棵树,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渐渐合而为一,成为有名的“连理树”。那千古的奇观,吸引了不少的游人。许多人在这里流连、照相。而我却忽然想起家乡的刺槐来了。刺槐也是美的呀,为什么没有人给它照相呢? 因为刺槐朴素?因为刺槐的满身尖刺? 三 小时候,我曾经从别处挖来一棵幼小的刺槐树苗,栽在我家屋后的小竹园边。粗心的我,以后竟再也没有照料过它,连一次水也没给它浇过,**忘了它的存在。 好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有**,父亲说:“园子里那棵刺槐太大了,影响竹子生长了,把它砍了吧。”我随父亲去帮忙。看着树,我忽然愣住了。我的记忆之火复燃了。这不是我栽下的那棵树吗?长这么大了,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呢?它是怎样成长的呢? 我仰视着这棵刺槐。它的树冠是那样大,突出于竹林之上,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享*着充分的阳光。我想,它的根一定也很发达。刺槐,它不求助于人类,全靠自己努力,上承*着温暖的阳光,下汲取着足够的养分,是自己长大成材的呀。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的刺槐树林。它们是怎样长起来的呢?是萌芽于飞鸟嘴里掉落的树籽?还是孕育于春风吹来的果实?或是由我一样粗心的人栽种?我相信,它们的成长道路一定跟这棵刺槐相同。 刺槐,是大地的儿子。 四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旁有一座小土山,上面遍布着刺槐树。哦,那可是我们的乐园呀!每当下课或者放学后,我们就爬上土山,在树林里捉迷藏、玩打仗。那时候,学生要学工学农学*,我们常常“行*拉练”,也大多在这土山上钻树林。 后来,公社忽然调集了大批民工来削平土山了。刺槐被砍光了,土山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据说,这是为了大办农业。农民们并不满意,我们*不满意了。唉,我们失去了乐园呀!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了,刺槐,岂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它的用处可大了。且不说为劳乏的农人提供阴凉、为破旧的*屋挡风遮雨吧,它还是打家具、盖房屋的好材料呢。我们上学用的课桌、凳子,都是用刺槐木做的。尽管时间久了,容易变形,但人们还是乐意用它。它适应力强,生长快而又实用。桌子或者凳子坏了,随意伐倒一棵刺槐,很快就**辑 故乡十忆 家乡,是我的 精神避难所 无论出走多年 不管走得多远 永远在那里 静静守候 家乡的刺槐树 ——故乡杂忆之二 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 一 在我心灵的海洋上,常常有绿色的波涛滚滚流过。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在我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有铮铮的乐声悠悠扬起。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是我的心里回荡着你绿色的进行曲?还是你超凡的生命力攫取了我的心?家乡的刺槐树,你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 二 刺槐树,是我的家乡的树。 在我的家乡,刺槐是随处可见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路边河畔,到处站满了刺槐坚实而腼腆的身影。一出门,如果看见树,那十有**就是刺槐。它是太平凡了,谁会注意它呢? 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不能不惊叹于刺槐的美。挺拔的树干,粗糙的皮肤,尖利的小刺,繁茂的树冠。这是一种阳刚之美,一种野性之美,一种奋发向上、充满勃勃生机的美。 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内,我看见过一株奇特的古树——严格地说,是两棵树,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渐渐合而为一,成为有名的“连理树”。那千古的奇观,吸引了不少的游人。许多人在这里流连、照相。而我却忽然想起家乡的刺槐来了。刺槐也是美的呀,为什么没有人给它照相呢? 因为刺槐朴素?因为刺槐的满身尖刺? 三 小时候,我曾经从别处挖来一棵幼小的刺槐树苗,栽在我家屋后的小竹园边。粗心的我,以后竟再也没有照料过它,连一次水也没给它浇过,**忘了它的存在。 好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有**,父亲说:“园子里那棵刺槐太大了,影响竹子生长了,把它砍了吧。”我随父亲去帮忙。看着树,我忽然愣住了。我的记忆之火复燃了。这不是我栽下的那棵树吗?长这么大了,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呢?它是怎样成长的呢? 我仰视着这棵刺槐。它的树冠是那样大,突出于竹林之上,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享*着充分的阳光。我想,它的根一定也很发达。刺槐,它不求助于人类,全靠自己努力,上承*着温暖的阳光,下汲取着足够的养分,是自己长大成材的呀。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的刺槐树林。它们是怎样长起来的呢?是萌芽于飞鸟嘴里掉落的树籽?还是孕育于春风吹来的果实?或是由我一样粗心的人栽种?我相信,它们的成长道路一定跟这棵刺槐相同。 刺槐,是大地的儿子。 四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旁有一座小土山,上面遍布着刺槐树。哦,那可是我们的乐园呀!每当下课或者放学后,我们就爬上土山,在树林里捉迷藏、玩打仗。那时候,学生要学工学农学*,我们常常“行*拉练”,也大多在这土山上钻树林。 后来,公社忽然调集了大批民工来削平土山了。刺槐被砍光了,土山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据说,这是为了大办农业。农民们并不满意,我们*不满意了。唉,我们失去了乐园呀!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了,刺槐,岂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它的用处可大了。且不说为劳乏的农人提供阴凉、为破旧的*屋挡风遮雨吧,它还是打家具、盖房屋的好材料呢。我们上学用的课桌、凳子,都是用刺槐木做的。尽管时间久了,容易变形,但人们还是乐意用它。它适应力强,生长快而又实用。桌子或者凳子坏了,随意伐倒一棵刺槐,很快就**辑 故乡十忆 家乡,是我的 精神避难所 无论出走多年 不管走得多远 永远在那里 静静守候 家乡的刺槐树 ——故乡杂忆之二 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 一 在我心灵的海洋上,常常有绿色的波涛滚滚流过。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在我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有铮铮的乐声悠悠扬起。那是你吗,家乡的刺槐? 是我的心里回荡着你绿色的进行曲?还是你超凡的生命力攫取了我的心?家乡的刺槐树,你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 二 刺槐树,是我的家乡的树。 在我的家乡,刺槐是随处可见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路边河畔,到处站满了刺槐坚实而腼腆的身影。一出门,如果看见树,那十有**就是刺槐。它是太平凡了,谁会注意它呢? 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不能不惊叹于刺槐的美。挺拔的树干,粗糙的皮肤,尖利的小刺,繁茂的树冠。这是一种阳刚之美,一种野性之美,一种奋发向上、充满勃勃生机的美。 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内,我看见过一株奇特的古树——严格地说,是两棵树,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渐渐合而为一,成为有名的“连理树”。那千古的奇观,吸引了不少的游人。许多人在这里流连、照相。而我却忽然想起家乡的刺槐来了。刺槐也是美的呀,为什么没有人给它照相呢? 因为刺槐朴素?因为刺槐的满身尖刺? 三 小时候,我曾经从别处挖来一棵幼小的刺槐树苗,栽在我家屋后的小竹园边。粗心的我,以后竟再也没有照料过它,连一次水也没给它浇过,**忘了它的存在。 好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有**,父亲说:“园子里那棵刺槐太大了,影响竹子生长了,把它砍了吧。”我随父亲去帮忙。看着树,我忽然愣住了。我的记忆之火复燃了。这不是我栽下的那棵树吗?长这么大了,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呢?它是怎样成长的呢? 我仰视着这棵刺槐。它的树冠是那样大,突出于竹林之上,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享*着充分的阳光。我想,它的根一定也很发达。刺槐,它不求助于人类,全靠自己努力,上承*着温暖的阳光,下汲取着足够的养分,是自己长大成材的呀。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的刺槐树林。它们是怎样长起来的呢?是萌芽于飞鸟嘴里掉落的树籽?还是孕育于春风吹来的果实?或是由我一样粗心的人栽种?我相信,它们的成长道路一定跟这棵刺槐相同。 刺槐,是大地的儿子。 四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旁有一座小土山,上面遍布着刺槐树。哦,那可是我们的乐园呀!每当下课或者放学后,我们就爬上土山,在树林里捉迷藏、玩打仗。那时候,学生要学工学农学*,我们常常“行*拉练”,也大多在这土山上钻树林。 后来,公社忽然调集了大批民工来削平土山了。刺槐被砍光了,土山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据说,这是为了大办农业。农民们并不满意,我们*不满意了。唉,我们失去了乐园呀!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了,刺槐,岂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乐园,它的用处可大了。且不说为劳乏的农人提供阴凉、为破旧的*屋挡风遮雨吧,它还是打家具、盖房屋的好材料呢。我们上学用的课桌、凳子,都是用刺槐木做的。尽管时间久了,容易变形,但人们还是乐意用它。它适应力强,生长快而又实用。桌子或者凳子坏了,随意伐倒一棵刺槐,很快就能做出新的。人们喜爱的是它的朴素、实用。 再说说刺槐花吧。这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淡雅、素洁。每到夏季,刺槐花一串一串地开了。远远望去,像漫天飘飞的柳絮,似覆盖树枝的雪花,整个村庄都成了花的海洋。刺槐花,不但美,而且是一种可口的小菜。摘回去,炒着吃,烙饼吃,都行,清甜中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小时候,家家都穷。春夏之季,青黄不接,刺槐花为多少人家解决过口粮不足的难题啊。现在想起来,回忆中还带着淡淡的香气呢。 刺槐还有*大的用处呢:它的茎、皮、根、叶、花、果实,都可入药,为人们医治疾病。刺槐叶是很好的饲料,无论是鲜叶还是枯落叶,都为牲畜所喜食。刺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的“槐花蜜”,就是蜜蜂采集刺槐花蜜酿成的。可以说,刺槐全身都是宝,一点废料都没有。 刺槐,你要求于人类的甚少,可为什么能给人类贡献那么多呢? 五 儿时的小伙伴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家的刺槐树吗?现在可是少见了。 是的。如今在我的家乡,已经难觅刺槐的身影了。这些年来,家乡的变化可大了。低矮、破旧的*屋不见了,代之以漂亮、舒适的瓦房;人们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与之相伴的,是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益恶化。清澈见底、鱼虾嬉戏的小河,变成了污浊不堪、鱼虾不生的臭水沟;道路两旁成排的刺槐不见了,硬邦邦的水泥路在太阳底下蒸腾着窒人的热气。刺槐树哪儿去了?似乎谁也说不明白。问起来,答曰:现在谁还用刺槐? 可是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我是在刺槐的怀抱中长大的呀,我能忘记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东西,独不能忘记家乡的刺槐!虽然没有刺槐那样健壮的体魄,可它坚强的性格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这么多年来不畏艰难,一路前行。我要用我这支无力的笔,为故乡的刺槐写下一点苍白的文字,怀念心中那永远的绿色! 六 刺槐树也值得写吗?那么土气的树? 怎么说呢,朋友?有人歌颂那参天的大树,也有人赞美那贴地的小*;有人喜爱那雍容华贵的牡丹,也有人怜爱那质朴无华的野花。我身上至少还有刺槐淡淡的影子,我的笔下当然可以流出刺槐绿色的歌。 七 让那绿色的波涛从我心灵的海洋中涌动吧,让它荡涤我的心灵;让那铮铮的乐声从我感情的琴弦上扬起吧,让它砥砺我的意志;让家乡的刺槐——那绿色的灵魂,永远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田…… 1984年 别 情 ——故乡杂忆之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 那**凌晨,正是黎明前*黑暗的时刻,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亲人,踏上了赴校的漫漫长途。 姐姐特地从家里赶来为我送行——把正在生病的一岁的儿子丢在家里,来为我送行。 动身前**的晚上,家里人都到深夜才睡。本来,接到通知书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父亲母亲不放心,生怕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母亲说:“到了北京可不比在县里读书……”说着,眼眶又红了。 在父母亲的催促下,我和哥哥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明天要早起去长途汽车站。我躺在*上,哪里睡得着?只听见外屋里父亲、母亲和姐姐的低语声,还有隐隐约约的叹息声。一时,外面又有了雨声,能做出新的。人们喜爱的是它的朴素、实用。 再说说刺槐花吧。这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淡雅、素洁。每到夏季,刺槐花一串一串地开了。远远望去,像漫天飘飞的柳絮,似覆盖树枝的雪花,整个村庄都成了花的海洋。刺槐花,不但美,而且是一种可口的小菜。摘回去,炒着吃,烙饼吃,都行,清甜中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小时候,家家都穷。春夏之季,青黄不接,刺槐花为多少人家解决过口粮不足的难题啊。现在想起来,回忆中还带着淡淡的香气呢。 刺槐还有*大的用处呢:它的茎、皮、根、叶、花、果实,都可入药,为人们医治疾病。刺槐叶是很好的饲料,无论是鲜叶还是枯落叶,都为牲畜所喜食。刺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的“槐花蜜”,就是蜜蜂采集刺槐花蜜酿成的。可以说,刺槐全身都是宝,一点废料都没有。 刺槐,你要求于人类的甚少,可为什么能给人类贡献那么多呢? 五 儿时的小伙伴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家的刺槐树吗?现在可是少见了。 是的。如今在我的家乡,已经难觅刺槐的身影了。这些年来,家乡的变化可大了。低矮、破旧的*屋不见了,代之以漂亮、舒适的瓦房;人们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与之相伴的,是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益恶化。清澈见底、鱼虾嬉戏的小河,变成了污浊不堪、鱼虾不生的臭水沟;道路两旁成排的刺槐不见了,硬邦邦的水泥路在太阳底下蒸腾着窒人的热气。刺槐树哪儿去了?似乎谁也说不明白。问起来,答曰:现在谁还用刺槐? 可是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我是在刺槐的怀抱中长大的呀,我能忘记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东西,独不能忘记家乡的刺槐!虽然没有刺槐那样健壮的体魄,可它坚强的性格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这么多年来不畏艰难,一路前行。我要用我这支无力的笔,为故乡的刺槐写下一点苍白的文字,怀念心中那永远的绿色! 六 刺槐树也值得写吗?那么土气的树? 怎么说呢,朋友?有人歌颂那参天的大树,也有人赞美那贴地的小*;有人喜爱那雍容华贵的牡丹,也有人怜爱那质朴无华的野花。我身上至少还有刺槐淡淡的影子,我的笔下当然可以流出刺槐绿色的歌。 七 让那绿色的波涛从我心灵的海洋中涌动吧,让它荡涤我的心灵;让那铮铮的乐声从我感情的琴弦上扬起吧,让它砥砺我的意志;让家乡的刺槐——那绿色的灵魂,永远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田…… 1984年 别 情 ——故乡杂忆之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 那**凌晨,正是黎明前*黑暗的时刻,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亲人,踏上了赴校的漫漫长途。 姐姐特地从家里赶来为我送行——把正在生病的一岁的儿子丢在家里,来为我送行。 动身前**的晚上,家里人都到深夜才睡。本来,接到通知书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父亲母亲不放心,生怕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母亲说:“到了北京可不比在县里读书……”说着,眼眶又红了。 在父母亲的催促下,我和哥哥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明天要早起去长途汽车站。我躺在*上,哪里睡得着?只听见外屋里父亲、母亲和姐姐的低语声,还有隐隐约约的叹息声。一时,外面又有了雨声,能做出新的。人们喜爱的是它的朴素、实用。 再说说刺槐花吧。这是一种白色的小花,淡雅、素洁。每到夏季,刺槐花一串一串地开了。远远望去,像漫天飘飞的柳絮,似覆盖树枝的雪花,整个村庄都成了花的海洋。刺槐花,不但美,而且是一种可口的小菜。摘回去,炒着吃,烙饼吃,都行,清甜中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小时候,家家都穷。春夏之季,青黄不接,刺槐花为多少人家解决过口粮不足的难题啊。现在想起来,回忆中还带着淡淡的香气呢。 刺槐还有*大的用处呢:它的茎、皮、根、叶、花、果实,都可入药,为人们医治疾病。刺槐叶是很好的饲料,无论是鲜叶还是枯落叶,都为牲畜所喜食。刺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的“槐花蜜”,就是蜜蜂采集刺槐花蜜酿成的。可以说,刺槐全身都是宝,一点废料都没有。 刺槐,你要求于人类的甚少,可为什么能给人类贡献那么多呢? 五 儿时的小伙伴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家的刺槐树吗?现在可是少见了。 是的。如今在我的家乡,已经难觅刺槐的身影了。这些年来,家乡的变化可大了。低矮、破旧的*屋不见了,代之以漂亮、舒适的瓦房;人们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与之相伴的,是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益恶化。清澈见底、鱼虾嬉戏的小河,变成了污浊不堪、鱼虾不生的臭水沟;道路两旁成排的刺槐不见了,硬邦邦的水泥路在太阳底下蒸腾着窒人的热气。刺槐树哪儿去了?似乎谁也说不明白。问起来,答曰:现在谁还用刺槐? 可是我总也忘不了家乡的刺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填饱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我灰暗的童年,它给了我多少乐趣!我是在刺槐的怀抱中长大的呀,我能忘记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东西,独不能忘记家乡的刺槐!虽然没有刺槐那样健壮的体魄,可它坚强的性格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这么多年来不畏艰难,一路前行。我要用我这支无力的笔,为故乡的刺槐写下一点苍白的文字,怀念心中那永远的绿色! 六 刺槐树也值得写吗?那么土气的树? 怎么说呢,朋友?有人歌颂那参天的大树,也有人赞美那贴地的小*;有人喜爱那雍容华贵的牡丹,也有人怜爱那质朴无华的野花。我身上至少还有刺槐淡淡的影子,我的笔下当然可以流出刺槐绿色的歌。 七 让那绿色的波涛从我心灵的海洋中涌动吧,让它荡涤我的心灵;让那铮铮的乐声从我感情的琴弦上扬起吧,让它砥砺我的意志;让家乡的刺槐——那绿色的灵魂,永远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田…… 1984年 别 情 ——故乡杂忆之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 那**凌晨,正是黎明前*黑暗的时刻,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亲人,踏上了赴校的漫漫长途。 姐姐特地从家里赶来为我送行——把正在生病的一岁的儿子丢在家里,来为我送行。 动身前**的晚上,家里人都到深夜才睡。本来,接到通知书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父亲母亲不放心,生怕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母亲说:“到了北京可不比在县里读书……”说着,眼眶又红了。 在父母亲的催促下,我和哥哥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明天要早起去长途汽车站。我躺在*上,哪里睡得着?只听见外屋里父亲、母亲和姐姐的低语声,还有隐隐约约的叹息声。一时,外面又有了雨声,开始很小,后来竟渐渐大起来,雨点打在树叶、竹叶上,“啪啪”地响。一会儿,母亲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站在*边看我;我便侧身朝里,很粗地呼吸,假装睡着了。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会儿,又有了轻轻的脚步声——母亲吸着鼻子出去了。我就这么睁着眼睛躺着,听着这些声音,想象着有生以来的**次远行,心里很迷乱,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翻来覆去,把*板压得吱吱叫。 不知何时才迷迷糊糊地入睡,不知何时又迷迷糊糊地醒来。窗外仍是滴滴答答的雨声,和呜咽似的风声。外屋仍亮着灯。鼻息中是饭香、菜香。只听母亲说道:“把孩子叫醒吧。” “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早着呢。”这是父亲的声音。 “苦就苦这么一回吧,赶不上车就麻烦了。”母亲的话是无可奈何的。 父亲把我们叫起。母亲说,天下雨,路上恐怕不好走,不如早些动身,到学校再休息。 早饭很丰盛,是米饭、炖肉和炒菜。可是哪里吃得下!勉强吃了点。两个哥哥早已穿好雨衣,扶着自行车,在外面等着。父亲执意要送我们一程,也拿着手电筒,在外面等着。 该动身了。 姐姐帮我穿好雨衣。我站在门口,看着哥哥他们,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回过头来再看看屋里—— 桌上的煤油灯,大概灯油快干了,灯光渐渐地暗淡下去;摇曳的灯光下,屋里忽明忽暗。母亲坐在桌旁,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眼睛看着地上,定定的,无神的,一声不吭。姐姐坐在母亲身旁,眼眶红红的,也低着头。 我的脑子一刹那变得**迟钝,血液似乎凝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想不出了。好容易憋出一句: “妈,我走了。” 母亲似乎没有听见,仍定定地看着地上。好久,才低低地应了一声: “好的。”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我咬着嘴唇。姐姐也抬起头,吩咐我:“到学校立即写信回来。” “嗯。”我使劲地点了下头,不敢多语,一转身,便走进黑暗里,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上路了。 那时才凌晨四点多钟,天黑得很,不时地有一股凉风吹来,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旁边是条小河,河水静悄悄地沉在梦里;河边的芦苇也在风中摇曳而且低吟着了。 父亲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再后面就是推着自行车的大哥、二哥。雨衣在身上摩擦着,发出令人讨厌的“呼啦呼啦”的声音;自行车的链条“咯咯”地哼着,似乎想唱一支歌,但总也唱不全——因为烂泥巴不住地粘在车轮上。 父亲打着雨伞,在前面慢慢走着。手电筒的光束一闪一闪的;黑暗中,只看见他模糊的背影。但他的谨慎、小心便是黑夜也掩不住的。他走得那样慢,脚步是摸索着向前的。每遇着一个小水洼儿,就用手电筒一照,示意我们绕过去。我并没怎么踩到水洼,可他的脚上、腿上肯定溅了不少泥水。 出村了。 大哥对父亲说:“父啊,你回去吧,不用送了。”父亲抬头看看天,说:“再送一程吧。”又在头里走了。 这时,我浑身突然冷起来,如掉进冰窟窿里,直打哆嗦,牙齿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我回首望望村庄,村庄被夜的黑面纱裹着,不肯对我露出真面目。蒙蒙眬眬的,倒有点让人留恋。我想起了家中的母亲,这时该在灯下垂泪吧?——我的牙齿响得*厉害了。 又走了一程。天渐渐亮了。雨停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在哥哥们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停下了脚步。 “我回去了,”父亲看着我,说,“到校后立即写信回来。” 我说不出一个字开始很小,后来竟渐渐大起来,雨点打在树叶、竹叶上,“啪啪”地响。一会儿,母亲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站在*边看我;我便侧身朝里,很粗地呼吸,假装睡着了。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会儿,又有了轻轻的脚步声——母亲吸着鼻子出去了。我就这么睁着眼睛躺着,听着这些声音,想象着有生以来的**次远行,心里很迷乱,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翻来覆去,把*板压得吱吱叫。 不知何时才迷迷糊糊地入睡,不知何时又迷迷糊糊地醒来。窗外仍是滴滴答答的雨声,和呜咽似的风声。外屋仍亮着灯。鼻息中是饭香、菜香。只听母亲说道:“把孩子叫醒吧。” “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早着呢。”这是父亲的声音。 “苦就苦这么一回吧,赶不上车就麻烦了。”母亲的话是无可奈何的。 父亲把我们叫起。母亲说,天下雨,路上恐怕不好走,不如早些动身,到学校再休息。 早饭很丰盛,是米饭、炖肉和炒菜。可是哪里吃得下!勉强吃了点。两个哥哥早已穿好雨衣,扶着自行车,在外面等着。父亲执意要送我们一程,也拿着手电筒,在外面等着。 该动身了。 姐姐帮我穿好雨衣。我站在门口,看着哥哥他们,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回过头来再看看屋里—— 桌上的煤油灯,大概灯油快干了,灯光渐渐地暗淡下去;摇曳的灯光下,屋里忽明忽暗。母亲坐在桌旁,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眼睛看着地上,定定的,无神的,一声不吭。姐姐坐在母亲身旁,眼眶红红的,也低着头。 我的脑子一刹那变得**迟钝,血液似乎凝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想不出了。好容易憋出一句: “妈,我走了。” 母亲似乎没有听见,仍定定地看着地上。好久,才低低地应了一声: “好的。”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我咬着嘴唇。姐姐也抬起头,吩咐我:“到学校立即写信回来。” “嗯。”我使劲地点了下头,不敢多语,一转身,便走进黑暗里,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上路了。 那时才凌晨四点多钟,天黑得很,不时地有一股凉风吹来,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旁边是条小河,河水静悄悄地沉在梦里;河边的芦苇也在风中摇曳而且低吟着了。 父亲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再后面就是推着自行车的大哥、二哥。雨衣在身上摩擦着,发出令人讨厌的“呼啦呼啦”的声音;自行车的链条“咯咯”地哼着,似乎想唱一支歌,但总也唱不全——因为烂泥巴不住地粘在车轮上。 父亲打着雨伞,在前面慢慢走着。手电筒的光束一闪一闪的;黑暗中,只看见他模糊的背影。但他的谨慎、小心便是黑夜也掩不住的。他走得那样慢,脚步是摸索着向前的。每遇着一个小水洼儿,就用手电筒一照,示意我们绕过去。我并没怎么踩到水洼,可他的脚上、腿上肯定溅了不少泥水。 出村了。 大哥对父亲说:“父啊,你回去吧,不用送了。”父亲抬头看看天,说:“再送一程吧。”又在头里走了。 这时,我浑身突然冷起来,如掉进冰窟窿里,直打哆嗦,牙齿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我回首望望村庄,村庄被夜的黑面纱裹着,不肯对我露出真面目。蒙蒙眬眬的,倒有点让人留恋。我想起了家中的母亲,这时该在灯下垂泪吧?——我的牙齿响得*厉害了。 又走了一程。天渐渐亮了。雨停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在哥哥们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停下了脚步。 “我回去了,”父亲看着我,说,“到校后立即写信回来。” 我说不出一个字开始很小,后来竟渐渐大起来,雨点打在树叶、竹叶上,“啪啪”地响。一会儿,母亲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站在*边看我;我便侧身朝里,很粗地呼吸,假装睡着了。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会儿,又有了轻轻的脚步声——母亲吸着鼻子出去了。我就这么睁着眼睛躺着,听着这些声音,想象着有生以来的**次远行,心里很迷乱,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翻来覆去,把*板压得吱吱叫。 不知何时才迷迷糊糊地入睡,不知何时又迷迷糊糊地醒来。窗外仍是滴滴答答的雨声,和呜咽似的风声。外屋仍亮着灯。鼻息中是饭香、菜香。只听母亲说道:“把孩子叫醒吧。” “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早着呢。”这是父亲的声音。 “苦就苦这么一回吧,赶不上车就麻烦了。”母亲的话是无可奈何的。 父亲把我们叫起。母亲说,天下雨,路上恐怕不好走,不如早些动身,到学校再休息。 早饭很丰盛,是米饭、炖肉和炒菜。可是哪里吃得下!勉强吃了点。两个哥哥早已穿好雨衣,扶着自行车,在外面等着。父亲执意要送我们一程,也拿着手电筒,在外面等着。 该动身了。 姐姐帮我穿好雨衣。我站在门口,看着哥哥他们,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回过头来再看看屋里—— 桌上的煤油灯,大概灯油快干了,灯光渐渐地暗淡下去;摇曳的灯光下,屋里忽明忽暗。母亲坐在桌旁,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眼睛看着地上,定定的,无神的,一声不吭。姐姐坐在母亲身旁,眼眶红红的,也低着头。 我的脑子一刹那变得**迟钝,血液似乎凝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想不出了。好容易憋出一句: “妈,我走了。” 母亲似乎没有听见,仍定定地看着地上。好久,才低低地应了一声: “好的。”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我咬着嘴唇。姐姐也抬起头,吩咐我:“到学校立即写信回来。” “嗯。”我使劲地点了下头,不敢多语,一转身,便走进黑暗里,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上路了。 那时才凌晨四点多钟,天黑得很,不时地有一股凉风吹来,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旁边是条小河,河水静悄悄地沉在梦里;河边的芦苇也在风中摇曳而且低吟着了。 父亲在前面领路,我跟在后面,再后面就是推着自行车的大哥、二哥。雨衣在身上摩擦着,发出令人讨厌的“呼啦呼啦”的声音;自行车的链条“咯咯”地哼着,似乎想唱一支歌,但总也唱不全——因为烂泥巴不住地粘在车轮上。 父亲打着雨伞,在前面慢慢走着。手电筒的光束一闪一闪的;黑暗中,只看见他模糊的背影。但他的谨慎、小心便是黑夜也掩不住的。他走得那样慢,脚步是摸索着向前的。每遇着一个小水洼儿,就用手电筒一照,示意我们绕过去。我并没怎么踩到水洼,可他的脚上、腿上肯定溅了不少泥水。 出村了。 大哥对父亲说:“父啊,你回去吧,不用送了。”父亲抬头看看天,说:“再送一程吧。”又在头里走了。 这时,我浑身突然冷起来,如掉进冰窟窿里,直打哆嗦,牙齿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我回首望望村庄,村庄被夜的黑面纱裹着,不肯对我露出真面目。蒙蒙眬眬的,倒有点让人留恋。我想起了家中的母亲,这时该在灯下垂泪吧?——我的牙齿响得*厉害了。 又走了一程。天渐渐亮了。雨停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在哥哥们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停下了脚步。 “我回去了,”父亲看着我,说,“到校后立即写信回来。” 我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的牙齿在咯咯打架,我尽力咬紧牙关,不让父亲看出来。看着父亲往回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来。 “路上小心啊。这土路上不能骑就不要骑,到公路上蹬快点。” 说完,走了。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我的身子在颤抖。 到北京后,我便赶紧给家里写信,报告我旅途的情形。不久,接到哥哥的回信。他在信中说:“那天送走你后,回到家里,父亲便趴在*上大哭,我们也跟着流泪。我们长这么大还没见父亲哭过,这是头一回。……母亲也病倒了。那些*子,她硬是撑着为你准备行装,你一走她就倒下了。”过了些*子,父亲又来信说:“你妈妈和我很不放心,问你现在冬衣置全了没有?”捧读家书,泪光晶莹中,我似乎又看到了暗淡的灯光下,母亲无神的眼和黑暗中父亲模糊的背影…… 我闭上眼,不敢面对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背影…… 1984年 作者小志:这是三十年前的一篇文字。如今,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重读旧文,依然泣下。 2014年来。我的牙齿在咯咯打架,我尽力咬紧牙关,不让父亲看出来。看着父亲往回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来。 “路上小心啊。这土路上不能骑就不要骑,到公路上蹬快点。” 说完,走了。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我的身子在颤抖。 到北京后,我便赶紧给家里写信,报告我旅途的情形。不久,接到哥哥的回信。他在信中说:“那天送走你后,回到家里,父亲便趴在*上大哭,我们也跟着流泪。我们长这么大还没见父亲哭过,这是头一回。……母亲也病倒了。那些*子,她硬是撑着为你准备行装,你一走她就倒下了。”过了些*子,父亲又来信说:“你妈妈和我很不放心,问你现在冬衣置全了没有?”捧读家书,泪光晶莹中,我似乎又看到了暗淡的灯光下,母亲无神的眼和黑暗中父亲模糊的背影…… 我闭上眼,不敢面对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背影…… 1984年 作者小志:这是三十年前的一篇文字。如今,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重读旧文,依然泣下。 2014年来。我的牙齿在咯咯打架,我尽力咬紧牙关,不让父亲看出来。看着父亲往回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来。 “路上小心啊。这土路上不能骑就不要骑,到公路上蹬快点。” 说完,走了。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我的身子在颤抖。 到北京后,我便赶紧给家里写信,报告我旅途的情形。不久,接到哥哥的回信。他在信中说:“那天送走你后,回到家里,父亲便趴在*上大哭,我们也跟着流泪。我们长这么大还没见父亲哭过,这是头一回。……母亲也病倒了。那些*子,她硬是撑着为你准备行装,你一走她就倒下了。”过了些*子,父亲又来信说:“你妈妈和我很不放心,问你现在冬衣置全了没有?”捧读家书,泪光晶莹中,我似乎又看到了暗淡的灯光下,母亲无神的眼和黑暗中父亲模糊的背影…… 我闭上眼,不敢面对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背影…… 1984年 作者小志:这是三十年前的一篇文字。如今,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老了。可我总也忘不了那雨夜,忘不了父亲的背影,母亲的眼神……重读旧文,依然泣下。 2014年 “徐可的文字,取法自然,明净无尘,真诚恺切。是至高的书写,也是人生的法度。” ——贾平凹 “徐可的文章,观世态,知人心,有冷暖。” ——穆涛 “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徐可致力于美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其文章有情有识亦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