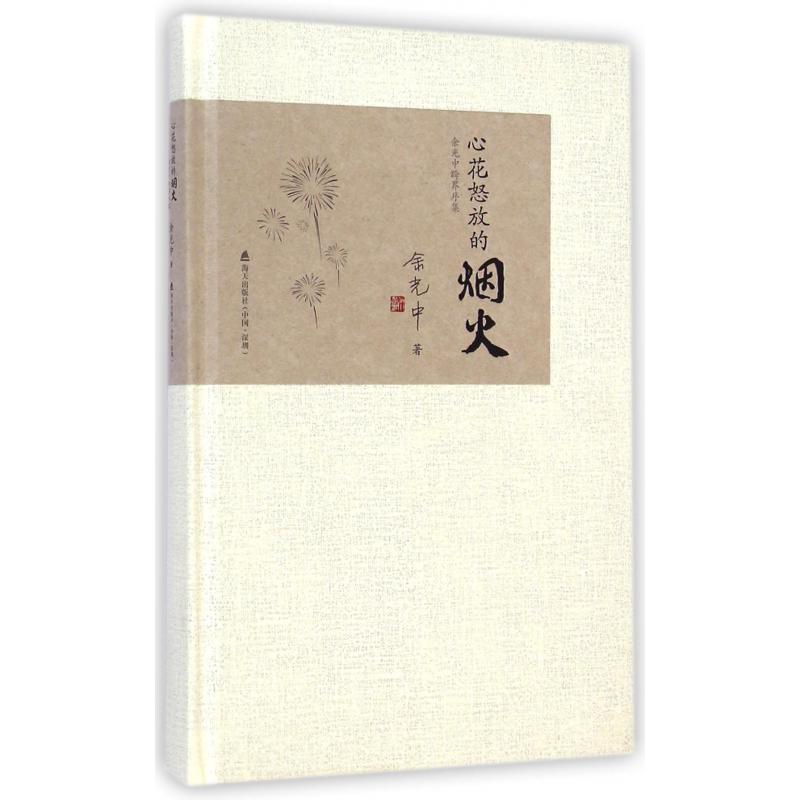
出版社: 海天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4.70
折扣购买: 心花怒放的烟火(余光中跨界序集)(精)
ISBN: 9787550711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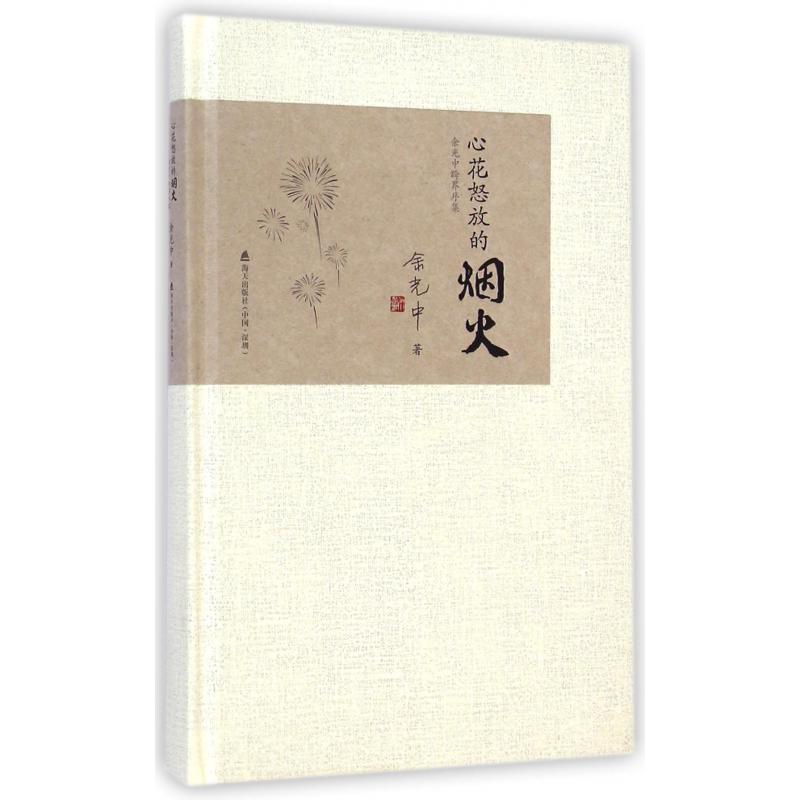
余光中,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因母亲、妻子均为常州人,亦自称江南人。曾在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读,毕业于**大学。在美国读书、教书五年,并任**师范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教授。 对诗、散文、评论、翻译均有贡献,已出版专著五十种。近年在大陆各省出书已逾二十种。余氏写诗、评诗、译诗、教诗、编诗,对诗之贡献堪称全才。诗作如《乡愁》、《当我死时》、《等你,在雨中》、《白玉苦瓜》等均传诵一时。
收入目前这一套《余光中集》里的,共为十八本 诗集、十本散文集、六本评论集。除了十三本译书之 外,我笔耕的收成,都在这里了。不过散文与评论的 界限并不严格,因为我早年出书,每将散文与评论合 在一起,形成文体错乱,直到《分水岭上》才抽刀断 水,泾渭分明。 早年我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是以诗为 正宗,文为副产,所以把**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 缪斯》。其中的**篇散文《石城之行》写于一九五 八 年。说明我的散文比诗起步要晚十年,但成熟的过程 比诗要快,吸引的读者比诗*多。至于评论,则在厦 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虽是青涩的试笔,却比写抒 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写诗也不过才晚一年。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 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未想到,这一别几乎 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二十一岁,只觉得前途渺 茫,*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 那时我如果*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 的感*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 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 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 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 ,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当年临风眷顾的那 少年,对这两个传统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 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摇撼;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阴 , 令人流连。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 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所以我 有志参加耕耘。后来兼写散文,又发现当代的散文颇 多毛病,乃写《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逐一指陈。 早在厦门大学的时期,我已在当地的《江声报》 与 《星光报》上发表了六七首诗、七篇评论、两篇译文 , *与当地的作家有过一场小小的论战。所以我的文学 生 命其实成胎于大陆;而创作,起步于南京;刊稿,则 发 轫于厦门。等到四十年后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陆刊稿 , 竟已是老作家了。一生之长亦如一*之短。早岁在大 陆 不能算朝霞,只能算熹微。现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隆 重 推出这部《余光中集》,倒真像晚霞满天了。 除了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我的创作可以分 为**、美国、香港三个时期。**时期*长,又 可分为台北时期(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与高 雄时期(一九八五年迄今)。其问的十一年是香港时 期(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至于先后五年的美 国时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一九**年至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则**包 含 在台北时期之中。 然而不论这许多作品是写于**、香港或美国, 不论其文类是诗、散文或评论,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 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二十一岁以前在那片华山夏 水笑过哭过的*子,收惊喊魂似的,永远在字里行间 叫我的名字。在梦的彼端,记忆的上游,在潜意识蠢 蠢欲动的角落,小时候的种种切切,尤其是与母亲贴 体贴心的感觉,时歇时发地总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 安。我所以写诗,是为自己的七魂六魄祛禳祷告。 2 到二〇〇〇年为止,我一共发表了八百零五首诗 , 短者数行,长者多逾百行。有不少首是组诗,例如 《三生石》便是一组三首,《六把雨伞》与《山中暑 意 七品》便各为六首或七首;《垦丁十九首》则包罗得 * 多。反过来说,《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 》虽 分成三首,也不妨当做一组来看。他如《甘地之死》 、 《甘地朝海》、《甘地纺纱》,或是《星光夜》、《 向* 葵》、《荷兰吊桥》也都是一题数咏。所以我诗作的 总 产量,合而观之,不足八百,但分而观之,当逾千篇 。 论写作的地区,大陆早期的青涩少作,收入《舟 子的悲歌》的只得三首。i次旅美,得诗五十六首。 香港时期,得诗一八六首。台北时期,得诗三四八首 ; 高雄时期,得诗二一二首。也就是说,在**写的诗 一共有五六。首;如果加上在《高楼对海》以后所写 而迄未成书之作,则在**得诗之多,当为我诗作产 量的十分之七。所以我当然是**诗人。不过诗之于 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虽然在**飘起, 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劲 , 旗怎能飘,我当然也是*广义*高义的中国诗人。 自一九八。年代开放以来,我的诗传人大陆,流 行*广的一首该是《乡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 引 述的频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竞激起如许波纹,当初怎 么会料到?他如《民歌》、《乡愁四韵》、《当我死 时》 几首,读者亦多,因此媒体甚至评论家干脆就叫我做 “乡愁诗人”。许多读者自承认识我的诗,都是从这 一 首开始。我却恐怕,或许到这一首也就为止。 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 制。我的诗,主题历经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 中一个要项。就算我一首乡愁诗也未写过,其它的主 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述、人物、咏物 、 即景、即事,每一项都有不少作品。例如亲情一项, 父母、妻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曾人诗,尤以母亲、 妻子咏歌*频。又如人物,于今则有孙中山、蔡元培 、 林语堂、奥威尔、全斗焕、戈尔巴乔夫、福特、薇特 、 赫本、杨丽萍,于古则有后羿、夸父、荆轲、昭君、 李广、史可法、林则徐、耶稣、甘地、劳伦斯。梵高 前后写了五首。诗人则写了近二十首,其中尤以李白 五首、屈原四首*多。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