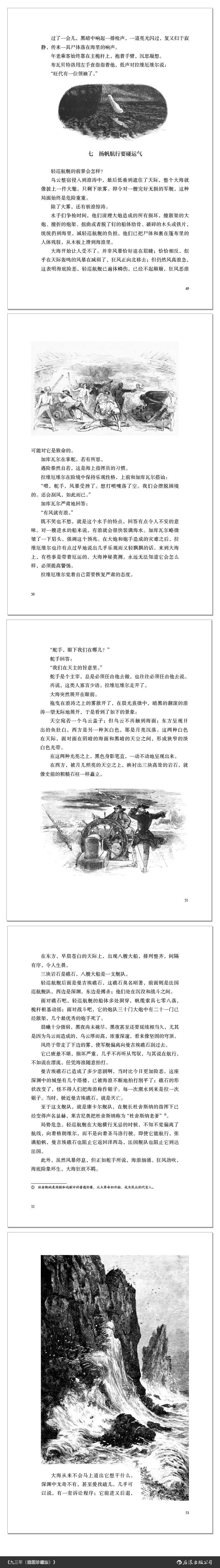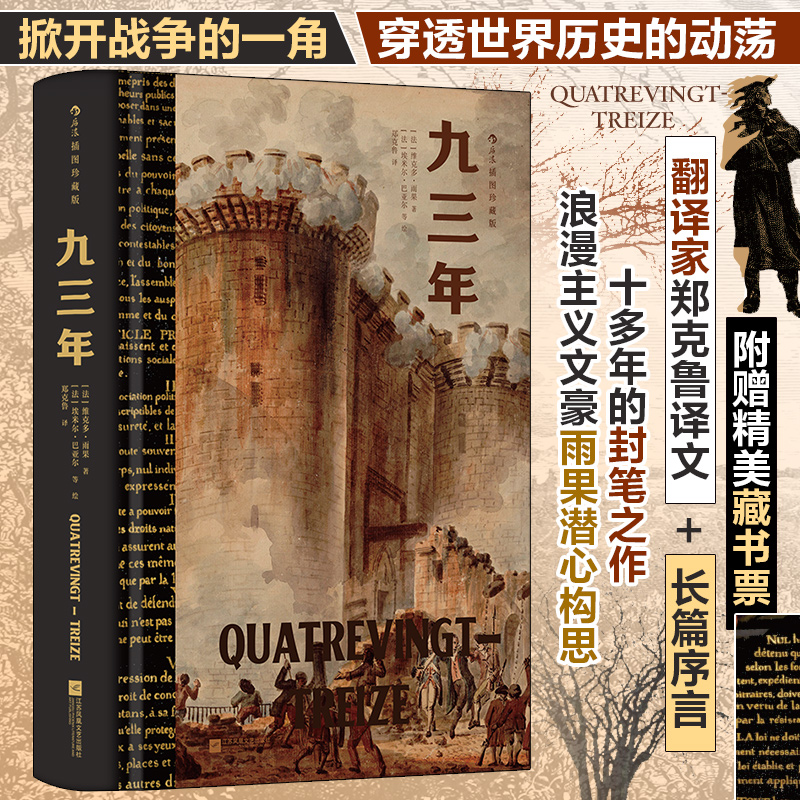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7.49
折扣购买: 九三年(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559489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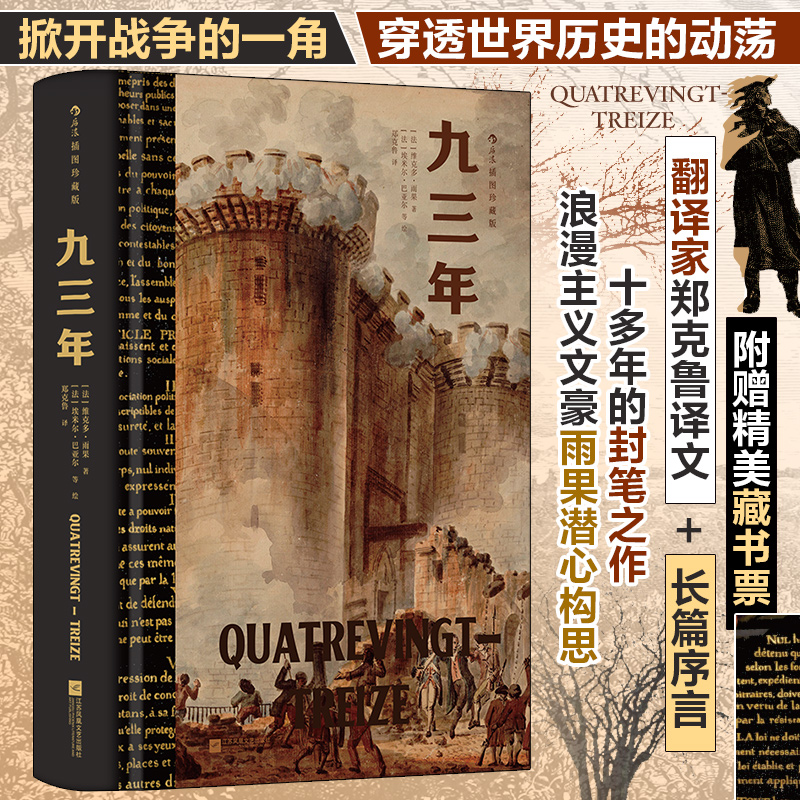
著&绘者简介 作者: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著名文学家、浪漫主义运动领袖。一生创作众多诗歌、小说、剧本、散文和文艺评论,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诗集代表作有《沉思集》《历代传说》,戏剧代表作有《克伦威尔》《爱尔那尼》。他的作品对音乐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了歌剧《弄臣》、音乐剧《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的诞生。此外,他还创作了数千幅画作,并为废除死刑和奴隶制奔走各界。他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艺术潮流,被法国尊为民族英雄。1885年雨果逝世时,法国在巴黎先贤祠为他举行了国葬,有超过200万人参加葬礼。 绘者: 埃米尔·巴亚尔(émile Bayard,1837—1891),法国画家、装饰家、设计师,曾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著名小说绘制插图。他在处理人物姿势与面部表情方面能力卓著,人物插画极具表现力。 古斯塔夫·布里翁(Gustave Brion,1824—1877),法国插画家,1847年在巴黎的沙龙首次亮相,作品受到广泛关注,被米卢斯美术馆、南特美术馆、斯特拉斯堡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译者简介 郑克鲁(1939—2020),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在近60年的翻译生涯中,一共完成1700万字的文学翻译,被誉为“以一己之力,把半个法兰西文学‘扛’到了中国”。代表译作有《悲惨世界》《九三年》《基督山伯爵》等。
第一章 索德雷树林[ 索德雷树林是舒安党(反对革命的群体)领袖聚集的地方。] 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 1793年3月初,旺代地区接连爆发反对共和党人政策的运动,集结成规模,被称为“旺代叛乱”或“旺代战争”。],由桑泰尔[ 桑泰尔(1752—1809),法国政治家,1789 年投身于大革命,1792 年任国民自卫军首脑,当时率军镇压旺代叛乱。]率领来到布列塔尼的营队之一,搜索了阿斯蒂耶那座阴森恐怖的索德雷树林。这个营队不足三百人,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战争中,伤亡惨重。那时,经过阿尔戈纳、热马普和瓦尔米战役以后,本来有六百志愿士兵的巴黎第一营,只剩下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下五十七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搏斗年代。 从巴黎派到旺代的营队,每营有九百一十二人,配备三门大炮。兵员是迅速组建的。当时,戈耶是司法部长,布肖特是陆军部长;四月二十五日,“忠告区”[ 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曾建议向旺代派遣志愿兵营队;公社委员吕班提出了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准备好派出一万两千士兵、三十门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营。这些营队虽然成立仓促,但组织严密,改变了以往士兵和下级军官人数的比例,因此今日仍然被当作楷模;当今的战斗连队就根据这种建构模式组成。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 1789—1798 年的巴黎公社是市政府,并非 1871 年的无产阶级政权。]给桑泰尔的志愿兵下了这道命令:“绝不宽恕,毫不赦免。”五月底,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两千人中,八千人殒命。 闯入索德雷树林的营队保持警惕。绝不贸然从事。同时观察前后左右;克莱贝[ 克莱贝(1753—1800),法国将军。1792 年加入革命军并迅速晋升,1793 年被派到旺代。]说过:“士兵后背也有一只眼睛。”他们搜索了很长时间。眼下大概几点钟了?什么时候了?很难说清楚。在这样乱生乱长的荆棘丛中,总是像在昏暗的暮色里,这座树林里面从来都不明亮。 索德雷树林悲剧环生。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起,就是在这座树林里内战开始狼奔豕突,凶残的瘸子“火枪”从这不祥的密林中走出来;那里犯下的杀人凶案令人头发倒竖。没有更加令人恐怖的地方了。士兵们小心翼翼地往里深入。处处鲜花盛开;人人周围是树枝颤动的墙壁,绿叶迷人的凉意从中倾泄而下;阳光这儿那儿斑斑点点落在绿色的暗影上;地上生长着菖兰、沼泽茑尾、草地水仙、预告明媚春光的小花、春天的藏红花,给厚厚的植物地毯刺绣和镶边,上面麇集各种各样的苔藓,有的像毛毛虫,甚至像星星。士兵们一步步向前,悄无声息,一面轻轻拨开灌木。鸟儿在刺刀上方啁啾。 以前,和平时期,人们在索德雷树林里“乌伊什巴”,就是在夜里猎鸟,眼下是在里面追逐人。 树林里全都是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平坦,苔藓和厚密的青草隐去了人的脚步声。没有任何小径,就是有,也迅即消失了;可以看到枸骨叶冬青、野李子树、蕨草。一排排芒柄花、高高的荆棘;十步之外就看不见人。 不时有一只苍鹭或者一只黑水鸡从树叶之间掠过,表明附近有沼泽。 士兵们向前走,盲目前行,忐忑不安,生怕遇到他们搜索的人。 他们不时遇到扎营的痕迹、烧过火的地方、踩踏过的草、十字架木棍、血迹斑斑的树枝。这些地方有人做过士兵的大锅饭,做过弥撒,包扎过伤员。但是经过的人已然消失。他们当下在哪里?说不定很远。说不定近在咫尺,藏了起来,手里握着喇叭口短铳。树林似乎空无一人。营队加倍小心。孤寂,因此令人狐疑。不见人影,就更有理由担心有人。他们是在跟一个声名狼藉的树林打交道呢。 很可能有伏击。 三十个精兵独立出来去侦察,由一个中士率领,与部队主力拉开相当大的距离,走在前面。营队的女小贩陪伴他们,她喜欢和先遣队在一起。要冒危险,但有东西可看。好奇心是女性勇敢的一种表现形式。 突然,这支小先遣队的士兵们战栗起来,就像猎人走近兽穴时常有的那样。他们好像听见了矮树丛中央有呼吸声,他们似乎刚刚看到叶丛中有晃动。士兵们互相示意。 在侦案兵警戒和搜索时,军官们不需要介入;应该做的事会自动完成。 不到一分钟,有晃动的地方就被包围了;一圈瞄准的枪团团围住了它,从四面八方同时对准了荆棘丛晦暗的中央;士兵们扣住扳机,眼睛盯住可疑的地方,只等中士下令就一阵齐射。 女小贩壮胆朝荆棘丛里张望,正当中士要喊出“开火”时,这个女人喊道:“且慢!” 她转身朝士兵们说:“别开枪,哥儿们!” 她冲进矮树林。大家跟着她。 里面确实有人。 在矮树丛最稠密处,有一小片圆形的林中空地,是烧树根的木炭窑形成的,边上有一个树枝搭成的洞穴,构成一个树叶遮盖的房间,犹如放床的凹室那样半掩半开。一个女人坐在苔藓上,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膝盖上还有两个睡熟的孩子,露出金黄头发的脑袋。 这就是埋伏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小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来。 女小贩气势汹汹地加上一句: “你在这里真是疯了!” 她又说: “你险些玩儿完了!” 女小贩对士兵们又说: “是个女人。” “没错,我们看见啦!”一个士兵说。 女小贩继续说: “跑到树林里找死!怎么想到干这种蠢事呢!” 女人惊慌失措,失魂落魄,目瞪口呆,环顾四周,仿佛在梦中看到这些步枪、这些刺刀、这些凶神恶煞的面孔。 两个孩子惊醒了,哭喊起来。 “我饿。”一个说。 “我怕。”另一个说。 那个小不点继续吃奶。 女小贩看着婴儿说: “你是对的。” 那个母亲吓得无言以对。 中士对她说: “别害怕,我们是红帽子营[ 当时的革命党人戴红帽子,穿长裤,称为“红帽子”或“长裤汉”。]。” 女人从头到脚直打哆嗦。她望着中士,那张粗犷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两只炭火般炯炯发光的眼睛。 “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营。”女小贩补充一句。 中士继续说: “你是什么人,太太?” 女人惶惶然望着他。她瘦削、年轻、脸色苍白、衣衫褴褛,戴一顶布列塔尼农妇的宽大风帽,脖子上系一条用细绳结住的毛毯。她像一只雌兽那样满不在乎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的脚没穿袜子也没穿鞋,鲜血淋漓。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小贩用大兵的,但其中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吃吃地说,几乎听不清: “米雪尔·弗莱沙尔。” 女小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宝宝多大了?” 母亲没听明白。女小贩坚持说: “我问你喂奶的那个孩子的岁数。” “啊!”母亲说,“一岁半。” “不小了,”女商贩说,“不应该再吃奶了。我们会给这孩子喝汤。” 母亲开始放下心来。惊醒的两个小孩好奇多于恐惧,他们欣赏着军帽上的翎毛。 “啊!”母亲说,“他们饿得够呛。” 她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吃,”中士大声说,“也给你吃。不过,话还没有问完,你是什么政治见解?” 女人望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话吗?” 她期期艾艾地说: “我年轻时被送进了修道院,但我结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教会我说法语。有人放火烧了我们村子。我们飞快地逃了出来,我都来不及穿鞋子。” “我问你,你是什么政治见解?” “我不知道。” 中士继续说: “因为奸细也有女的。女奸细要被枪毙的。喂,说呀。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是哪里?” 她望着他,好像不明白,中士重复说: “你的祖国是哪里?”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你的老家在哪里?” “啊!我的老家。我知道。” “那么,你的老家在哪里?” 女人回答: “在阿泽教区的西斯夸尼亚庄园。” 轮到中士惊愕了。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这不是一个国家呀。” “这是我老家。” 女人沉吟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先生。你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怎么说?”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大声说。 女人只限于回答: “我是西斯夸尼亚人。” “是西斯夸尼亚人也就罢了,”中士接着说,“你的家庭是在那里吗?” “是的。” “做什么的?” “家里人都死光了。我再没有亲人了。” 中士有点爱滔滔不绝地说话,继续追问下去。 “见鬼!人总有亲戚,或者有过亲戚。你是什么人?说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或者有过亲戚”,更像野兽的咆哮,而不是人的话语。 女小贩感到需要介入。她又抚摸吃奶孩子的脑袋,并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她是个女孩噢。” 母亲回答:“叫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个男孩。” “叫勒内-让。” “他的弟弟呢,这也是个男孩,脸蛋胖乎乎的。” “叫胖子阿兰。” “这些小不点儿多可爱啊,”女小贩说,“模样儿已经是大人了。” 但中士坚持不懈。 “说吧,太太。你有一个家吗?” “我有过。” “在哪儿?” “在阿泽。” “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 “因为家被烧了。” “谁烧的?” “我不知道。打过一场仗。” “你从哪儿来?” “就从那儿来的。” “你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 “说正题吧。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属于哪个党派?” “我不知道。” “你是蓝党还是白党[ 蓝党是共和党,他们穿蓝色军服;白党是保王党,他们穿白色军服。]?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 停顿一下。女小贩说: “我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时间生养。” 中士又开始问。 “你的父母呢?喂,太太,告诉我们,你父母的情况。我呀,我名叫拉杜,我是中士,我住在舍尔什-米迪街,我的父母曾住在那里。我可以谈谈我的父母。你给我们谈谈你的父母吧。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 “他们是弗莱沙尔夫妇。就是这些。” “是的,弗莱沙尔夫妇就是弗莱沙尔夫妇,就像拉杜夫妇就是拉杜夫妇。但总有个职业吧。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他们原先干什么?眼下干什么?你的弗莱沙尔夫妇干什么玩意儿?” “他们是农民。我的父亲残废了,由于他挨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棒,还算发善心呢。因为我的父亲捉过一只兔子,按理要判死罪;老爷发善心,说道:就打一百棍算了。我的父亲便成了残废。” “还有呢?” “我爷爷是胡格诺派[ 胡格诺派是16世纪法国的新教徒。]。本堂神父让他去做苦工。那时我很小。” “还有呢?” “我公公是私盐贩子。国王下令绞死了他。” “你的丈夫呢,他是干什么的?” “前一阵子他在打仗。” “为谁打仗?” “为国王。” “还为谁?” “当然还为领主老爷。” “还为谁?” “当然还为本堂神父先生。” “真他妈的,该死的畜生!”一个士兵喊道。 女人吓了一跳。 “你看,太太,我们都是巴黎人。”女小贩和蔼可亲地说。 女人合十双手,高声说: “啊!我主耶稣基督!” “不要迷信。”中士说。 女小贩在女人身边坐下,把大孩子拉到两膝之间,孩子任由她这样做。孩子们放下心来和受到惊吓,原因都讲不清楚。不知道他们内心有什么在警示他们。 “可怜而善良的布列塔尼女人,你有几个漂亮的宝宝,这是确实的。可以猜出他们的年龄。大的有四岁,他的弟弟三岁。啊,这个吃奶的小不点儿可真是个馋猫。啊!小妖精!你这样不是想把你娘吃掉吧!喂,太太,千万别害怕。你应该加入我们的营队。你会像我那样做事。我名叫乌扎尔德,这是一个绰号。但是我更喜欢叫乌扎尔德,而不是像我母亲一样叫比柯尔诺小姐。我是随军食品商贩,就是军队互相射击、互相残杀时,给人酒喝的女人。麻烦多得要命。咱们的脚差不多大小,我会把鞋给你。八月十日我在巴黎。[ 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冲进市政厅,巴黎和各省武装民众联合进攻王宫,逮捕路易十六,推翻了封建王朝。]我给维斯泰尔曼[ 维斯泰尔曼(1751—1794),法国将军,丹东的盟友,在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793年被任命为将军,前往旺代镇压叛乱,以严酷闻名。1794年和丹东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喝酒,事情顺利。我看到路易十六,就是人们所说的路易·卡佩上了断头台。他不愿意。嘿,你就听着。真想不到,一月十三日他让人烤栗子,和家里人一起欢天喜地。当刽子手把他强按在所谓的铡头板上时,他没有外衣,也没有鞋子;他只有一件内衣、一件凸纹短褂、一条灰呢短裤和一双灰色丝袜。我呀,我见过这个场面。押运他来的马车漆成绿色。得啦,跟我们走吧,营里都是好小伙子,你来当二号女小贩;我会指点你怎么干。噢!简单得很!你带上桶和铃铛,走到闹声震天和子弹呼啸中,冒着炮弹,在喊杀声里大声嚷嚷:‘孩子们,谁想喝一口酒?’这有什么难啊。我呢,我给所有人喝酒。确实是的。给白军的人喝,也给蓝军的人喝,虽然我是蓝军。甚至是忠诚的蓝军。但我给所有人喝酒。受伤的人口渴。人死时不分观点。临死的人应该互相握手。打仗真是蠢事!跟我们走吧。如果我被打死,你就接替我。你瞧,我就是这副模样,可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抵得上一个正直的男子汉。你怕啥子呢。” 女小贩住了口,女人讷讷地说: “我们的邻居叫玛丽-让娜,我们的女仆叫玛丽-克洛德。” 中士拉杜正在训斥那个士兵: “闭嘴。你吓坏了太太。在女人面前不该说粗话。” “这是因为,在正直的人看来,这毕竟是真正的屠杀,”士兵反驳说,“你看这些不开化的人,父亲被领主打残废了,祖父被本堂神父送去做苦工,公公被国王绞死,他妈的龟孙子还打仗,还投身叛乱,替领主、本堂神父和国王卖命,弄得个粉身碎骨!” 中士申斥道: “队伍里不许说话!” “那就保持沉默,中士,”士兵又说,“可是,像这样一个标致的女人为了一个什么教士的漂亮眼睛,去冒脑袋开花的危险,这算什么事啊。” “这个士兵,”中士说,“我们这里不是在梭枪区俱乐部。别耍嘴皮子。” 说罢,他转向那个女人。 “太太,你丈夫呢?他干什么的?眼下怎样了?” “眼下他啥也不是,因为他被杀死了。” “在哪儿?” “在树篱那儿。” “什么时候?” “三天前。” “谁打死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是谁打死你的丈夫吗?” “不知道。” “是蓝军还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三天以前吗?” “是的。” “在哪一边?” “在埃尔内那边。我的丈夫倒下了,就是这样。” “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干什么?” “我带着这些小不点儿逃走。” “你把他们带到哪儿?” “往前赶呗。” “在哪儿过夜?” “在地上。” “你吃什么?” “啥也没吃。” 中士以军人方式噘起嘴,髭须碰到了鼻子。 “啥也没吃?” “也就是荆棘丛里去年剩下的黑刺李、桑椹,还有越橘果子、蕨草的嫩芽。” “不错。等于说啥也没吃。” 大孩子好像听懂了,说道:“我饿。” 中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分配的面包,递给那个母亲。母亲将面包掰成两半,给了两个孩子。小家伙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她一点不留给自己。”中士喃喃地说。 “这是因为她不饿。”一个士兵说。 “因为她是母亲。”中士说。 孩子们停下不吃。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另一个孩子也说。 “这个见鬼的树林里没有小溪吗?”中士说。 女小贩解下挂在腰间小铃铛旁边的铜杯,旋开斜挂在身上的酒壶盖,往杯里倒了一点酒,送到两个孩子的嘴边。 第一个孩子喝了,做了个鬼脸。 第二个孩子喝了一口,吐了出来。 “这可是好东西。”女小贩说。 “是烈性烧酒吗?”中士问。 “是的,最好的。他们可是乡下人。” 她擦拭杯子。 中士又问: “太太,你就这样逃命吗?” “没法子啊。” “穿过田野,就像有人追赶你?” “我使尽力气跑,然后行走,再然后倒了下来。” “可怜的教徒!”女小贩说。 “到处在打仗,”女人结巴着说,“周围子弹横飞。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丈夫被打死了。我只明白这个。” 中士用枪托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嚷道: “打仗多么愚蠢!真他妈的!” 女人继续说: “昨夜我们在一棵古树里睡觉。” “四个人吗?” “四个人。” “睡觉?” “睡觉。” “那么,”中士说,“是站着睡的?” 他转身对着士兵们: “弟兄们,这里有一种老得枯死的空心大树,一个人可以像种子一样钻进去。这些粗野的人管这叫埃穆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总不会像在巴黎那样睡觉。” “睡在树洞里!”女小贩说,“而且还有三个孩子!” “要是孩子们喊叫起来,”中士又说,“过路人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一棵树在喊‘爸爸,妈妈!’,那应该很古怪。” “幸亏眼下是夏天。”女人感叹说。 她看着地面,逆来顺受的模样,眼里流露出对灾难的惶惑。 默默无言的士兵们在这苦难的景象前围成一圈。 一个寡妇,三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逃难,无依无靠,孤立无援,战争在周围四野里轰鸣。饥饿,口渴,除了草叶没有别的食物,只有以天为屋顶。 中士走近女人,盯住吃奶的孩子。小家伙松开奶头,慢慢地转过头来,用漂亮的碧眼瞪着俯向她的毛发竖起的、野兽般可怕的脸,微笑起来。 中士直起身,只见一大颗泪珠滚落在面颊上,宛如一颗珍珠停在髭须尖端。 他提高了声音。 “弟兄们,由此可见,我们营要当父亲。同意吗? 我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这句话和共和国的目标之一相应:“它通过祖国收养的孤儿”被宣称为“神圣的孩子”。]。”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高呼。 “一言为定。”中士说。 他将两只手伸到母亲和孩子们的上方,说道: “这就是红帽子营的孩子们。” 女小贩高兴得跳起来,她喊道: “一顶帽子下有三个脑袋。”[ 表示三个人共有一个观点,这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梦想。] 接着她号啕大哭,发狂地拥抱可怜的寡妇,对她说: “小宝宝已经有淘气的神态了!”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又一次高呼。 中士对母亲说: “女公民,一起走吧。” ◎ 潜心构思十多年,浪漫主义文豪雨果的封笔之作。 ?“爱就是行动。” 1885年5月22日,雨果在法国逝世,并留下最后的笔记:“爱就是行动。”雨果的一生处在民主革命与封建制度解体的激烈交锋之中,他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并通过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绘画,以及政治活动,带着艺术家的热情与秉持的“人道”之心,矢志不渝、毫不动摇地投身于生活的巨浪之中,以热忱观察、探索、记录着社会的深渊。 雨果的小说创作一直承载着某种社会使命感:《巴黎圣母院》讨论了哥特式建筑,并推动了巴黎圣母院的复兴;《悲惨世界》关注妓女、劳工等各类底层人的生活,直接将各类保障议题推到了议会里;《笑面人》则着重批判性地描写了贵族阶层,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可以说,雨果的创作就是他“行动”的方式,他的作品跨越了国别、语言和时间的界限,以共通的人性,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心中唤起相通的情感,形成了人道的共鸣与交融。 ?“《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 雨果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现实社会,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挥洒着人文的理想,而这一切的前提——法国大革命,一直是回荡在雨果心中的重要议题。早年创作中他回避着政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渐衰,他愈发感到自己必须去写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将多年以来经历的革命与战争,以及其中之人的矛盾与抉择铭刻下来。1862年末至1863年初,雨果的心中就明确了以旺代战争为主题进行创作的想法。 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选取了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年作为故事的背景,创作《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他给友人写信道:“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然,《九三年》在雨果心中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它是雨果最后一部小说,给雨果丰饶又厚重的小说创作历程画上了伟岸的句点。 ◎ 掀开战争的一角,穿透世界历史的动荡。 ?“九三年,这可怕的一刻震古烁今,比这个世纪的其他时刻都更加伟大。” 1793年是关乎法国大革命生死存亡的一年。当时,巴黎革命的影响扩散,激起了各地保王派的反叛,雅各宾派取代吉伦特派掌权,以断头台进行恐怖统治,又进一步激起保王派的残酷。革命者与反对革命者,贵族与平民,教士与学者……思想的交锋外化为暴力对抗,所有人都被卷入新与旧轮转对峙的战火之中。 从时间上看,雨果选取了“九三年”这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作为故事的背景,并直接以此为名,用“九三年”这一角凝聚起法国大革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的核心冲突与矛盾。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从各方面压迫我们,我们管它叫‘必然’。” “八年的恐怖,十四个省遭到蹂躏,田地荒芜,庄稼毁于一旦,村庄焚烧净尽,城市化成废墟,房屋劫掠一空,妇幼惨遭杀戮,茅屋付之一炬,利剑直插心脏,文明惊悸万分……” 故事的每一个人都在被革命和战争“压迫”,凭着信仰、意志、理性和无法解释的冲动生存着。雨果从战争的群像之中,选取了三个冲突激烈的角色,来表达这种复杂的必然。 年轻的将军、子爵郭文有“预言家的严峻目光,孩子的笑容”,某种意义上,他是雨果本人的化身,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打仗时机敏灵活,但内心纯善,待人温柔。他作战的对象是他的叔祖、他唯一的亲人朗特纳克侯爵,攻打的地方是自己长大家族堡垒,但这些并没有让他太过困扰,因为他相信革命将会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了拯救三个无辜的孩子,朗特纳克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同时舍弃了自由、生命和自己坚定的事业。这件事给让郭文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他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人道在敌人身上同样存在,而他将要且必须要处死自己的亲人、这位刚刚以善行震撼了所有人的老人。 朗特纳克是一名贵族,从骨血到灵魂都是,他坚守着自己的修养与道德,并秉持着众人的期待,成为一名铁血无情的领袖——为了对抗革命者,这种残酷被认为是必须的。他下令烧死整个村子的革命军,其中的妇女、无辜的村民都没有放过。然而,“他对自己感到厌恶。母亲的叫喊在他心中唤醒了人类古老的怜悯心,这是一种普世的积淀,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里,甚至在最冷酷无情的心灵里。听到这喊声,他又返回。他从踅入的黑暗中又回到光明。”为了救三个孩子,他放弃了逃走和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