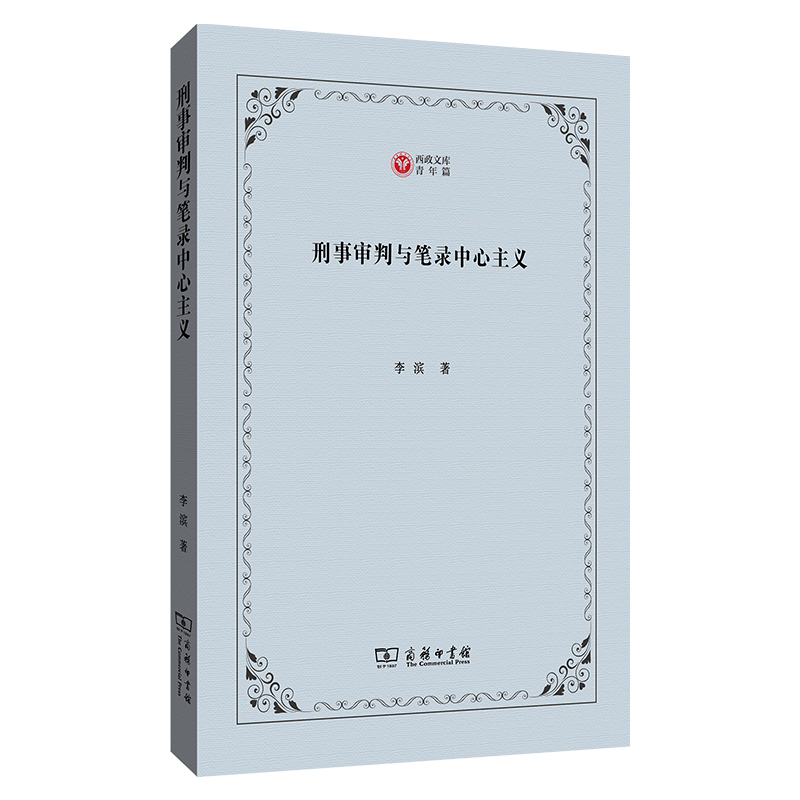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64.30
折扣购买: 刑事审判与笔录中心主义/西政文库
ISBN: 9787100215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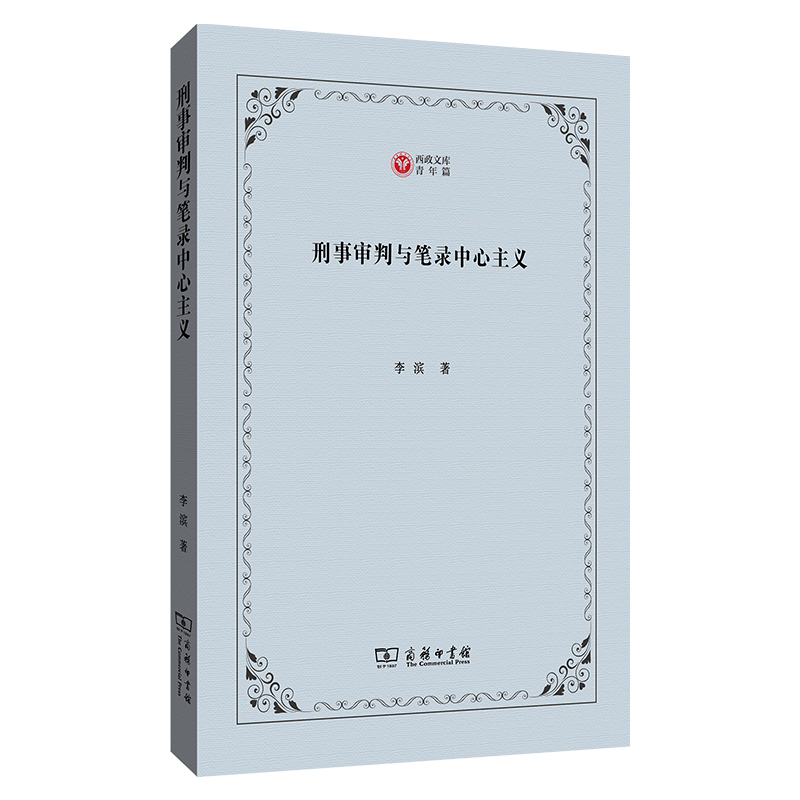
李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美国休斯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2013),主要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证据法学。曾任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庭法官,熟悉司法实务。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扎实的经验基础。
? 写作本书的动机 凡是熟悉刑事司法运作的人,都会了解我们的刑事诉讼离不开刑事卷宗。卷宗的存在非常普遍,专业人士天天翻看、整理,埋首于其间,以至于几乎很少有人去思考,如果没有卷宗,我们的刑事诉讼还可以进行吗?当笔者刚刚走上刑事法官的审判岗位时,看到一摞摞高高隆起的卷宗,几乎困惑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的刑事诉讼是围绕案件事实和被告人进行呢,还是围绕卷宗进行?前辈法官语重心长的话语经常萦绕在耳边:不管丢了什么,卷宗可万万不能丢!于是,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也不断地思索,我们如此重视的卷宗,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当法庭上的被告人面对案卷笔录的指控发出大声的反驳,直斥其虚假、伪造之时,我们还能像往常一样,以这样的笔录来定案吗?……本书的写作即起始于这样的思考。 ? 笔录材料对庭审的深远影响 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案卷笔录对审判程序、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造成深远影响。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刑事案卷使得审判法官在开庭以前可以充分研究案卷材料和信息,从中初步勾勒出案件的面貌和框架,引导其审理工作。其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笔录材料的运用极为普遍。其三,在庭审结束以后,如果诸多的难题与疑问在庭审中并没有得到释疑,那么这些问题只有留诸法官于庭审之后再度慢慢“咀嚼”笔录材料进而化解。 ? 什么是笔录中心主义? 案卷笔录对刑事司法程序和结果的影响一直以来都为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瑞华教授,他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指出“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在这一审理方式下,公诉方通过宣读案卷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调查过程,法庭审判成为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程序,不仅各项控方证据的可采性是不受审查的,而且其证明力也被作出了优先选择”。 ? 本书基本结构 本书由绪论、结语和主体的五章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本书研究的目的和动机,结语部分对本书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将来的研究。 本书主体由五章构成,第一章首先对刑事笔录资料的一般情况进行了解读,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一般性的基础。第二章对境外司法制度下笔录资料的规制方法进行全面和深入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刑事庭审中的笔录中心主义现象进行全方位描述和深入分析。第四章对形成笔录中心主义这一现象背后的经验与逻辑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揭示笔录中心主义在我国刑事程序中长期且显著存在的多重原因。第五章探讨我国运用庭前笔录资料的合理方法与限度。 ? 笔录资料的种类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的笔录资料:1.言词证据之笔录。2.警察、检察官或者法官所采取的调查行为和结果之笔录。3.鉴定人所出具之书面鉴定意见。4.行政机关所收集之笔录。 ?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对待笔录材料的主要方法 笔录在英美法的证据理论中是作为书面的庭外陈述,即书面传闻来对待的。尽管关乎传闻证据的概念及其外延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但广义的理解一般将传闻证据界定为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形式。传闻证据规则基本上构成了英美法系国家处理笔录资料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 直接言词原则和对质权要求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待笔录材料的主要方法 大陆法系国家处理笔录资料不以可采性规则为方法,而主要是以直接言词原则和公正审判权下的对质权要求来规制,同时也体现在裁判之正当化论证上。通过对德国、法国规制庭前笔录立法之分析和实践之考察,可见两国虽然在具体的规制路径上有差异,但在效果上都实现了对庭前笔录的严格规制。 ? 现代刑事审判对笔录材料使用的限制 在现代刑事程序中,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抑或是“混合式”模式下的刑事诉讼,无不对书面笔录作为证据使用予以严格限制。从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其处理书面笔录资料的基本方法是传闻证据规则,这与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诸多制度背景和特点是相契合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法国和德国刑事程序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直接言词原则,这也是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特点相一致的。“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日本、意大利的刑事程序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当事人主义的改造,并借鉴了传闻法则与之相适应。 ? 出庭作证难是我国刑事审判的一大难点 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一直以来都存在一大难题,即证人出庭作证困难。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只是在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一般性地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对证人依法可以不出庭的例外情形规定也极为粗疏。而在实务中证人、鉴定人等则普遍不出庭作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一般原则反倒成了例外,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虽然确立了在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情形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原则,但是实务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也正是因为证人不出庭,特别是关键性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司法现状突出,法庭通过证人询问发现事实真相的设想在事实上难以实现,证据调查活动也就明显表现为对庭前笔录资料的调查,因此,法庭调查活动的笔录化特征并不是仅在个案中呈现,而是有其普遍性。 ? 刑事审判向以庭审为中心转移 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后,理论上将此概括表述为庭审中心主义。根据这一概括,庭审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而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关键则是“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尽管司法体制与观念的转变是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从刑事司法改革的现状来看,这一转变也正在进行之中。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完善立法规定并缓解司法的现实困难,或者说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和具体途径实现对庭前笔录资料的合理规制。 文摘2: 笔录资料是什么? 在刑事诉讼中,笔录并不令人陌生,是我们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实实在在看到、听到并且用到的各种文字材料或者记录材料,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不是“口头的”,而是“书面的”。比如一份由证人口述、侦查人员记录的材料,就是一份笔录资料,因为作出陈述的主体是证人,在法律上也称为证人证言笔录(《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再比如,侦查人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同时也把勘验的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经由这种书面化的记载,勘验这一侦查的行为和结果就固定了下来,而不是即时逝去,那么这一记载下来的“生成物”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勘验笔录(《刑事诉讼法》第133条)。当然还有一种记载的形式即侦查人员大脑中储存的记忆,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好的证据方法,因为基于侦查人员的亲历性,其出庭作证最具有说服力,而且还可以当庭接受质疑并向质疑者释惑,但是人的记忆总有一个消退的过程,故而单纯依靠自然人的记忆对过往事件进行固定和储存也是不现实的。 “笔录”作为一个法律用语,并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独有的。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德语Protokoll即意指笔录,相应地,Protokollverlesung意指对笔录的朗读,Richterliches Protokoll则指的是法官笔录,而如果对《德国刑事诉讼法》德文版进行检索,Protokoll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78次,由此可见笔录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是常见的。在法国《刑事诉讼法》中,法语procès-verbal也是指笔录,而且由于法律要求对刑事程序中的各项活动都予以准确记载,故而各种类型的笔录在法国刑事诉讼中也极为常见,比如audition de témoin意指证人听取的笔录,interrogatoire par la police指警察讯问的笔录,transport sur les lieux指现场勘验笔录,等等。事实上,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传统上深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和日本,审前程序中的笔录都是极为常见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传统上都是以官方主导诉讼活动的进程,尤其是在侦查程序,官方在调查的同时也将其所收集的证据资料固定下来,并汇入卷宗(dossier),以备将来在审判过程中使用。正如比较法学者Langbein教授指出的,在大陆法系纠问式或者非对抗式刑事诉讼中,官方主导程序的进程并以真实发现为目的在诉讼活动的每一个阶段进行详细记录,最终形成全面和内容完整的卷宗,既包括指控有罪的证据,同时也包括可能无罪的证据。 全书较细致地总结了国内外刑事审判中对待笔录资料及证人作证的规定,提出了我国刑法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 概述了笔录在刑事诉讼中的一般情况,包括它的形成机制、移送方式和基本性质等。 ? 介绍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运用笔录资料的情况,为我国的刑事笔录研究提供了学术背景。 ? 论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笔录资料的基本情况,包括立法规制、现实运用和本质问题三个方面。 ? 分析了笔录中心主义的形成原因。 ? 勾画了笔录中心主义改革的草图,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就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的实现提出了可行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