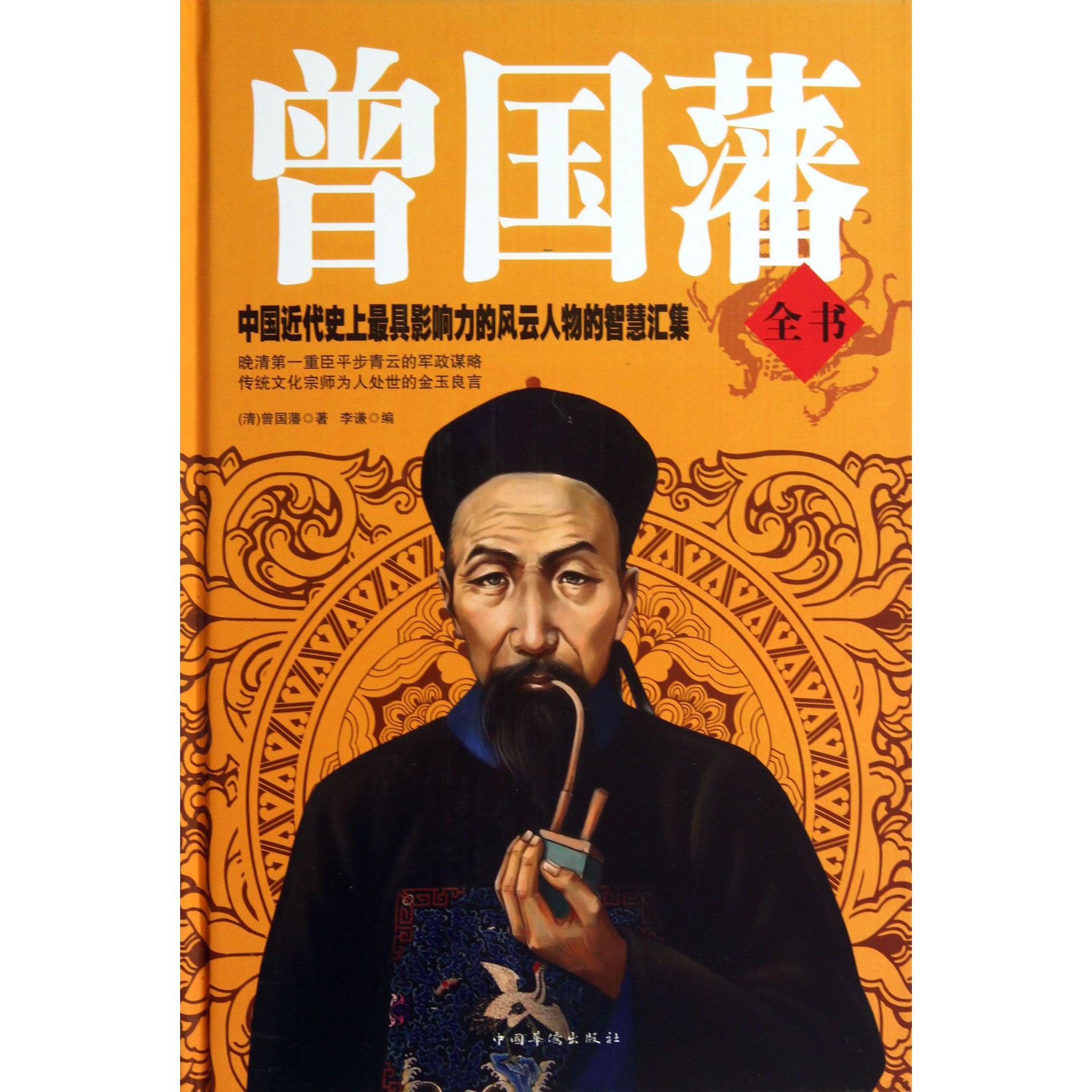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华侨
原售价: 29.80
折扣价: 22.30
折扣购买: 曾国藩全书(精)
ISBN: 9787511337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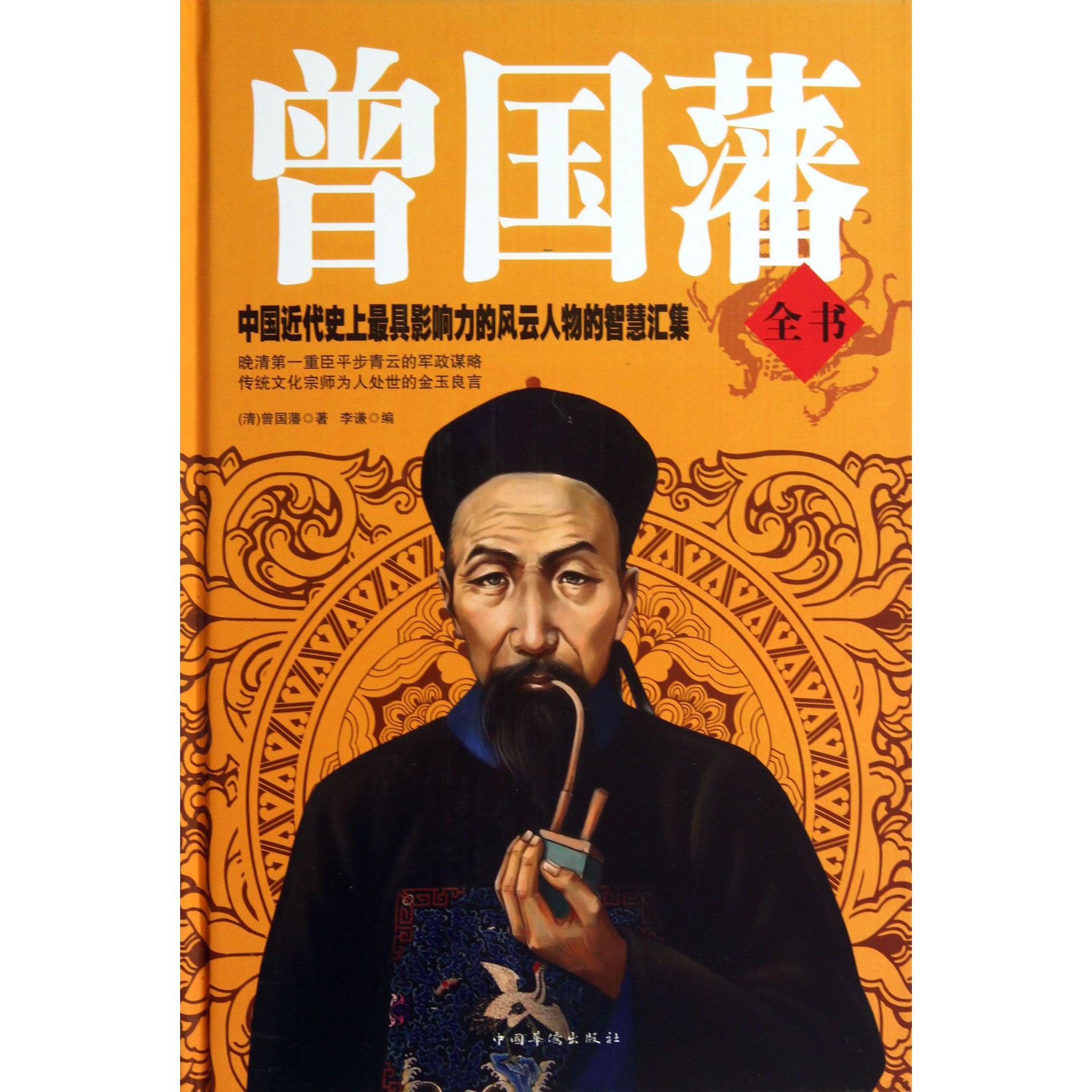
在中国,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始终推崇诚信。“ 诚”被认为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人的美好内在,相比于一个人外在华丽的 衣饰,内心的“诚”是一件水不过时的衣饰。与人交 往,以“诚”为基础说话办事,是对他人的尊重,一 个人的时候以“诚”为原则,反观自我言行,是对自 己的诚实和负责。对自己诚实,还要不断累积自己诚 实的念头,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守诚之人。曾国藩 是一个主张“诚”的人,但他遵循的“诚’,和一般 的“诚”相比略有不同,带有几分为臣的忠诚、血性 的义气,以及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咸丰初年,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 样子。臣子们于是直陈时弊,各抒己见。一时纷纷纭 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 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 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 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他口中的“书生之血诚”与 “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 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 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 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不要钱,不怕死”,是曾国藩对国家、朝廷的 赤诚之心。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的 奏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 一力经理”,绝不含糊。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 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 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 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 作医治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 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 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 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又说:“大 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 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 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 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的精神 力量,也是他实现“复礼”、“礼治”的重要保证和 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 ,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在政治上如此,在军 事方面,曾国藩也努力实践“诚”。 金陵之战时,曾国荃呕心沥血,不过是为了占有 攻破天京的头功,对于曾国荃的这点心思胡林翼知道 ,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 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手中 。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 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 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 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 信:“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 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 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 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 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 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 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人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 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攻克金陵、苏州。李鸿章也 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 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 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 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 ,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信中,曾国藩对弟弟的批评之意不掩而发,其千 言万语背后不过一个主旨: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 言不由衷都是不合乎为臣原则的行为。曾国藩虽然理 直气壮地指责弟弟,但他本人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 “诚”为原则。在他看来,偶尔的不诚并不代表全部 ,也不能否定一个人的处事原则,就像对敌人、对恶 人,就没有诚的必要。 生活中也有很多善意的谎言,是没有任何恶意, 也不会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不“诚”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毕竟这样的善意谎言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 们还是应该做到诚实,真诚待人,真诚做事。 曾国藩的一生对人诚恳,做事诚实,他的生活少 些遮掩,胸怀中多些坦荡。在现代,“诚”是情商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诚还 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怎样的人或事, 尽量做到诚实,会让我们的人生减少许多遗憾,多很 多色彩。诚为人立之本,没有诚,一个人也就不能称 之为人了。坚守“诚”这一字,是对别人、对自己最 大的尊敬。 在只有自己的时候,人会暴露出最真实的本性, 显露出最真实的自己。这种情境下,我们可以不用去 考虑任何人的感受,不用为了说一句话就思前想后, 心思千回百转,所以人们可以在独自一人时放开一切 束缚,无拘无束地做自己。这样独立而没有束缚的空 间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渴望。 有这样的空间,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固然好,但是 物极必反,在好的同时弊端也在悄然出现,如果不注 意不克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众人眼光的注 视下,偶尔地为自己松绑可以减轻压力,但是因为没 有公众眼光的约束而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有可能会 演变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这样反而会让人远离安然 。 一个擅长与自己独处的人,反而在一个人的时候 严格要求自己。这种带着镣铐舞蹈的人。之所以要给 自己一个框架规范,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因放松而放 纵。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自制力和自知力,以求做到 “在独处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 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他把“慎独”列为四条处世经验之首,足见他对“ 慎独”的重视。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慎独,管好自己, 那么在人多的时候,对自己会有更大的把控力,从而 对人际往来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曾国藩真正开始慎独的修养历程是在道光二十二 年十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这一天的经历: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 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所谓“知几” “研几”,都是对自我的省察。《易经》中说:“几 者,动之微也,”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 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如此才能在“独”时“慎”。 曾国藩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每天都学着倭艮 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 心理、行为。他每日静坐半时,以求提高自己的心性 修养。静坐的过程中,两耳屏蔽嘈杂的声音,两眼默 闭不看沧桑变幻,身体和心灵在沉寂和思维中安静, 从而获得心境的升华和清明的认识。他的静坐已不再 仅仅是养性的方式,而是一种对人生进行沉淀和积累 的行为。 心静对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心浮 气躁,没法静下来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客观地看待事 情,也就不可能觉察出自身的错误;但是只要稍稍人 静,稍作停留,仔细反思,自然会恍然有所悟,认识 到自己错在何处。沉静中获得自知,而人一旦有了自 知之明,有了这一觉悟,就能慢慢加深自己心静的功 夫。当这番功夫到一定的火候“遏欲”“循理”就不 会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有了这样一门 慢慢加深的静功,就算不静坐,也能时时警惕自己的 想法,把每一个不像话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P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