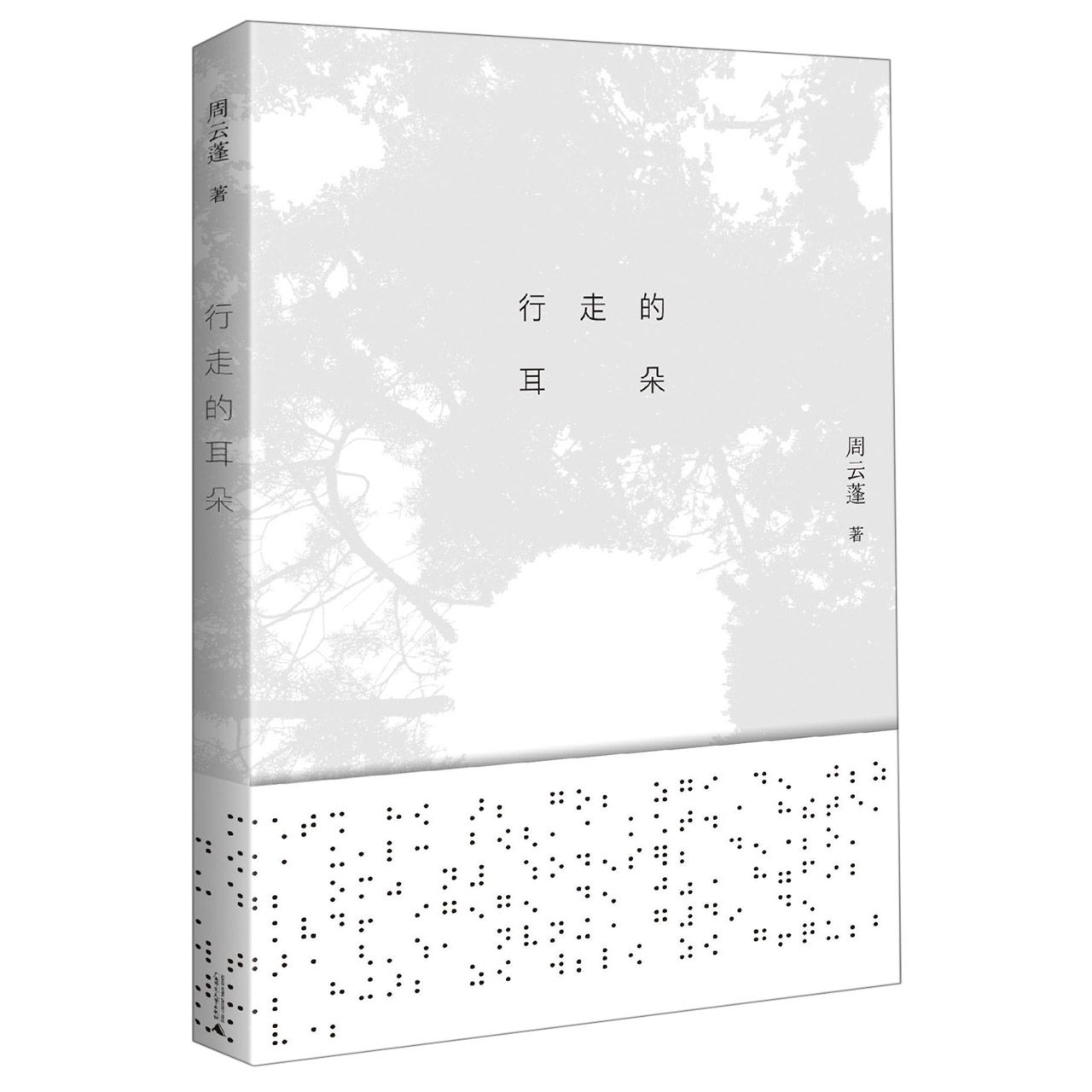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50
折扣购买: 行走的耳朵
ISBN: 9787559812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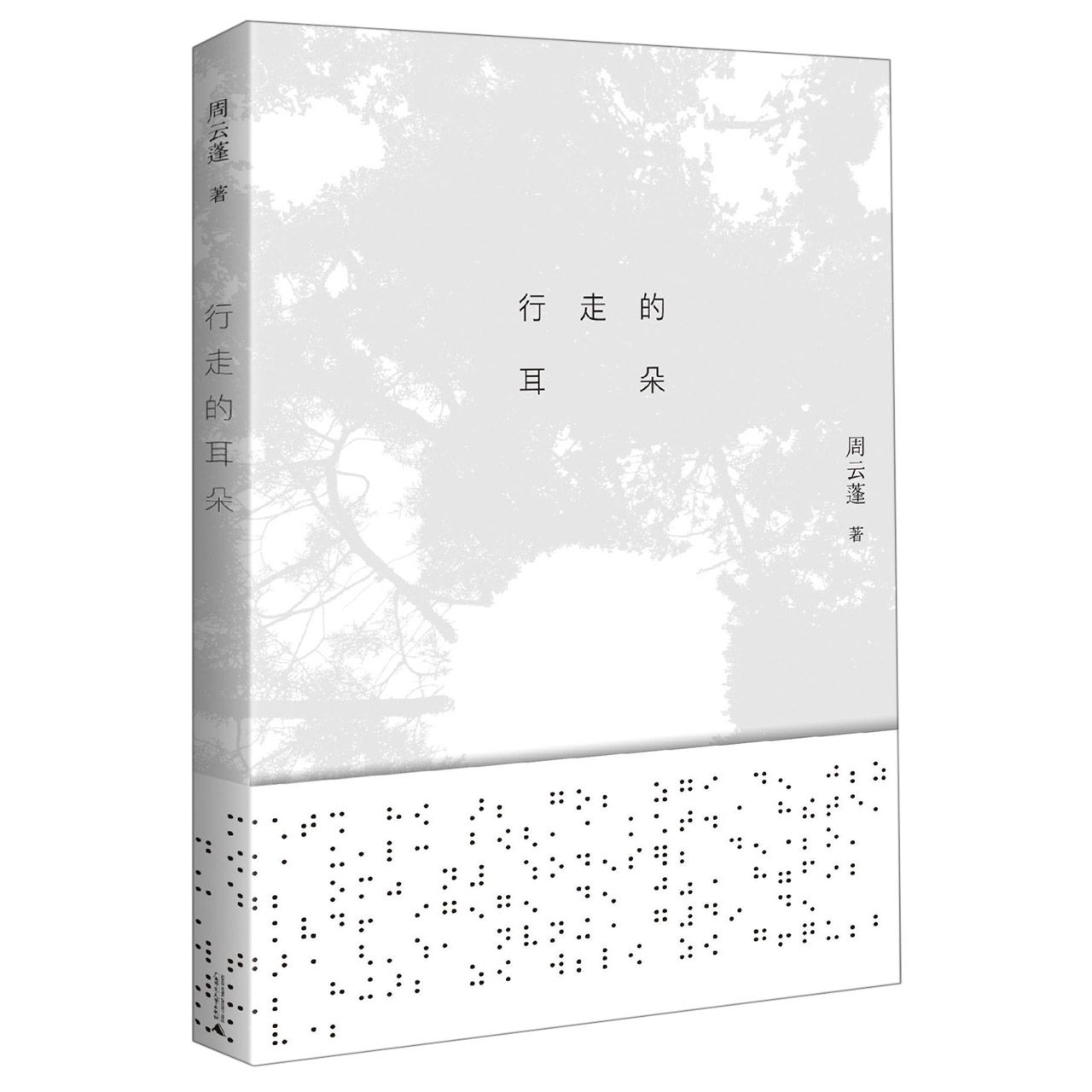
周云蓬,诗人、作家、歌手,被称为“中国*具人文气质的民谣音乐代表”。发行有音乐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清炒苦瓜》《牛羊下山》《四月旧州》等,出版有诗文集《春天责备》、杂文集《绿皮火车》等。
世界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行走的耳朵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 尤其重要起来,没了大儿子,二儿子就担负起长子的责任 了,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 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 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 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 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 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 。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 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 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 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 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 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人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 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 ,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 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 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了。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古老的 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 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的同学 ,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呜 ”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某首歌刚被唱完 ,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所以,有很多莫扎特一 样的盲童,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没能成为音 乐家。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 ,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 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 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 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 ,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 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 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 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 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好地享 *、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 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贵重的家用电器。那 时听音乐真是人心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 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 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 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 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请你可怜了 !可怜之人又不是*物,有义务总是可怜见儿的吗?或许 “蓝色清真寺,不用偏要进去,我只把这名字细细地咀嚼,满口的橄榄味,满脑子的天空高远,各种蓝层叠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