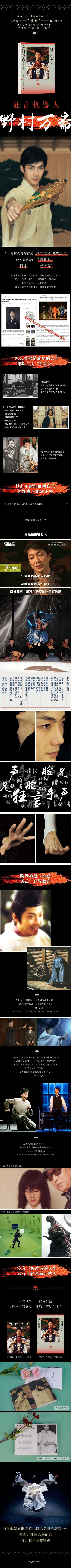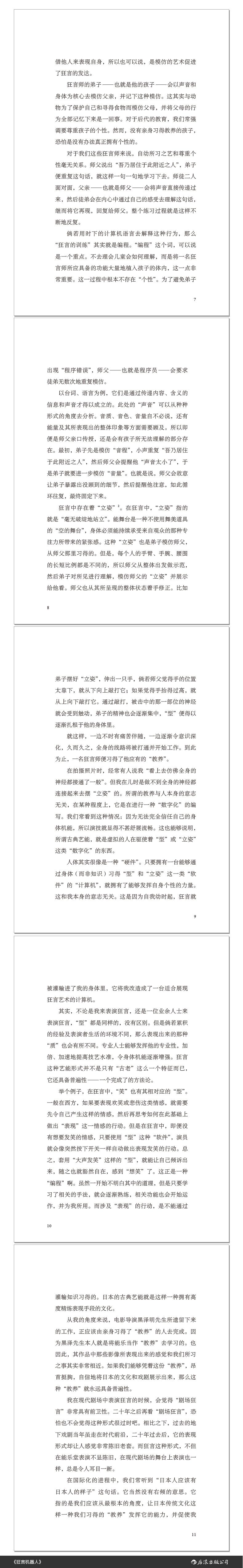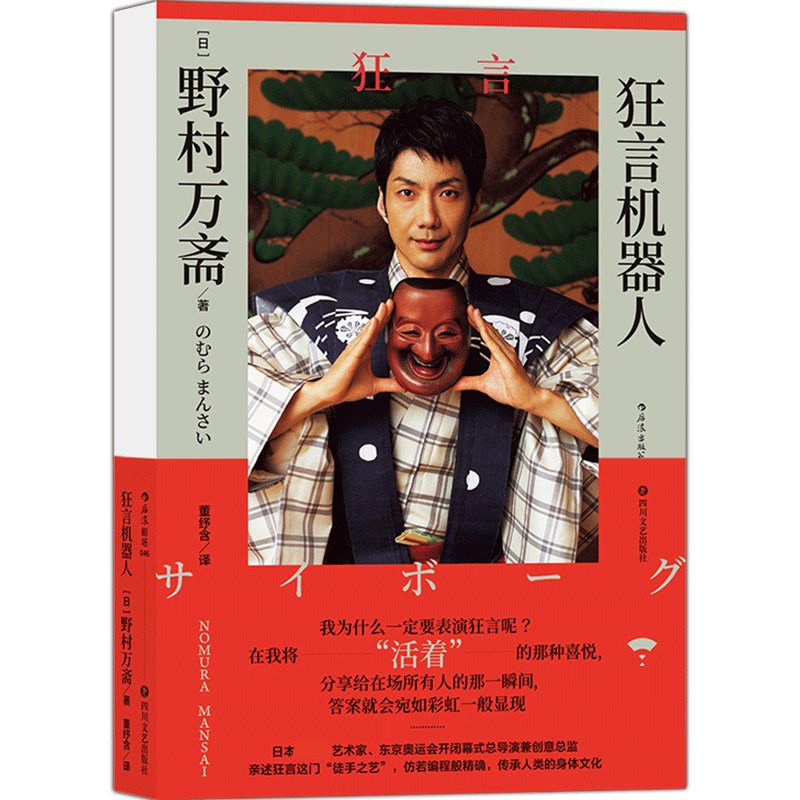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文艺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40.30
折扣购买: 狂言机器人
ISBN: 9787541158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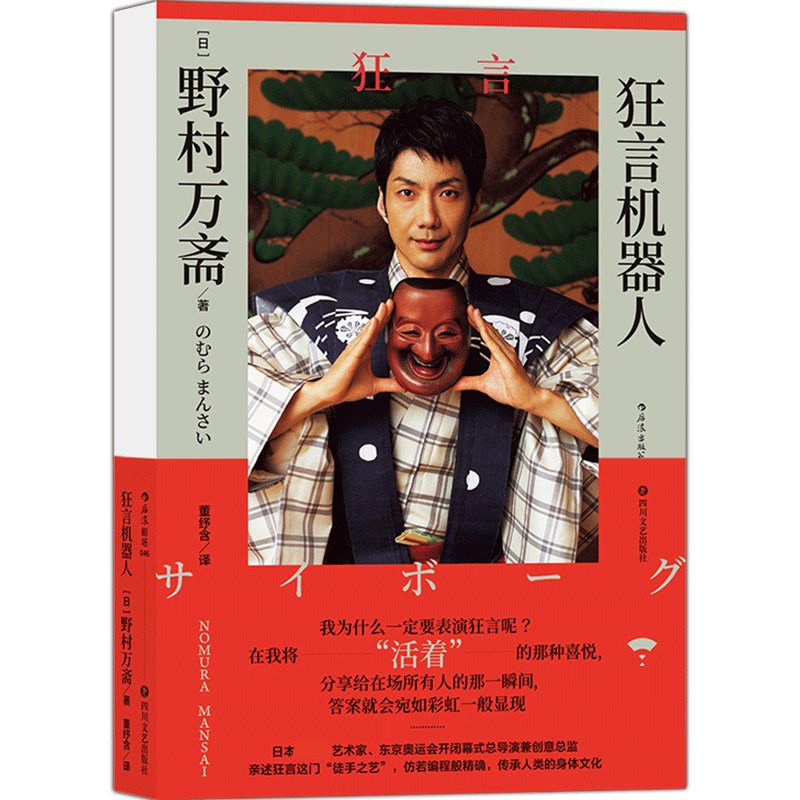
著者简介 野村万斋,狂言师,日本国宝级艺术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指定者。1966年出生于东京,师从其祖父六世野村万藏和父亲野村万作。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邦乐科,主修能乐。1994年依日本文化厅艺术家在外研修制度赴英国留学。1999年获日本文化厅艺术节戏剧部门新人奖。2005年获纪伊国屋戏剧奖。主办剧团“狂言是也座”,2002年起出任世田谷公共剧场艺术总监。担任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兼创意总监。 自三岁初登舞台以来,在国内外演出了数十部经典狂言剧目,并致力于狂言的现代化,运用古典艺术手法跨界执导了舞台剧《敦:山月记?名人传》《国盗人》等。在为能?狂言的普及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参演了许多舞台剧、电影、电视作品,如:主演蜷川幸雄的《俄狄浦斯王》《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三谷幸喜的《贝吉?帕顿》中饰演夏目漱石,在《上海月亮》中饰演鲁迅;出演黑泽明的《乱》,主演《阴阳师》《傀儡之城》,在宫崎骏的《起风了》中担任配音,在《新哥斯拉》中担任哥斯拉的动作捕捉。此外,还长期出演日本NHK电视台的《用日语来游戏吧》节目。其他著作有《吾乃万斋》《万斋解体新书》等。 译者简介 董纾含,日本东北大学比较文化论方向硕士,中央戏剧学院东方戏剧方向博士。时常笔译,零散口译。爱猫嗜闲散人员。
1 狂言与“身体” 狂言与“脸” 有人称狂言是“徒手之艺”。 因为,狂言是在能舞台这样一种空的舞台上,仅凭声音和身体进行表演。能舞台上不存在大型的舞台装置、灯光和音响。演员也不化装,除神、鬼、动物、丑女、老人以外,不着面具,以素颜进行表演。 能?狂言的源头据说来自中国唐代的一种名为“散乐”的艺能形式。这种包含滑稽模仿、杂技曲艺、奇术魔法等在内的街头艺能传至日本,同寺院的祭祀典礼和祭神仪式发生联系,于是“散乐”的读音(sangaku)在讹传中逐渐成了“猿乐”(sarugaku)。 所谓表演,从根本上说就是模仿某一种人格。不过,虽说是对人格进行模仿,却并不能“克隆”这种人格,而是提取这一人格的部分特征,对其进行夸张处理。近些年在新年期间,电视上会固定播放《模仿歌会》这个节目,参与表演的模仿者们基本上是将“声带模仿”和“形态模仿”这二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夸张。 用胶带将鼻子朝上固定、让眼睛变成一道细缝、眼梢向上吊、在额头贴一块大大的黑痣,这些手段只能说是一些比较低端的技能,但是它们具备颠覆性,常让观众捧腹大笑,这其实是对夸张的一种滑稽化处理。 我想,散乐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与电视上播放的模仿节目之间决定性的不同在于二者所模仿的对象。当今时代,电视这种媒体已经十分发达,只要是位名人,人人都会认识他。所以只要夸张滑稽地模仿这位名人,便会赢得笑声。然而,在能?狂言趋于成熟的室町时代是没有电视的。当时的所谓名人——也就是“将军”大人——的脸,可不像现在的国家元首这样众所周知。 狂言的演出,是从一位登场人物自我介绍“吾乃居住于此附近之人”开始的。也就是说,登场人物并非某个特定的“名人”,他或是一名普通人,或是能够代表观众的一个人,抑或是代表观众内在的某种人格的人。这个人一开场便宣布要模仿自己所“代表”的种种了。 能取材自文学作品,主要的模仿对象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名人,如:光源氏、六条御息所、平家诸公卿、小野小町、在原业平等等。如此一来,一卵双生的能与狂言,两者的性格便逐渐演变成一方为表、一方为里。我认为,狂言更接近其本源的形态,它继承了散乐的滑稽模仿,成为运用语言和动作进行表演的一种喜剧形式;能则在形式性上逐渐强化,以文言体内容的“歌伴舞”形式进行假面剧形式的悲剧表演。 狂言在表现普通的女性时不戴面具,以素颜示人。只不过在表演的时候会将一种名为“美男发”的漂白布片缠在头上,将男性的下颌和面颊的骨骼遮挡起来就变成了女性。狂言里也从没出现过什么有名的美人,只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女性”而已,所以做到这个程度也就足够了。但要是年老的能演员不戴面具就表演小野小町的话,就有点…… 狂言中有一出剧目名为《业平饼》,其中比较罕见地出现了在原业平这样的人物。在能中,自然需要戴着面具来演绎业平这样一位绝世美男;在狂言中,则是以狂言师本来的面目进行表演。而且在狂言的这出《业平饼》中,越是同业平大人的气质相去甚远者,在表演的时候越是能突显狂言的滑稽讽刺,显得尤为生动。因为狂言既是“徒手之艺”,也是“本真耿直的艺术”。 狂言与“颈、肩” 我脖子很长,并且还是个溜肩膀。这种体态非常像“鹤”,还会让人联想到勃艮第红酒的酒瓶子。 所谓“坐高”,本是指人在坐着的状态下腰部以上的高度,但一般都被直接理解成躯干的长度。 相对于我的身高来说,我的坐高是在平均范围以内的,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不同,有些不太平衡。我躯干的长度和脖子以上的长度很不和谐,估计快到三比二的程度了。 常有人说,脖子比较长又溜肩膀的人很适合穿和服。我就常被人这样讲。但这种说法其实是女性穿和服时的一种常识,它并不适用于男性着能?狂言装束时的情况。 在狂言中,主人小名身着长裃,作为其仆人的太郎冠者则身穿肩衣。这些服装皆是素袄、挂素袄的简略形态,或许就是这种将袖长缩短、口袋省去,以服装的功能性优先的做法,导致其从形态上更突显了肩部的棱角。 在能的装束中,狩衣、法被、水衣这一类装束的衣袖、口袋都十分宽大,而在饰演一些动作较大、性格刚烈的角色时,为了配合动作,表演者会将袖子折挽到肩膀上,使肩部的形态更为突出。虽是在模仿身着甲胄——也就是护具——时的姿态,但倘若是溜肩膀的话,反而会显得过于夸张。不过,头上再戴顶巨大的红白或黑色长假发,倒是又找回了平衡…… 在电视上播放的时代剧中,大家熟知的远山阿金以奉行之姿态出现时,身上穿的是裃,翘起的肩部不但具备形式美,同时还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但是当他展示自己的樱吹雪文身时,却显露出了本来的圆润肩头。这种做法不只是在人物造型上加以变化,同时也富有现实气息,能够十分明确地让观众感受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这些从事能?狂言艺术的人,因为忌讳生动的也就是日常性的表演,同时又厌恶将原本的形体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此,我们用装束武装身体。能的表演甚至到了要用假面遮挡脸部的地步。也就是说,绝不可以将头部和手以外的身体暴露出来,这正可谓是一种“无机的现实主义”了。 另一方面,能在有史以来这六百年间始终只有男性能够表演,这并非出于对女性的蔑视,而是因为能的表演需要仰仗男性肉体强大的形态。虽然这种强大无法直接地展现出来,但是观众能够感受到被包裹在厚重装束之下的肉体是训练过的和洗练的。在这一点上,能也和穿着紧身衣裤展现西洋雕刻般肉体的芭蕾等艺术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当我在饰演女性角色时,我溜肩膀的特征就可以不加修饰地被直接利用起来。而因为男性角色多会使肩部摆出上挑的姿态,这时我的长脖子又派上了用场,因为脖子不会被高高翘起的服饰挡住。 不过,这样的脖子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印象呢?我想,它其实就是从腰部笔直延伸向上的一条线。演员的形体虽被装束修饰出了凹凸错落感,但仿佛被高高吊起的那种紧张感反而在和演员自身的重力抗衡,这也成为演员所诠释角色的“重量”与“存在”。而这种“平衡感”方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与理想。然而,在真实的日常世界中,人的头部无法稳定,脖颈动不动就向前倾斜,这样“不平衡”的事情是很多见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表演狂言呢? 在我将“活着”的那种喜悦 分享给在场所有人的那一瞬间, 答案就会宛如彩虹一般显现。」 野村万斋,当代首屈一指的人气狂言师,活跃于多方舞台的跨界艺术家,被誉为日本未来的“人间国宝”。怎么看都是成功的人生,他却自比“狂言机器人”。生为狂言,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身体里便被编入了“程序”。背负着宿命,只有在这条路上不停地走下去,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不断地证明自己,才能真正地活下去。 在这本随笔集中,野村万斋分享了他的成长历程、创作焦虑、不满足的自省,以及自我挑战与突破。正如狂言,有正经,才得以欢笑。当他将宿命化为活着的原动力,生命之花已然绽放。 * * * ◎ 通过“解剖”狂言师的身体,从头到脚、由内及外地生动展示了狂言这门“徒手之艺”。 ◎ 编年体讲述了个人狂言生涯的发端与修行,从武司时期的点滴到成为人气狂言师万斋。 ◎ 回顾了留学英国期间尽情呼吸自由的现代空气,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切磋的宝贵经历。 ◎ 阶段性记录了在“狂言是也座”的创作体会与演出心得,以及在海外文化交流中的有趣见闻。 ◎ 分享了在古典艺能、现代戏剧和影视表演中的尝试与探索,以及对“传统的当下”和狂言未来的思考。 ◎ 字里行间流露真性情,绝美写真令人惊叹,原来他是这样的野村万斋。 * * * #万斋OS# 「自我幼时起,狂言就被灌输进了我的身体里,它将我改造成了一台适合展现狂言艺术的计算机。」 「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头发留到了肩部,长度足够在脑后束起来。但回国后第二天我就把头发剪了。要是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梳成丁髻,或许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吧?我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些强词夺理的解释,一边惋惜地望着自己的头发像流水素面一样簌簌掉落,仿佛自己逝去的青春。」 「“我为什么一定要表演狂言呢?”当年我因为害怕师父万作,所以不敢这样问他。轮到我的儿子,他却很简单直白地问出了这个问题。我苦苦思索答案而不得,于是老实地回答道:“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