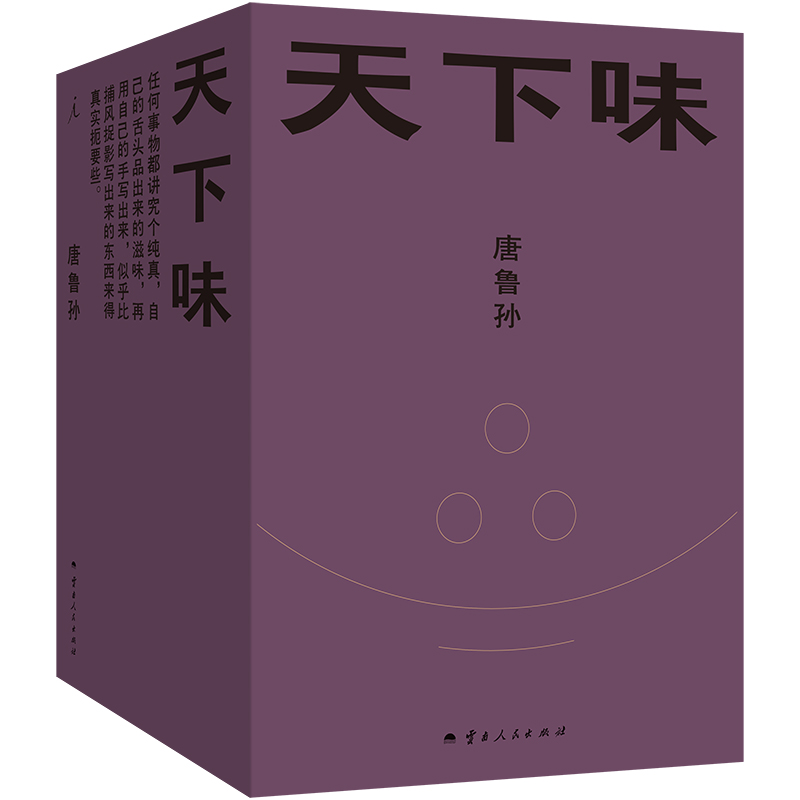
出版社: 云南人民
原售价: 240.00
折扣价: 148.80
折扣购买: 唐鲁孙全集:天下味(20周年典藏增补版)
ISBN: 9787222225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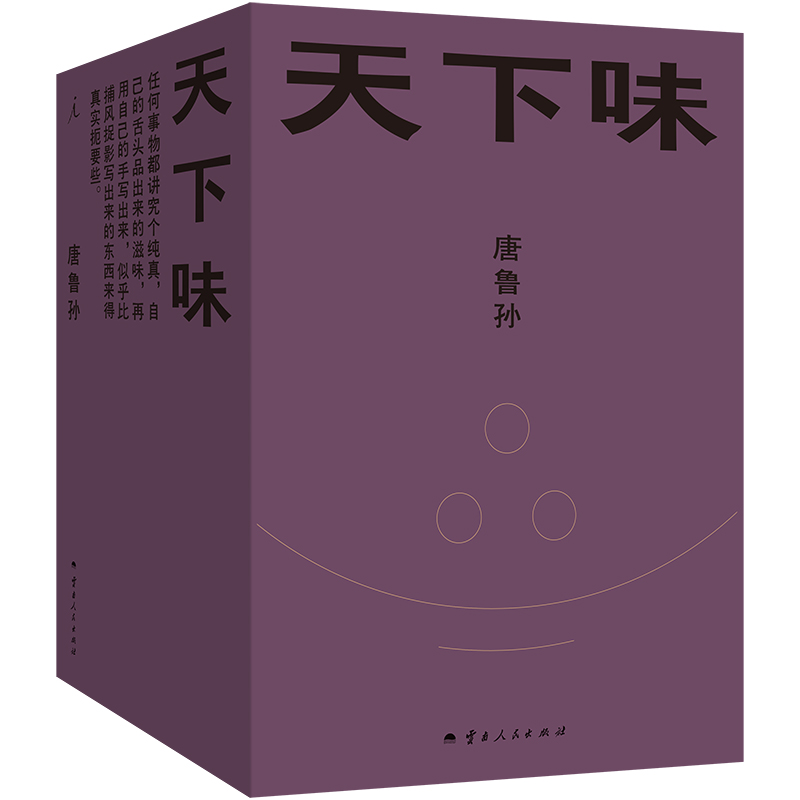
唐鲁孙,一九〇八年九月十日生于北平,满族镶红旗后裔,原姓他塔拉氏,本名葆森,字鲁孙。其曾祖长善,字乐初,官至广东将军。曾叔祖父长叙,官至刑部侍郎,二女并选入宫侍光绪,为珍妃、瑾妃。 唐鲁孙七八岁时进宫向瑾太妃叩春节,被封为一品官职。因父亲早逝,十六七岁便顶门立户,交际应酬。于北京崇德中学、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任职于财税机构,后以弱冠之年只身外出谋职,先后客居武汉、上海、泰州、扬州等地。一九四六年随张柳丞先生赴台,任烟酒公卖局秘书,后历任松山、嘉义、屏东等烟叶厂厂长。一九八五年在台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唐鲁孙年轻时游宦全国,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平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作为民俗学家,其写作“和《清明上河图》有相同的价值”;加之出身贵胄,常出入宫廷,习于品味家厨奇珍,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闲暇时对各类美食揣摩钻研,改良创新,又有美食家之名,被誉为“中华谈吃第一人”;一九七三年退休后,以民俗、美食为基调进行创作,凡百万字,内容丰富,自成一格,允为一代散文大家,“可以当作《洛阳伽蓝记》看,比照《东京梦华录》来读”。
?★ “馋人说馋”的饮馔传奇,老北京人的莼鲈之思: “中华谈吃第一人”带你领略 “舌尖上的民国史”—— “他用他一生的际遇,写出了人生中种种的回不去,却成就了一席民国盛宴,一部有滋味的民国史。”(王家卫) 七十年代初,文坛突然出了一位新进的老作家。一九七二年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的一篇充满“京味儿”的《吃在北平》,不仅引起老北京的莼鲈之思,海内外亦一时传诵。 唐鲁孙对吃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又那么执著,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字,就是“馋”。唐鲁孙说:“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别人也称我馋人。所以把以往吃过的旨酒名馔,写点出来,也就足够自娱娱人的了。”梁实秋先生读了唐鲁孙最初结集的《中国吃》,写文章说:“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唐鲁孙的响应是:“在下忝为中国人,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够得上馋中之馋了。”馋是他写作的动力。他写的一系列谈吃的文章,可谓之“馋人说馋”。 不过,唐鲁孙的馋,不是普通的馋,其来有自。唐鲁孙是世泽名门之后,世宦家族饮食服制皆有定规,随便不得。他家以蛋炒饭与青椒炒牛肉丝试家厨,合则录用,且各有所司。小至家常吃的打卤面也不能马虎,要卤不澥汤,才算及格;吃面必须面一挑起就往嘴里送,筷子不翻动,一翻卤就澥了。这是唐鲁孙自小培植出馋嘴的环境。(逯耀东) ★ 最当代的美食观念+老派人的自我修养: 真正的美食是没有阶级的——“人不分南北,菜一样东西。” 1.虽为王孙贵胄,但唐鲁孙并不推崇穷奢极欲胡吃海喝,而是珍惜粮食,取其本味,丰俭由人: “我们讲求饮馔,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最经济实惠原则之下,变粗粝为珍肴,不但是色、香、味三者俱备,而且有充分均衡的营养。至于一饭千金、一席数万金的华筵盛馔,穷奢极欲地挥霍浪费,那就不足为训了。” 2.虽生在北平,但唐鲁孙自认是“东西南北之人”,兼容并蓄,而非独沽一味,既无国族、地域之藩篱,亦无食材贵贱之分别,适口充肠就是最好的美食: “舍下虽然是北平的老住户,可是先世宦游江浙两广,远及云贵川,踵武至圣先师,成了东西南北之人。就是饮食方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变成杂合菜的口味啦。”在他的笔下,既有精益求精的谭家菜,也有三分钱一大碗的羊杂汤;既有老北京的八大楼,也有瀛寰饭店的法式红酒焖蜗牛、泰国街头的小吃、土耳其的香烟、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3.虽也搜奇尝鲜,但唐鲁孙并不认同为美味而虐杀动物,馋人有所吃有所不吃: “听人说,杀鸽子要把铜钱孔套在鸽子嘴上,把鸽子闷死,然后宰杀,鸽子才鲜嫩好吃。我认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让鸽子这样死法,未免太残忍些,所以任何做法的鸽子,登盘荐餐,虽有朋友坚劝,我仍旧不动筷子。”后得知鸽子并未遭遇虐杀,且野生肉鸽大吃田禾,才开始初尝鸽肉美味。 4.食物的味道就是人生的味道。饮馔不外乎人情,最“落胃”的还是关心: “据说产妇吃了缸烙,身体可以早点儿复元,不掉头发。饽饽铺恐怕贫寒人家花费太大,于是所做缸烙分毛边、不毛边两种式样。其实两种火候分毫不差,无非是给手头紧的人打个小算盘而已。现在商场上整天喊商业道德,比较一下当年饽饽铺的做法,能不惭愧吗?” ★ 在一个价值与话语纷飞的暧昧时代,重建一个久违的、确凿的物质世界: 拒绝二手经验,不做过分阐释——“任何事物都讲究个纯真,自己的舌头品出来的滋味,再用自己的手写出来,似乎比捕风捉影写出来的东西来得真实扼要些。” 吃喝玩乐是最为具体、真实的经验,不是修辞,不是叙事,不是泛滥的话语,调动的也是人最切身的感受。 从《红楼梦》对家具、首饰、衣料的大量着墨,沈从文转而研究文物与传统服饰,张爱玲对色彩、材质的迷恋,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种中文世界共同的失落感——不只是家道中落,世道变化,也是一整个物质世界的失落。他们用笔墨饱蘸记忆,勾勒出一个久违的、确凿的物质世界,而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也仿佛身临其境,经验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世界。“唐先生的文字是白描式的,绝不妄言己所不知的领域,所涉皆为亲身历见,有多少记多少,很少浮夸与过多的峻峭深刻之笔。其文字中既没有子虚乌有的满汉全席,也没有时下两岸某些文化名人的谈禅说道。娓娓道来,朴实无华,反而更加引人入胜。”(赵珩)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感官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