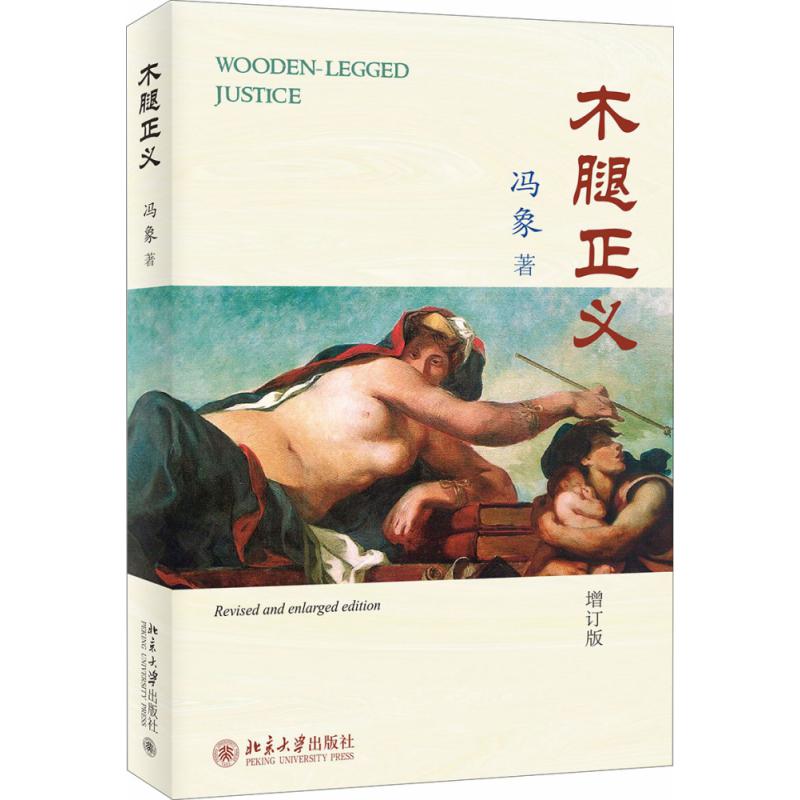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3.40
折扣购买: 木腿正义(增订版)
ISBN: 9787301114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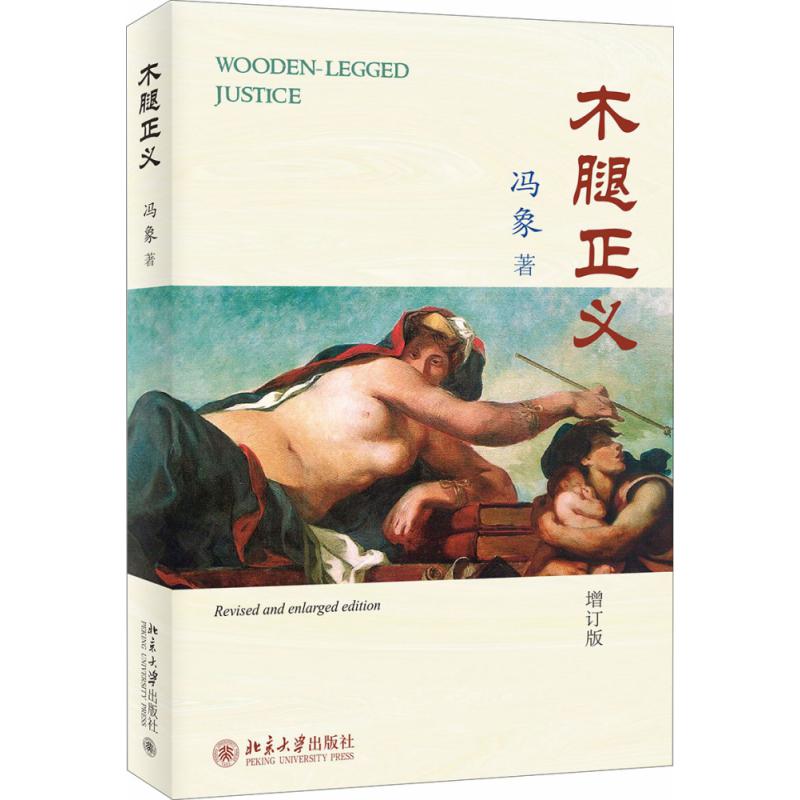
冯象,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曾任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哈佛大学兼职教授。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
我国法学向来有“幼稚”之名,业内人士并不讳言。但衡量一个国家一 门学科的学术水准,除了看从业人员整体的学养和品质,主要还是看它的代 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比如美国,我们说它的学术如何如何,无非指它的顶尖 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若是把全美国四百二十五种学生主编的法学杂志上刊 登的论文一总儿拿来细算(美国法学院的传统,学术刊物一律由学生办),情 况便大不一样了。美国学者自嘲说,一年到头雨后春笋般发表的论文当中的 多数,读者恐怕不超过五个,即作者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委(格兰顿,第2 05页)。中国的法学“研究”,滥起来当然没有让美国佬占先的道理。毕竟 ,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可是同时,近年来中国法学 出类拔萃的少数代表作,其成绩之骄人,又是举世瞩目的。不读这些作品, 就不知道中国有一群脚踏实地、孜孜砣砣、上下求索的法学家,不知道他们 的关怀之广、抱负之大、于学术事业的信心之坚。 今年六月到清华讲学,承苏力兄赐教,得一册他的新著《法治及其本土 资源》。七月初回波士顿,坐在飞机上把这本将近三百五十页的论文集一口 气读完。读到精彩之处,忍不住翻回扉页去看那题记。那是我敬佩的前辈同 行袁可嘉先生的名句:“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窄而去/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 根本”。我以为《资源》确实大大“提升了中国法学的学术声誉”(赵晓力 序),应当摆在标志着中国法学(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开始成熟的代表作之列 。 法律社会学我是外行。全面探讨《资源》提出并论证的一系列观点,应 该由方家来起头。苏力为我们开掘的“学术富矿”的大致面貌和他的“既出 世又入世”的学术品格,他的高足赵晓力君已经在序中作了生动的评述。此 处我只挑一个通俗的题目,接着苏力的精湛分析发挥两点,聊表我“恍然于 根本的根本”的体会。我想从《秋菊打官司》这个苏力喜爱的个案(故事)说 起。 《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特别引起法学家研究兴趣的,是秋菊讨的那个 “说法”和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故事很简单:秋菊的男 人和村 长吵架,骂了一句“断子绝孙”(村 长只生了四个女儿,没儿子)。村 长大怒,踢了秋菊男人“要命的地方”。秋菊要村认错,村不肯,她就 一级一级告状,讨她的“说法”。后来秋菊难产,村 长领了人冒着大风雪, 走几十里山路把她抬到县医院,救了秋菊母子的命。没想到,正当秋菊感恩 不尽,等着村 长来家吃给儿子做满月的酒席的时候,上级查出了秋菊男人被 村 长打的伤处(但不在下身),派了一部警车把村 长带走了——十五天行政拘 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1)项)——害得秋菊好不难堪:她 讨的是“说法”,政府却把人给抓了。 苏力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国家制定、实施法律为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 ,为什么反倒让秋菊输了理·以这样的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的”法治,能否 在中国农村运行·其代价又是什么(第25页)· 首先,秋菊对权利的“思想认识”似乎和法律规定的不同。例如秋菊说 ,村 长可以踢她男人(因为男人骂了“断子绝孙”),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 ”踢。她没法理解,为什么法律先是把她的官司一把推开,调解了事;后来 又让她请律师,告那位曾经帮助过她的公安局长(不服公安局维持司法助理 员调解处理的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而一旦发现男人受了轻伤,便不 管两家事实上已经和解,把村 长送进班房。她的“说法”明明是再简单不过 的“理”,一碰上法律,事情就复杂化了。苏力说得好,“[法律]制度的逻 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第26页)。 于是,苏力把讨论引向对普适主义法制的批判。他指出,所谓“现代的 ”(西方式)法律只是正义的一种,没有资格自称“大写的真理”,代表着语 境的、普适的权利界定和权利保护。如果我们对此不保持清醒的怀疑态度, 那“大写的真理”就“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 臣服于它”(第27页)。 在苏力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 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 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因此,至少从秋菊的困 惑看,“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 ”(第28页)。就是说,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过分强调了与国际“接轨”,而在 运作中压制了民间法及其他传统规范(道德、习俗、宗教和行业伦理等)的成 长,忽略了这些非正式法律和规范曾长期有效地调整着的那些社会关系。结 果正如《秋菊》描绘的,正式法律的干预破坏了社区中人们传统上形成的默 契和预期(包括秋菊与村 长之间“那种尽管有摩擦、争执甚至打斗但仍能相 互帮助的关系”)。“一个‘伊甸园’失去了,能否回来,则难以预料”(第 30页)。 这里涉及一个我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即正式法律作为国家意识 形态的机器(aparatus),在实际运作中跟民间法等传统规范究竟是什么关系 ·回到《秋菊》,也就是秋菊讨“说法”究竟与什么相冲突·这冲突于我们法 治的现代化又具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资源》的基本观点已经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但作者更关注 的是批判西方法权的普适主义和本质主义,论证法治利用本土资源的正当性 和必要性。限于篇幅,他没有展开对秋菊讨“说法”本身的讨论,并就此考 察“大写的真理”的实际构造和运作。 《木腿正义(修订版)》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法律与文学方面的一些文章,作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阐释了法律与文学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在书中作者也谈到了法学方法论的问题。本书作者是当今国内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其作品在国内图书市场很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