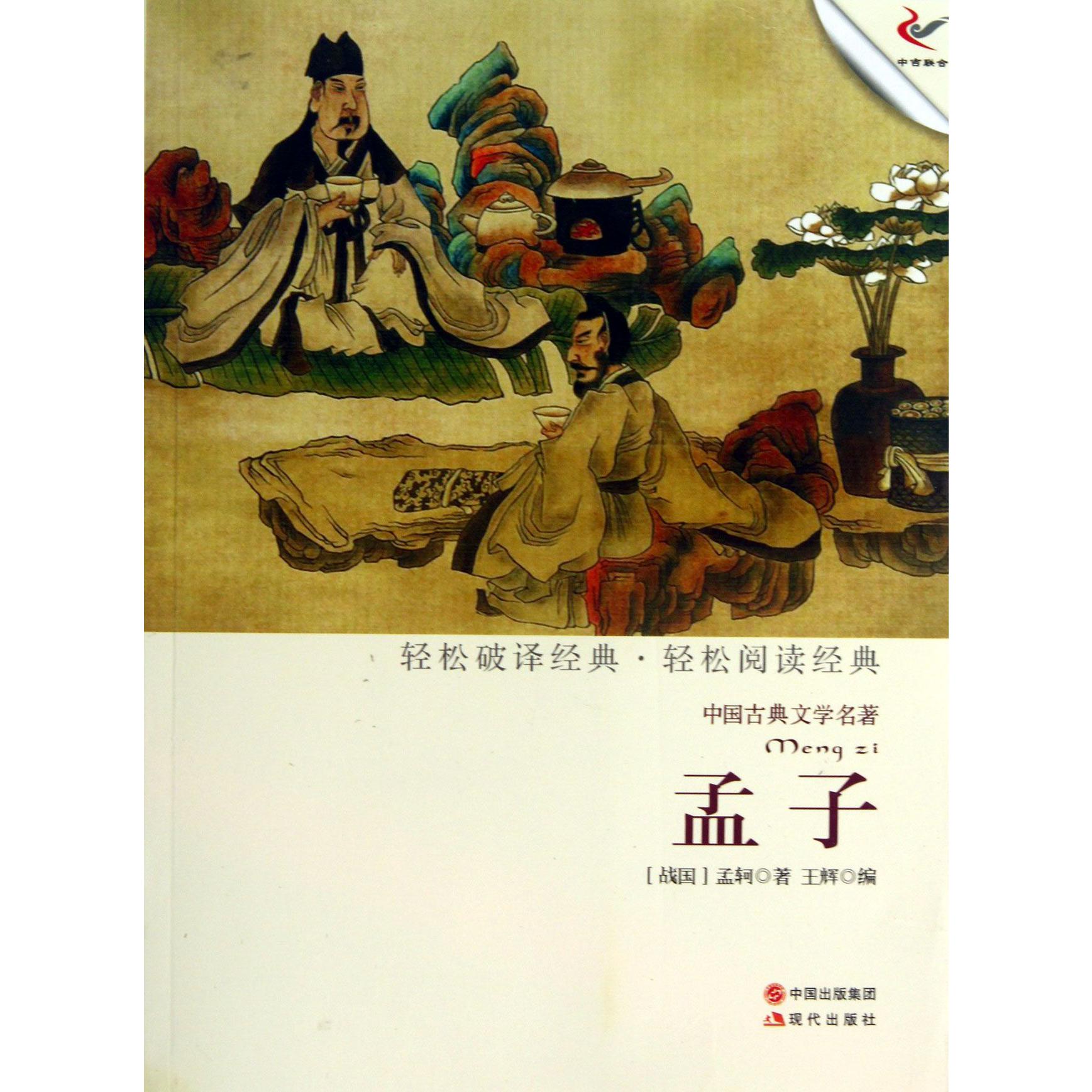
出版社: 现代
原售价: 25.80
折扣价: 14.19
折扣购买: 孟子/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9787514308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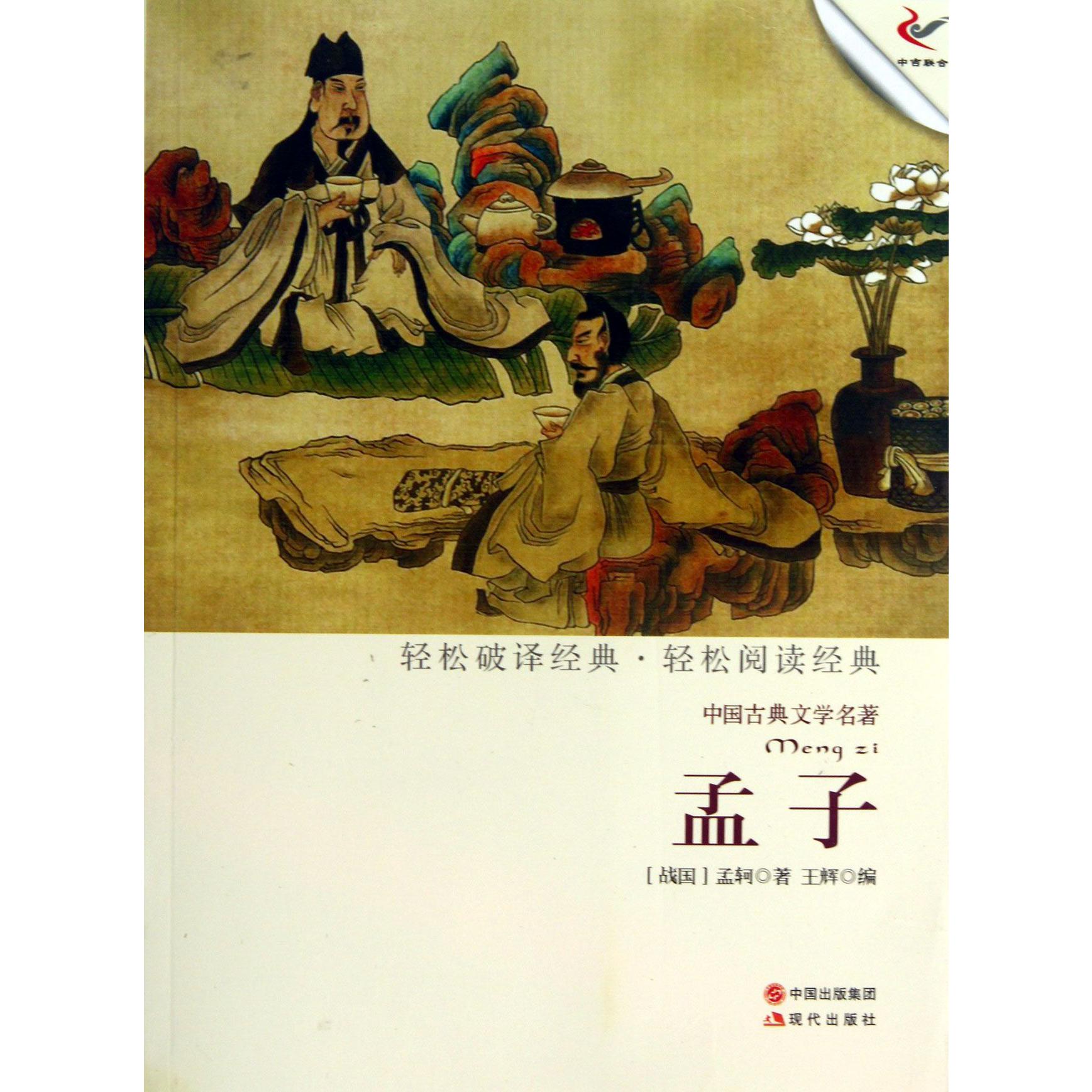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故乡曲阜不远,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三岁丧父,母亲仉氏把他抚养成人。“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故事,流传至今,影响深远。据《烈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无论是受教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学说无疑都受到了子思很深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孟子从四十岁开始教徒。和孔子一样,他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所以辞官还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是《孟子》一书的由来。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 “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 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 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 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 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 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 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减轻赋 税,发展生产,衣食无忧之时才能关注精神,而成“礼”。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混乱, 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 育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 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 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 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 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是怎 样称霸的,您能给我讲 讲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们没记录下齐桓公、 晋文公的事迹,所以齐、 晋二公的事迹没有传到后世来,我也不曾听过。王如 果一定要我说,就讲讲 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道:“要有怎样的道德才能够统一天下 呢?” 孟子说:“一切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安居乐业而 努力,这样去统一天下, 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吗?” 孟子说:“能。” 齐宣王说:“您从哪看出我能呢?” 孟子说:“胡龅曾告诉我一件事:王坐在大殿之 上,有人牵着牛从殿前走过, 王看见了就闸道:‘牵着牛往哪儿去?’那牵牛人回 答:‘准备宰了榘钟。’ 王就说: ‘放了它吧!看它哆嗦的,太可怜了,牛 本身没什么错,却被送进屠 宰场,我实在不忍哪!’那人就说:‘那么,难道就 废除祭钟这一仪式吗?’ 王又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来代替吧!’—— 不知道这事是否属实?” 齐宣王说:“有的。” 孟子说:“您有同情心就可以统一天下了。百姓 都以为王是吝啬,我早 就知道王是同情牛啊!” 齐宣王说:“对呀,竟然有这样的百姓。齐国虽 然不大,我也不至于连 一头牛都舍不得呀!我就是不忍看它吓得浑身发抖的 可怜样儿,毫无罪过而 被送进屠宰场,才用羊代它送死。” 孟子说:“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用小 的代替大的,他们哪能 理解您的良苦用心呢?如果说可怜它毫无罪过却被送 进屠宰场,那么宰牛和 宰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笑着说:“其实我也搞不懂自己是怎么想 的。我的确不是吝啬钱 财才用羊代替牛的。您这么一说,百姓说我吝啬真是 理所当然的了。” 孟子说:“百姓误解您没什么关系,您这种不忍 之心正说明您仁爱。关键是: 您亲眼看见了那头牛,却没有看见那只革。君子对于 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 着,就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哀号, 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 君子把厨房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就是这个道理。” 齐宣王高兴地说:“有两句诗歌:‘别人想什么 ,我能揣摩到。’您就 是这样的。我虽然这样做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您老人家这么一说, 我的心就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了。但我这种心情和 王道相合,又是什么道 理呢?” 孟子说:“如果有一个人对您说:‘我能举起三 千斤的重量,却拿不起 一根羽毛;我能看清候鸟的细毛,一车子柴火摆在眼 前我却看不见。’您能 相信这种话吗?” 齐宣王说:“不能。” 孟子随即说:“如今您的恩惠足以使动物沾光, 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 为什么呢?这样看来,拿不起一根羽毛,只是不肯用 力气的缘故;看不见一 车子柴火,只是不肯用眼睛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 的生活,是因为您不肯 施恩于民。所以您不行仁政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干, 不是不能干。” 齐宣王说:“不肯干和不能干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把泰山夹在胳臂底下跳过渤海,告诉 人说:‘这个我办不到。’ 这是真的不能做。替老年人折取一段树枝只是举手之 劳,却对别人说:‘这 个我办不到。’这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您不行仁 政,不属于把泰山夹在 胳臂底下跳过渤海一类,而是属于替老年人折取树枝 一类的。 “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 ;爱护自己的儿女,从 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如果以此作为惩治政的原 则,邪您想统一天下简 直太容易了。《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 推广到兄弟,再进而推 广到封邑和国家。’这就是说把这样的恩惠推广到其 他方面就行了。所以由 近及远地把恩惠推广开去,就足以安定天下;不这样 做,甚至连自己的妻子 都保护不了。古代圣贤之所以比普通人强百倍,没有 别的诀窍,只是他们善 于推行他们好的行为罢了。如今您的恩惠足以使动物 沾光,百姓却得不到好处, 这是为什么呢? “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 万物皆同一理。人心更 是这样。王,您考虑一下吧!难道说,动员全国军队 ,使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 和别的国家结仇构怨,这样做您心里才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为什么定要这么做才痛快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 过是想得到我最想要的东西啊!” 孟子说:“王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可以讲给我 听听吗?” 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就说:“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为 了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 是为了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是为了美好的音乐不够 听吗?还是为了侍候您 的人不够多吗?这些,以您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实 现,难道您真是为了这 些吗?” 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最想得到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您是想要扩张国土,使秦、 楚大国都来朝贡,自己做天下的盟主,同时安抚周围 的落后的民族。不过, 以您这样的做法想满足憨这样的欲望,好比爬到树上 去捉鱼。” 齐宣王说:“有这么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更严重呢。爬上树去捉鱼, 虽然捉不到,却没有祸害。 以您这样的做法想满足您这样的欲望。处心积虑,劳 民伤财,不但达不到目的, 反而会引祸上身。”齐宣王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可以讲给我听吗?” 孟子说:“假设邹国和楚国打仗,您以为哪一国 会打胜呢?” 齐宣王说:“楚国会胜。” 孟子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小国不可以跟大 国为敌,人口稀少的国 家不可以跟人口众多的国家为敌,弱国不可以跟强国 为敌。现在中国土地总 面积为九百万平方里,齐国的领土不过一百万平方里 。以九分之一的力量跟 其余的九分之八为敌,这和邹国跟楚国为敢有什么分 别呢?这条路行不通, 那么为什么不试着换条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 “现在王如果能改革政治,施行仁德,就会使天 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 来做官,庄稼汉都想到齐国来种地,行商坐商都想到 齐国来做生意,来往的 旅客也都想取道齐国,各国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们也都 想到您这里来控诉。如 果真能达成这种局面,又有谁能抵挡得住您呢?” 齐宣王说:“我脑子不好使,对您讲的理想不能 再有进一层的体会。希 望您辅佐我达到目的,明明白白地教导我。我虽然无 能,但可以按您说的试 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 念和行为准则的,只有 士人才能够做到。至于一般人,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 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 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 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等他们犯了罪,再去惩罚他们,这等于陷害。哪有仁 爱的人身为父母官却做 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 ,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 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农足食 ;坏年成,也不致饿死。 然后再去诱导百姓走正路,百姓就甘心听从他的命令 了。 “现在呢,规定人们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 ,下不足以抚养妻儿; 好年成,尚且度日艰难;年成不好,只有死路一条。 这样,大家想活命还怕 来不及,哪有闲工夫学习礼仪呢? “如果您要施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入手呢?每 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 让他们在四周种植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 以有丝帛袄穿了。鸡、 狗和猪这类家畜,都有力量和时间去饲养、繁殖,那 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 都有内可吃了。一家给他一百亩田地,并且不去妨碍 他的生产,就能解决八 口之家的温饱问题。办好各级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 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 来开导他们,那么,须发花白的人,就不致头顶着、 背负着物件在路上行走了。 老年人个个穿丝吃内,百姓不用忍冻受饿,这样还不 能使天下归服的,那是 从来没有的事。” P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