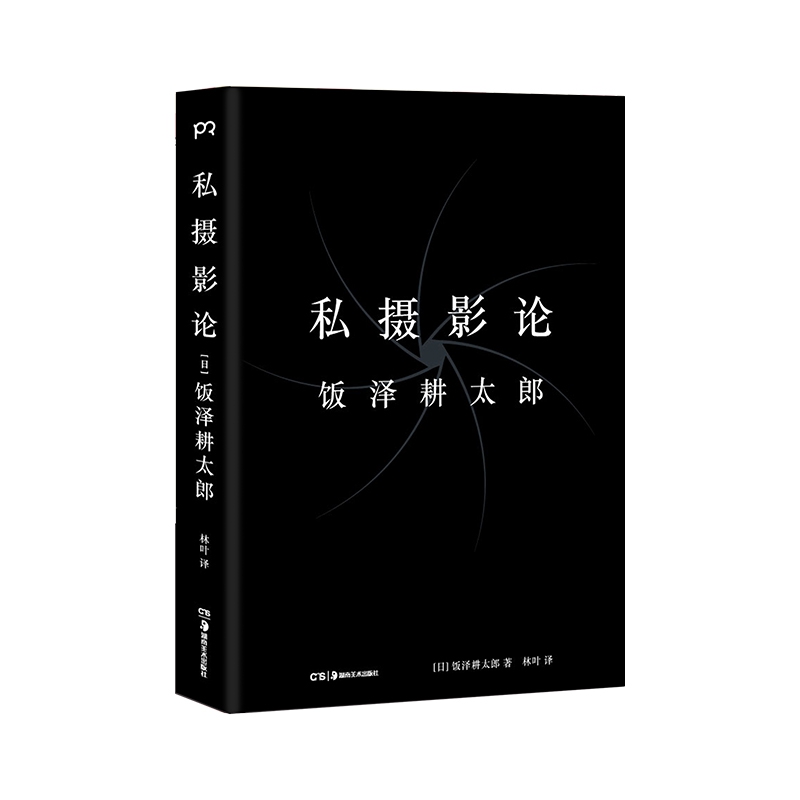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30
折扣购买: 白(精)
ISBN: 9787549512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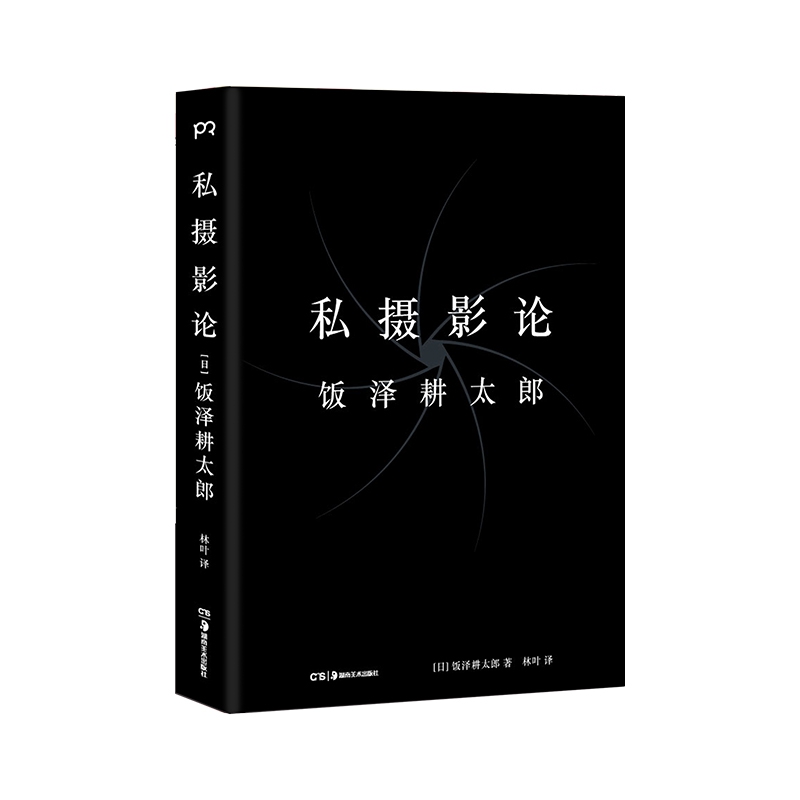
原研哉(1958— )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展现了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在银座松屋百货更新设计中,实践了横跨空间和平面的整体设计观念。在梅田医院CI设计中,尝试表现了触觉在视觉传达中的可能性。
作为创造催化剂的纸 纸常被称为“印刷媒介”,由于电子媒介的兴起,此 言尤为正确。但与电子媒介本质上缺乏实体存在不同,纸 的基本特性是无法用“媒介”这一概念完全概括的。 当我们以知觉的观点看待文化与文明,我们会发现, 一个时代的人们周围存在着一种刺激创造欲的催化剂。以 石器时代的文化为例,我们只需手握一柄石斧便可感受到 那造斧之人发自心底的创造冲动。石头的重量与触感给了 它某种可能性,激发着任何拿着它干活的人。石器时代持 续的时间惊人漫长,据说这种斧子的形状传承了有十万年 之久。我们在今日很难想象一种工具及其使用能保持上千 个世代基本不变,而当我们拿起这样一件东西,去感觉其 重量、硬度、质地,我们仍能从直觉上理解其创制背后的 那种冲动。即便是现在,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手里拿着这 样一件东西,我都会变得兴奋起来。这种兴奋可被视为一 种激发所有创造行为的动力。 铁器时代提供了类似的媒介。铁这种介质既硬且韧的 特性可视为农业和战争这类活动的一种催化剂。犁与铲翻 转土地的感觉鼓励人们去开垦荒地,建立和平的居所。而 他们侵略邻居的野心,他们对支配生死的力量的冲动,无 疑受到了寒光闪闪的钢剑之锋的刺激。 巴比伦时期的泥板与楔形文字则为另一种媒介。这些 泥板的表面并不总是平的,实际上许多都鼓得好像要爆开 一样,如同充斥着文件的笔记本,表面拥挤不堪地刻写着 细小的楔形文字。这些板子为何翘曲得这么厉害呢?原因 大约是它们得是便携的,这种形态能让它们挤下更多的字。 换句话讲,高密度排字的原因可能源于想令其可用表面最 大化的考虑。因此,字母一定要小,表面一定要弯。我们 可以从实实在在的东西——泥板本身,和它上面的文字 推断出这种愿望的强烈。文化是人类愿望的一种反映。如 我们将此愿望与一艘船上的风帆相比,我们就能看出风这 个关键角色,即盈帆的助力。沿着文化与文明,这样实际 的“媒介”总能找到。 纸的白色与弹性亦类似地刺激了人类的愿望。纸不仅 是一种无机物,一种可用于文字及图像印刷的中性表面, 纸的本性更将人们引入了一种延伸的对话,丰富了人们表 达自己的能力。书可理解为一种把这种对话往前推进的重 要工具。当我们沉入如空气般包围我们的电子媒介的内容 之中,我们难道不应首先重新评估其沟通的感性力量吗? 白的反刍 我的工作需要我坐在一台电脑前,花上相当长的时间 敲敲打打。即便现在我都是在键盘上敲着,但我也花同样 多的时间与纸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我能感到头脑的另 一部分正被激活,大脑消耗的能量突然剧增。我只需让我 的钢笔或铅笔尖与纸相触即可发生,而我的指尖与眼睛一 旦介入,我的反应就强烈了。例如,当我为印刷选纸,或 是在做书的过程中考虑用纸时,与其说是去接触纸,或许 更准确地说是我在对其进行反刍。我们用“反刍”这个词 一般是指牛对一团草反复咀嚼吞咽的行为,而这里我是指 对形象进行考虑与估量的重复过程。我从记忆里召集一系 列白的形象,然后悠闲地将它们与我面前的真纸进行比 较。“反刍”似乎与此行为完全吻合,比“选择”或“审查” 要准确得多。 书装设计始于将各种纸集合到一起。你需要一种纸用 于环衬,一种用于护封,一种用于内封,一种用于扉页, 如此等等。最终,还要有印正文的纸。近年来,我用彩色 纸越来越少。为什么是白纸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开始时我 被彩色纸的变化多端吸引住了,对色标本中的大量色彩运 用自如。而到了某种程度,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转向了白。 设计包含着对差异的控制。不断重复相同的工作使我 懂得,重要的是要限制那些差异,只保留那些最关键的。 我逐渐明白,如果我想编织一块有意义的地毯,重要的是 细微的渐变,而非悬殊的不同。如此,这块地毯便会精致 许多。当我在街上碰到的颜色变化激增,当纸质或电脑上 的色彩模版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我发现自己对颜色多 样性的兴趣反而少了,我只把最基本和必要的材料放到我 的工作台上。这个决定无疑左右了我的工作。因此到了某 种程度,颜色本身变得多余而过剩。 颜色当然是文化,我在关于传统色的讨论中已经指出。 黑白照片当然是美的,但若是把所有颜色都从世界上去掉, 它们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当然我也不觉得人造色就是丑的。 正相反,我欣赏那些迷恋原色及其他鲜艳颜色的人,我也 对能在真实世界中操控纯色的色彩计算能力着迷。不容置 疑,设计的正常做法不允许对颜色的忽略。我不是一个特 别喜欢白的人,也并不回避使用颜色。作为一个职业平面 设计师,我每天都要用到它。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当我动 用颜色时,我会敏锐意识到这样做的“功能性”原因。我 理解,红色是用于紧急事故按钮和灭火器的一种适当颜色, 简言之,支撑标识系统的逻辑出自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无论怎样,当我专注于工作中的细微情感与审美差异, 我即开始无意识地从人造色的洪流转向不太惹人注意的纯 自然色的领地。相比于对鲜艳与明亮的强调,我发现自己 更加震颤于旧书褪去之色、混入日本和纸的纸板上的灰色, 以及锈蚀的雅致之色。从植物种子与沙子那时尚、自然的 色彩中,我发现了真实,甚至是一种血缘关系。在所有这 些东西中,留下最伟大印记的是白色。 白纸有无数种。有些平滑如镜面,有些看起来则像鲨 鱼皮一样粗糙;有些有着石膏般平整的表面,有些则有着 蛋壳似的肌理;有些闪亮如覆上了滑石粉,有些则莹白如 雪。我们找到的白纸可能摸上去如阴天般模糊不清,看上 去如毛毯般又软又厚,或硬如木板,或轻如空气,或随和, 或强硬……这个单子可以这样一直列下去。因此,也许开 始时看着容易,其实为一本书选纸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 过程,因为要把这许多不同的“白”整合到一起。我们必 须在“红白”、“蓝白”与“黄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选 定适当的纤维长度和厚度。这样书的各部分就能各自扮演 其恰当的角色:护封传达一种有力的沉默,内封则为初启 之纯净,扉页乃新开始之肌理,正文则将文字与图像放在 清洁的背景上,或对读者的指尖柔声细语:“触摸我!” 白在与其周边颜色的关系中时进时退。有时它会显得 更“白”一些,有时又会显得不那么白,原因并非物理的, 而是要看此种对比是使它显得更亮,还是淡入背景,或是 显得暗淡。纸于今日是一种制造产品,已设立了标准,以 衡量其白度。碳酸镁——我们看到体操运动员在双杠比 赛前往手上擦的白粉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用于衡量白度已 有很长时间。近年来竟又开发出一种更白的纸,它不像荧 光灯那样发青,而是纯白。这种白能在与其他白纸的对比 中显出来。因此,当我们想要加重白时我们就用它。 到了某个地步我开始意识到,仅凭使用最白的纸并 不能使人获得白的最强烈印象。事实上,一本只使用纯 白的书给人留下的印象会很弱,远比不上一本对其封面、 腰封、扉页、正文等处仔细斟酌着使用的不同深浅白的 书。这大概是人眼对明暗的深浅适应太快的缘故。而只 有当我们的感官必须对透明度和重量也给予评估时,白 的完整面貌才会呈现,最强的效果才能获得。当把一张 半透明的玻璃纸放在一种带有蛋壳肌理的糙白纸上时, 一种白的深度感才会被唤醒。或当快速翻动镜子般的光 面纸时,我们会遇见一种石膏般不透光的白,我们即会 惊异于白之圣洁清丽。 白的物理标准,即所谓的白“度”,并非我们如何感 知白的一项指标。相应的,只是白度更高并不能形成我们 的印象。大簇怒放盛开的鲜花之自给予我们的体验,一旦 背后被衬上一张复印纸,立即就会遭到削弱。浅白的花瓣 饱含水分,而我们对其繁茂花朵之白的感知却是震撼的。 简言之,白是一种自我们的感觉之内产生的现象。 一本书的建构是基于对白的不断反刍,牵涉到眼睛、 指尖和记忆。我们对一本书的设计始于一本假书,一本空 白页的书,也就是说,一个纸制的建筑形象,而我已无数 次立起这样的大厦了。也许,像那白色的花朵一样,信息 就是这类实验行为与无意识之间的一种合作产物。我认为 这种过程支撑着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感知。 P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