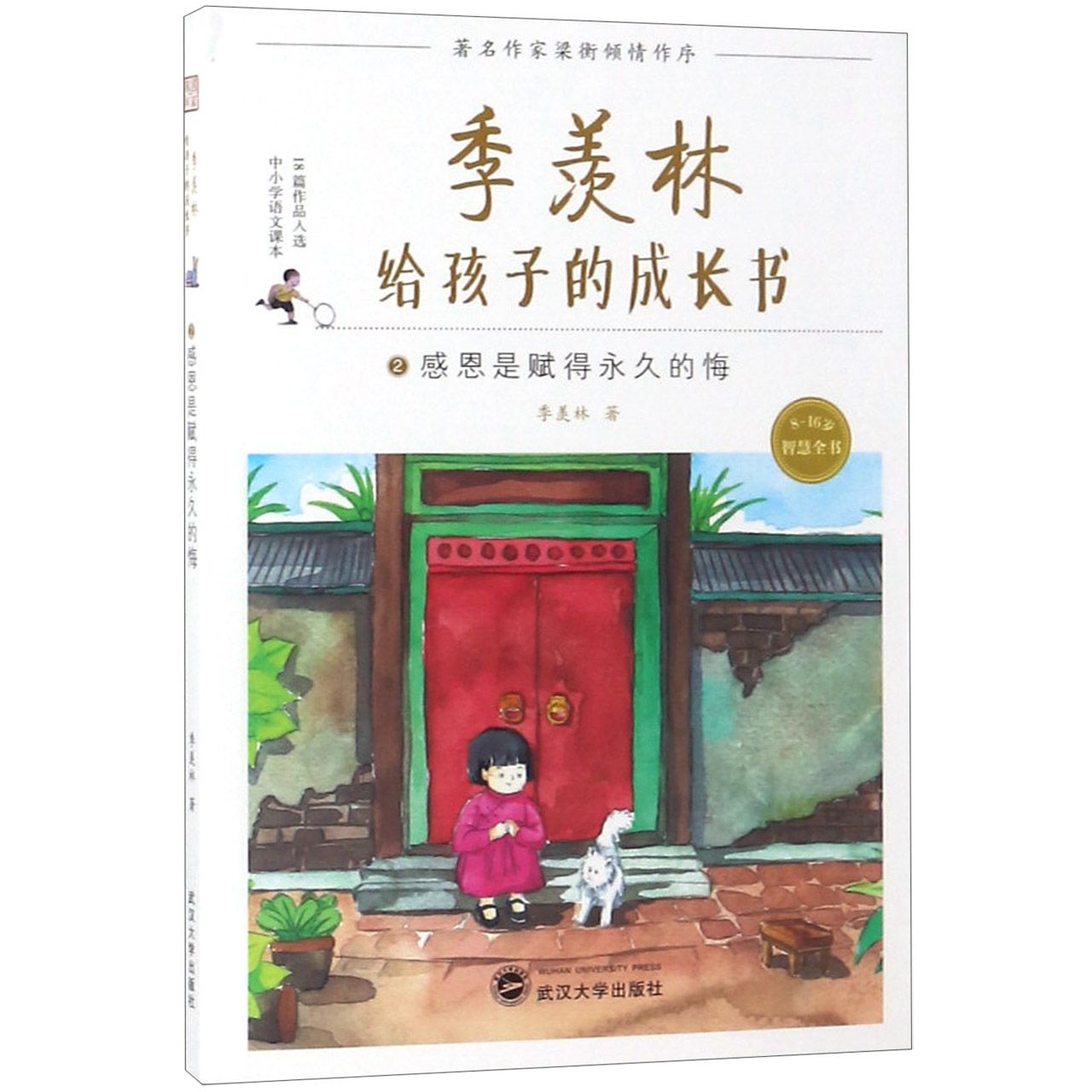
出版社: 武汉大学
原售价: 29.80
折扣价: 16.40
折扣购买: 季羡林给孩子的成长书(2感恩是赋得永久的悔)
ISBN: 9787307195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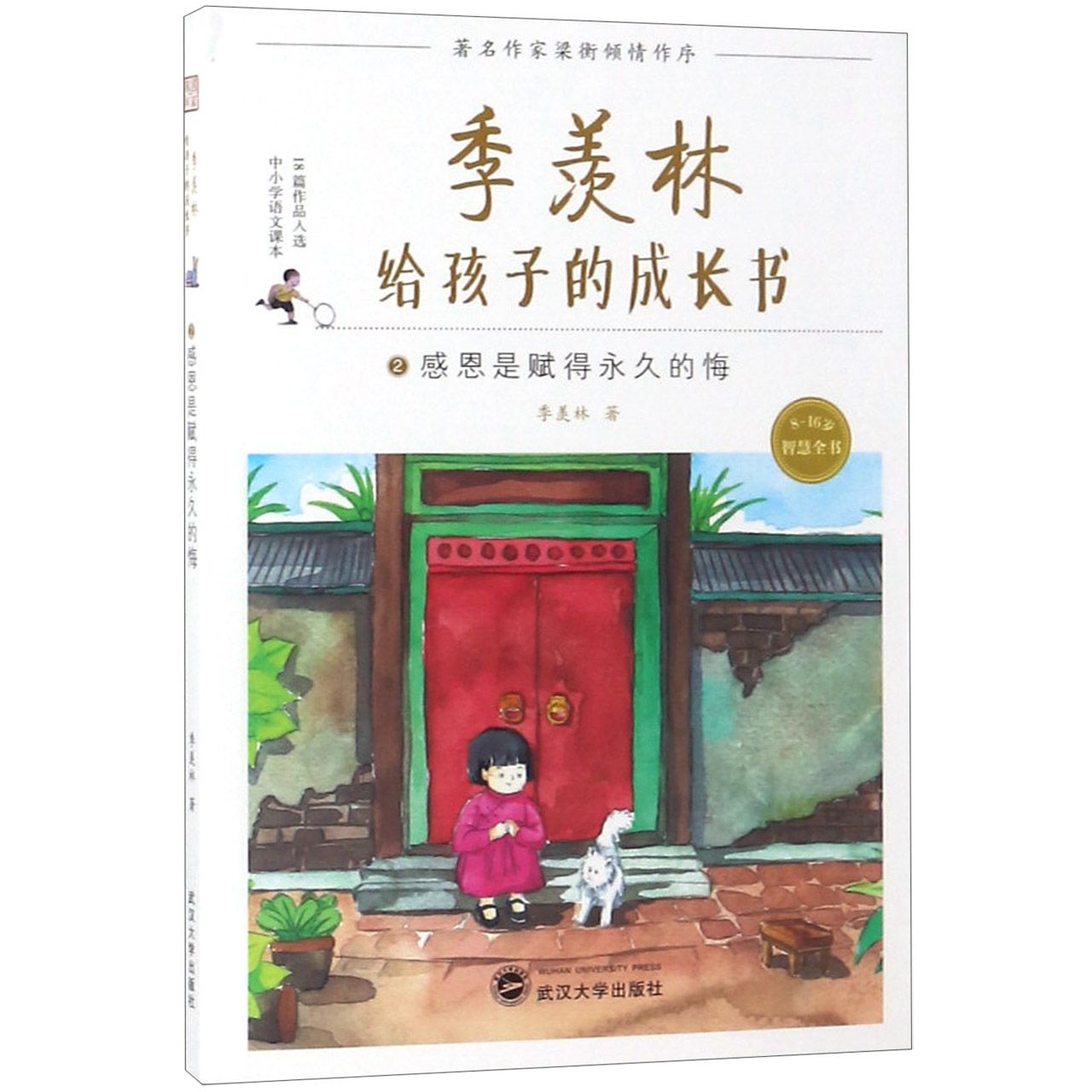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 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我祖父 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 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母亲的娘家姓赵,门 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 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 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 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 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 。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 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 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 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 ”(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 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 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 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 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 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 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 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 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 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 馍馍来。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 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 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 ——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 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 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 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 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 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 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 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 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 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 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 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 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 —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 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 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 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 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