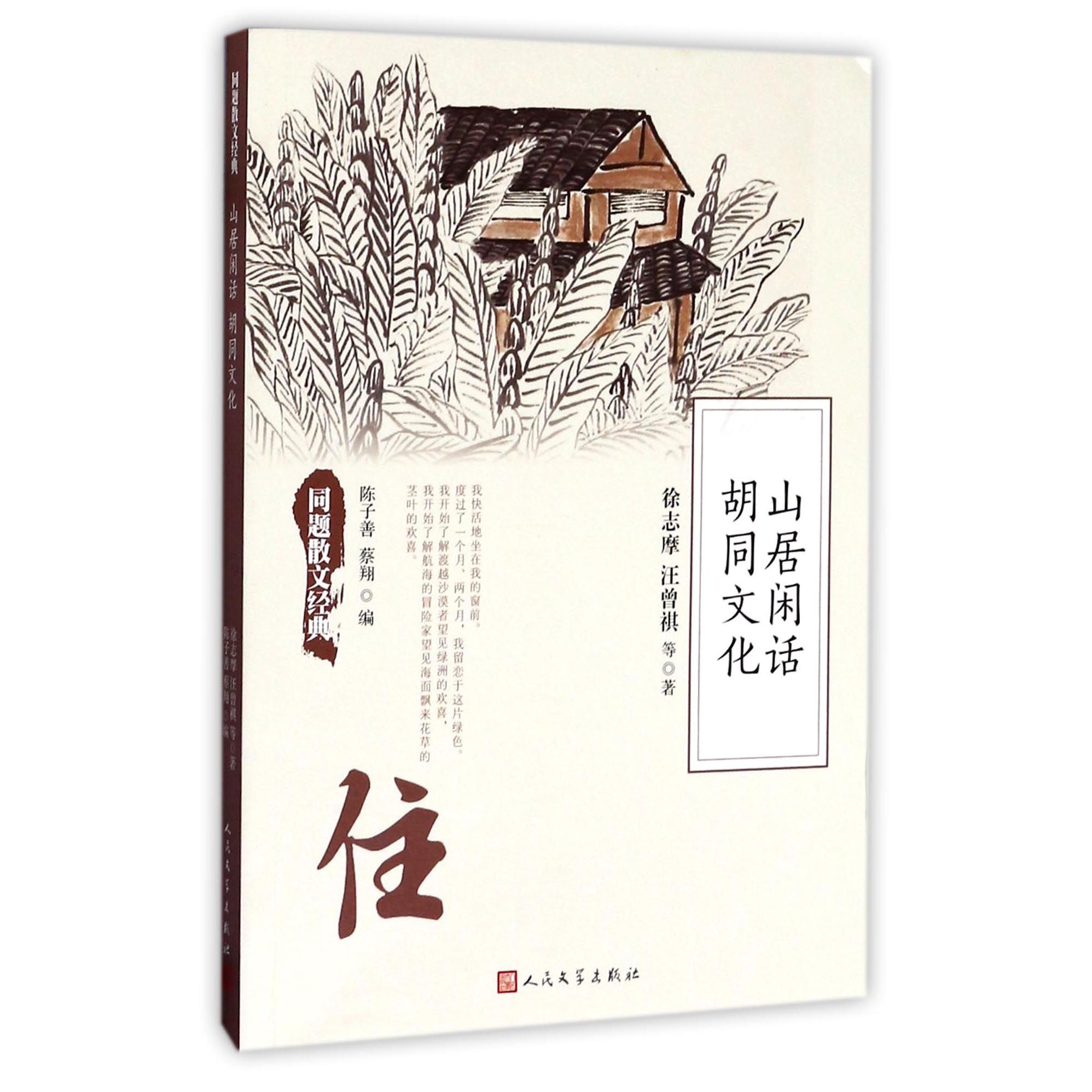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6.10
折扣购买: 山居闲话胡同文化/同题散文经典
ISBN: 9787020127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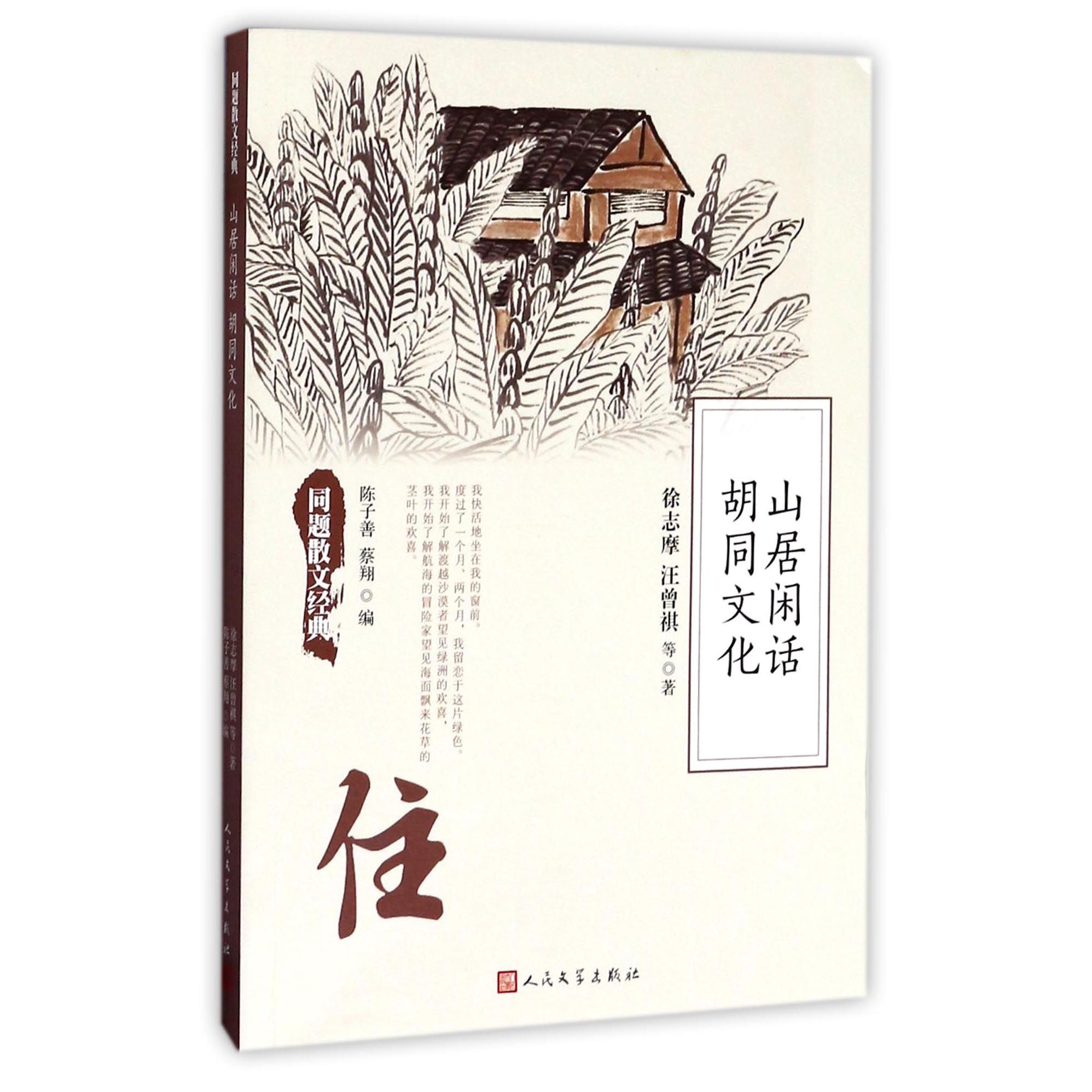
秋夜 ——野*之一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 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 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 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之蓝,闪闪地眨 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它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 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 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 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 开着,但是*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 泪擦在她*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 ,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 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 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 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 ,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 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 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 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 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但是*直*长的几枝, 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 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 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 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 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 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的,似乎不愿意惊 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 有别的人,我即刻昕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 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 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 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 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 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 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 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 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 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 小,向*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 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 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娱园 ◎周作人 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 的缘故。**是《夏夜梦》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 故乡城外的娱园。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 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 《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 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 。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 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 遍地都长了荒*,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 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记中称它“方池 湛然,帘户静镜,花水孕觳,笋石饾蓝”的便是。《 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樊樊山的《望江南》 云: 冰谷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偎瘦鹤,波摇琴 幌散文鱼:水竹夜窗虚。陶子缜的一首云: 澄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蛎洞,柳丝泉 筑水凫*:古帧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 电文,但因此总可约略想见它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 是废墟,但也觉得**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 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的游乐之地,也是一个 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舅父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 西厢,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秦氏的西邻是沈 姓,大约因为风水的关系,大门是偏向的,近地都称 作“歪摆台门”。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 已很是衰颓,我们曾经去拜访他的主人,乃是一个二 十岁左右的青年,跛着一足,在厅房聚集了七八个学 童,教他们读《千家诗》。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 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 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 忘记了是哪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那 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 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 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 姐,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 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秘地怀抱着对于她的情意,当 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 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 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Troubadour)的余风了。当时我 们住在留鹤盒里,她们住在楼上。白天里她们不在房 里的时候,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乘虚内犯”走 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 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 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 很得意的一件事。后来读木下奎太郎的《食后之歌》 ,看到一首《绛绢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