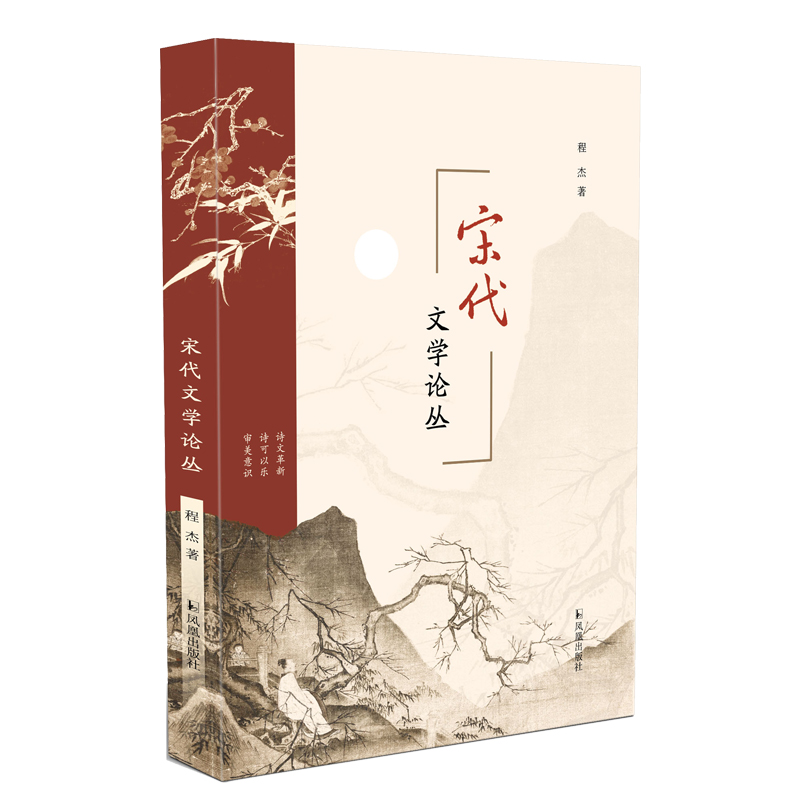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7.60
折扣购买: 宋代文学论丛
ISBN: 9787550636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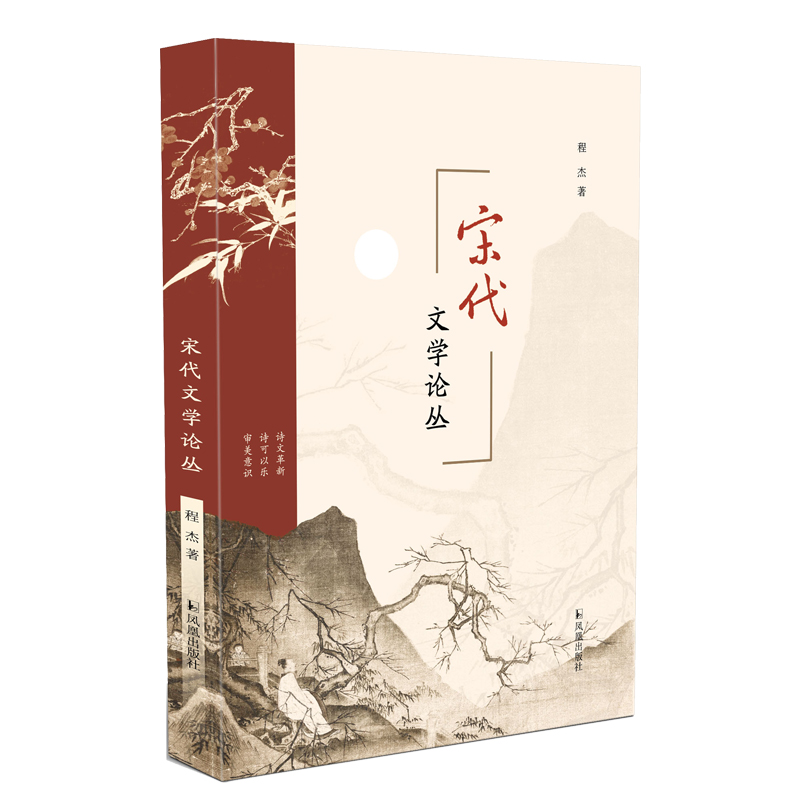
程杰,男,1959年3月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1975年高中毕业,在乡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82年本科毕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 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花卉文化研究,著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花卉瓜 果蔬菜文史考论》等书。
一、 宋初南方士人与晚唐五代文风的继承 宋初文坛的复苏是与整个南方士人的活跃密切相关的。《宋史·文苑传》前三卷收载宋初三朝文士三十八人,其中南、北(以秦岭、淮水为界)各十九人,可谓平分秋色。由于南北方在国家统一进程中有着时间上的先后,数量上的平衡并不能掩没南方实际存在的优势。这种优势到统一格局大为稳定的真宗朝便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宋史·文苑传》前三卷所载北方十九人中,十七人见于前两卷,主要活动于太祖、太宗朝,而南方的十九人中十五人见于第三卷,属于真宗朝。南方这种逐步发展的优势还可以通过一个诗人名单的统计数字来证明。杨亿《谈苑》曾列举宋太宗雍熙以来文士“能诗”者四十二名,其中里籍可考者三十八人,加上杨亿本人,南方是二十六人,北方仅十二人。南方之二十六人大都活跃于真宗朝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两处所引文字稍异,此处参用。。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南方士人不断增长的势头。 不仅数量上如此,在实际的文学才具上,南人也具鲜明的优势。宋初北方士人中固然有宋白、李昉这样以诗才著称的文学之士,但如《文苑传》所载梁周翰、郭昱、和岘、柳开等人是以“习尚淳古”或律历学问为世所知。而南方士人则普遍地以诗赋之才称胜。如太宗朝之杨徽之、徐铉,真宗朝之路振、杨亿、钱惟演等都以词翰敏赡称雄一时。 宋初南方士人在文学上的优势,是晚唐五代南方文学活跃状况的继续。唐末五代,中原干戈不断,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地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文学活动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州士人纷纷投身南方,如牛希济、韦庄、张蠙古、张道古入蜀,江为、韩偓避闽,高越等仕南唐,其他投老南迁或流寓江南不归者更多。宋人《莆阳志》记载:“黄滔字文江,乾宁二年乙卯赵观文榜进士,光化中除四门博士。寻迁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者,滔规正有力焉。中州若李绚、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传懿避地于闽,悉主于滔。”黄滔《唐黄御史集》附录,《四部丛刊》本。这是闽中一地的情况,其他地区不难推想。 当时诸国霸主为了网罗人才,于文学之士多能礼遇善待,如前蜀王建“虽武人,颇折节好宾客,游士、缁流至者,无不倾怀结纳”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〇〇,清康熙汇贤斋刻本。。前蜀王衍、后蜀孟昶都雅好艺文。吴据今江、皖、赣诸地,擅渔盐之利,物产富饶。南唐代吴,李璟、李煜工诗善词,上行下效,一国君臣,文采炳焕。吴越诸王皆具文采,宗室善诗者颇多。至如楚之文昭王马希范,史家称其“好学善诗,颇优礼文士”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八。,幕下人才济济,齐己、徐仲雅等“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引《雅言杂录》。。乱世之下,文学依附于南方诸国霸主,获得生息的机会。 五代之际的南方文学弥漫着“缘情绮靡”和苦吟弄巧的风气。肇自晚唐,国势衰颓,社会黑暗,士人消沉之余,多寄情诗酒声色,文风因之哀怨萎靡,其中尤以温庭筠、韩偓等人的“花间”“香奁”之作最为突出。这种文风被五代中原的连年干戈挤压到南方富庶苟安的环境里进一步滋长,又与江南僧侣、隐士的林下唱和、僻居苦吟之风气合流。这两种文风都注重字词、格律等方面的技巧。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也务以精意相高”。五代之际,各种诗格、赋格、诗句图之类著作极多,几乎构成了一个“诗格的时代”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8页。。唐末五代文学理论中最流行的审美范畴是“清”“丽”二字,如欧阳炯《花间集序》、韦縠《才调集》自序、徐铉《成氏诗集序》都以此二字誉人文才之美。所谓“清”主要指音律的细切谐婉,所谓“丽”则指词藻的赡美富艳,总归是对词采声韵技巧的重视,集中体现了士风浸弱、寄情声色、耽愉辞华的衰世审美心理。 宋朝立国,在文学政策上一开始便缺乏唐初君臣那种以史为鉴、摈弃浮华、取裁前朝、融合南北的阔大气派。正如王夫之所说,“宋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其得天下于一朝一夕,故“承天之佑,战战栗栗”王夫之《宋论》卷一,清道光二十七年听雨轩刻本。。这样的忧患防范心理决定其在文化建设上表现出谨小慎微、攀美前朝、笼络人心、期求粉饰的倾向。“太祖尝顾近臣曰:‘五代干戈之际,犹有诗人。今太平日久,岂无之也?’”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二引《古今诗话》。这是对诗人以文效忠的期待。落实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便是广开科举、精择翰林、优礼文士、奖劝艺文等一系列袭唐崇文之举,因之在全社会养成了普遍的崇文风气。正是适应“润色鸿业”的时代需要,南方士人以其优越的词翰之才成了宋初文化复苏和建设的主力。早在统一战争尚未结束时,宋廷“李穆使江南,见其兄弟(引者按:徐铉、徐锴)文章,叹曰‘二陆不能及也’”脱脱等《宋史》卷四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徐铉入宋后,中州士人纷纷归之,遂为文坛盟主。李至师事徐铉,“手写铉及其弟锴集,置于几案”《宋史》卷二六六。。杨徽之以南人入北,诗名赫赫,宋太宗“闻其名,索所著,数百篇奏御”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后诏李昉编《文苑英华》,“以徽之精于风雅,分命编诗,为百八十卷”《宋史》卷二九六。。宋初屡荐神童,贾黄中、刘少逸、杨亿、晏殊、夏竦等人都是几岁、十多岁便以诗赋天才被地方官表荐朝廷,受试获官。其中除贾黄中是沧州人,地属北方,其余均为江南人。宋初有所谓诗歌“三体”(白体、昆体、晚唐体),就时间上看,典型的“白体”浅切平易诗风主要见于王禹偁、李昉、李至等北方士人,而“昆体”“晚唐体”之绮丽和精巧与五代江南士人吟业风习一脉相承,其中名家如杨亿、钱惟演、林逋、“九僧”都是南方人,其流行范围也主要是南唐、吴越故地。 在宋初三朝逐步活跃的江南籍士人中,杨亿的崛起最具代表性。杨亿,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家世尚武,财雄当地,曾祖辈始读书为士。从祖杨徽之,随邑人江文蔚、江为习诗学赋,并与之齐名,后潜赴中原,以诗才蒙太宗知遇。杨亿“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后入馆阁,为词臣《宋史》卷二九六、三〇五。。杨氏祖孙以闽人相继显名当世,为文坛盟主,代表了南方士人应时而起、以才艺致身的奋进姿态。闽越自古属荒屿边隅,民风鄙陋,唐德宗贞元八年(792),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李绛同登“龙虎榜”,由闽入京,一路强烈地感受到故里文化落后的孤寂:“某世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欧阳詹《上郑相公书》,《欧阳行周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经晚唐五代经济之开发、文化之孕育,加之北方士人南下之影响,入宋后闽中文教便为江南之先。《宋史》地理志称闽中风俗“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宋史》卷八九。。宋真宗时泉州人段全《仙游县建学记》称:“圣宋以文化天下,岁诏州县贡秀民,士倍于昔,而闽人十计三四。”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九五,巴蜀书社1989年版。杨亿等闽中士人在宋初文坛的崛起,正是五代以来闽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 杨亿在真宗朝以“西昆酬唱”和“时文”风采耸动天下。虽然其中刘筠(河北大名人)等人作为辅佐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杨亿却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时诗赋、四六中讲究词藻、音律、组织的风尚主要是由杨亿、钱惟演等人作成。追溯其源,不难发现,这种风尚是晚唐五代诗赋绮靡之风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杨亿推崇李商隐之“才调”“雅丽”,又慕唐彦谦之“清峭感怆”,主张诗歌应“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其实质仍不出晚唐五代诗美意识中的“清丽”之求。据记载,杨亿之创始“西昆体”是他“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细加研味推求的结果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但存在如下情况:唐末五代绮艳诗风的代表作家韩偓流寓闽中,以晚辈亲戚与李商隐交往颇深,其《无题》、咏物及艳体诗都受到李商隐的直接影响;莆田徐寅善律诗,今见于《全五代诗》者二百六十余首,全为近体,且以七律为主,他的赋当时被“目为锦绣堆”刘克庄《徐先辈集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四部丛刊》本。原文“绣”作“锈”。;另如陈贶、江文蔚、江为等人诗歌都以近体为主,风格靡丽纤巧。因此杨亿之学习李商隐,致力于近体,风格赡博秾丽,不得不说受到了这些闽中前辈的影响。当然,杨亿等人的创作带有真宗朝承平有日、民康物阜、文化蕴积的特定时代色彩,与晚唐五代之末世衰颓卑陋相比,艺术格调和技术水准都有了不少改变和进步,杨亿等人的创作在当时被目为“新体”便是这个原因。 总之,宋初三朝是宋代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完整阶段,政治思想上的抑武右文、“文德致治”和实际制度措施上的袭唐之故、摹唐之盛,构成了文学上铺摛辞藻、润色鸿业的现实基础。南方士人以其与前朝文学风习的紧密联系,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宋初文坛的主角。 阅读资深学者的精华文章合集,深入领略大宋文学的优雅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