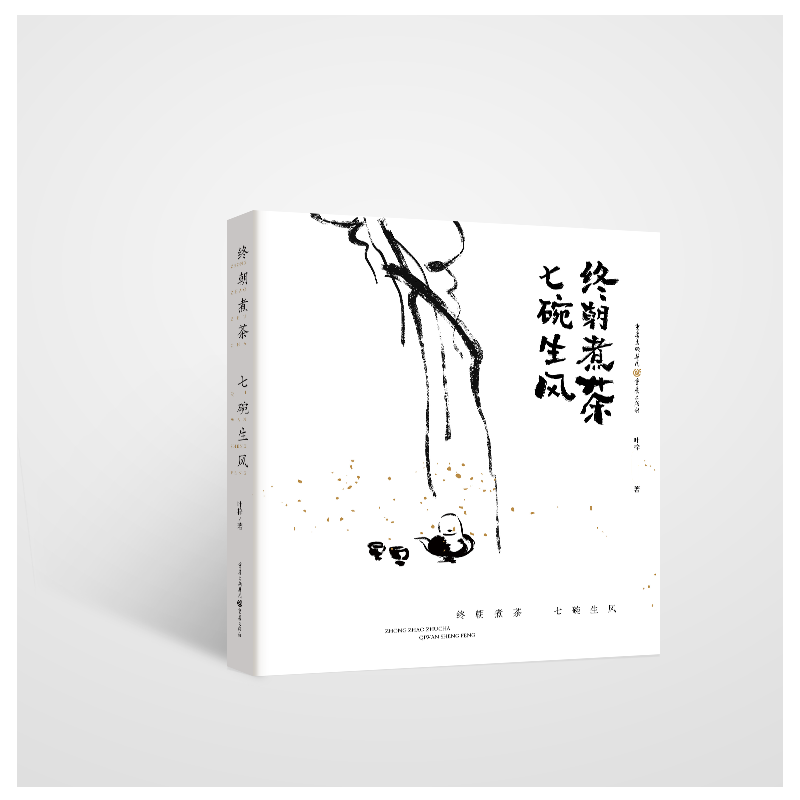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2.30
折扣购买: 终朝煮茶七碗生风
ISBN: 9787229153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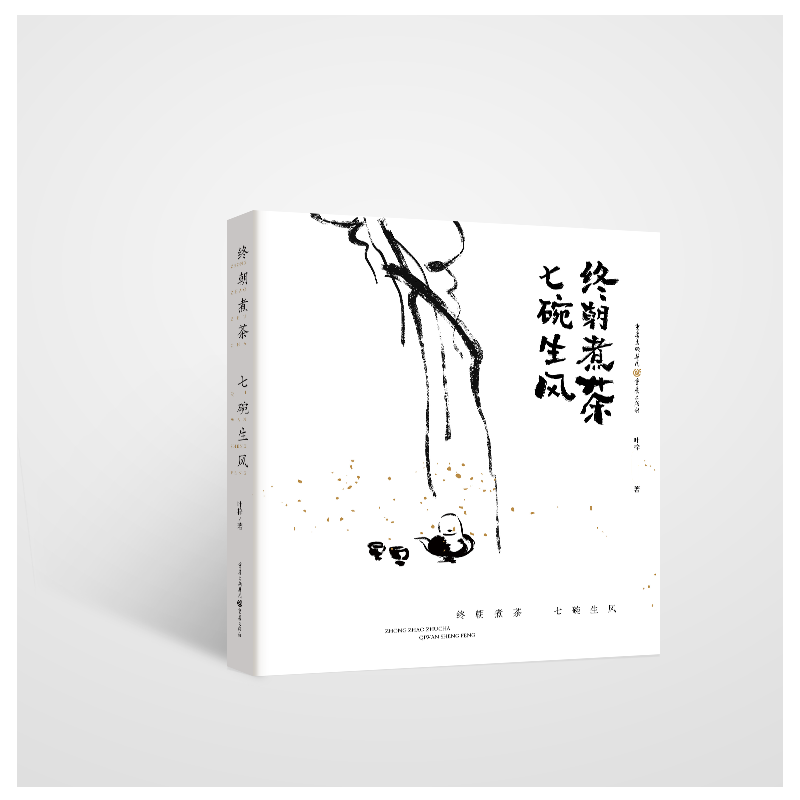
叶梓,本名王玉国,中国作协会员。现居苏州,供职于吴中文化馆。出版有《馈赠》《天水八拍》《流浪的诗圣》等。
葛 仙 茶 圃 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那个久远时代里,大地深处充满了阴谋、血腥、杀戮与残酷。 刀剑相见的影子,在白花花的阳光里,寒气逼人。但远在江南的天台山顶,却有人安心 求道,与世无争,在那古木参天葱葱郁郁的华顶山峰的一间小小寺庙里,随心所欲地活 着。他自吴国赤乌元年的某一天开始,于山顶创建道观后,开辟茶圃,以茶养生,以读 老庄安度余生,累了,就走出居住着的山洞——后世者命名为归云洞——在茶圃里散散 步,放松一回。回来的时候,眼前自然会多出一杯汤色鲜亮的茶。他在独享着这份宁静 时,并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在多年之后的唐代,有一个叫陆羽的人,没有忘记他曾经 在这里生活过的隐秘历史,并且怀着一腔敬意前来瞻仰他生活过的这块仙气盈盈的地 方——甚至有日本的僧人前来在此求学,并且在归国时带去了若干茶种,在他们自己的 国度种下了第一株茶。又过了很多年,另一位日本高僧虚心地来这里考察茶种,研习茶 道,撰写 《吃茶养生记》,成为传播天台山茶文化的鼻祖,且被日本国尊称为“茶圣” “茶神”“茶祖”——浪潮般奔涌而来的盛名,反而让更多的人记下了华顶山峰那间小小 寺庙里的主人——葛玄,生于164年,卒于244年,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道士,天台山道教 源流始祖,被后世尊为“太极左仙翁”,故叫葛仙——他的一生像一片隐于时间深处的茶 圃,甚至没有肉体,只有辽阔的云雾烟岚。 茶 山 居 士 南宋诗人曾几,因反对秦桧议和而遭贬,就去了江西上饶广教寺寓居,旁有茶山, 遂自号茶山居士。这里的居士,大抵就是隐士的代名词,与宗教关系并不大。在古代的 中国,文人们常常以居士自居,如李白号青莲居士,范成大号石湖居士,这既是文人的 自我放逐,也是佛教在文人心理上的投影。当然,居士也并非佛教专指,作为隐士之一 种,早在 《礼记》 里就有这层意思了—— 《礼记》 里的“居士锦带”一语,就是这个 意思。 曾几偏偏自号茶山居士,是因为广教寺旁即是茶山。 我常常想,那是一片什么样的茶山呢?我是北人,进茶园的机会不多,更何况是进 一片史籍有载的南宋茶园。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必定不是一片轻风能把汽车尾气吹进去 的茶园,而是一片清风、雨露、阳光与株株茶树的秘密集合之地。稍后,则知道此茶山 早就因“茶圣”陆羽而出名了。据南宋韩元吉《两贤堂记》载:“广教僧舍在 (上饶) 城 西北三里而近,尤为清幽,小溪回环,松竹茂密。有茶丛生数亩,父老相传唐陆鸿渐所 种也,因号茶山。泉发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陆子名。”这样的叙述让我不禁要想,曾几是 不是因为茶神陆羽曾经造访而索性隐居这座茶山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上饶籍女诗人林莉告诉我,茶山之茶,已经不是当年的茶了。而且,清代张有誉 《重修茶山寺记》 里叙述过的那眼色白味甘、被誉为天下第四泉的陆羽泉,在某个狂热的时代里因为“挖洞”而泉脉皆损,只剩下古人所题的“源流清洁”几个篆体小字,作为后人凭吊古迹的唯一标志了。 不过,茶山居士的来历,仅有茶山可能还远远不够,一定与诗人的嗜茶不无关系。 我这么判断,是因为我确实读过他的茶诗。而且,元人方回在评论时言之凿凿地说:“茶山嗜茶,茶诗无一篇不清峭有奇骨。”据细心的权威人士考证,曾几的诗集 《茶山集》里,涉及茶的诗有二十余首,而我独喜欢这一句:独烹茶山茶,未对雪峰雪。 这句子,对仗工整,既入江西诗派,又出江西诗派,自然流转,独成一格。因为这句诗,我喜欢上了整部《茶山集》。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因为某一点而会忽略其他的毛病与缺点。关于《茶山集》,《永乐大典》里说:“凡得古今体五百五十八首。虽不足尽几之长,然较刘克庄《后村诗话》所记九百一十篇之数,所佚者不过三百五十二篇耳。 隐 于 茶 大隐隐于市。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说的是真的隐士,往往就在日常生活里。但是,市者 大矣,有人隐于学,有人隐于商。我这里说的隐于茶,则是想说,一介真的隐士,他的 案前总有一杯清淡的茶,寂寥,清雅,又有辽阔的风吹来。 茶,是一个隐士的日常。 中国古代的隐士,是农耕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所谓隐士,大部分会选 择过上一种农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田野,栽桑植麻,既解决日常生活, 又是隐者的一件外衣。因此,栽茶采茶也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一。于是,他们耽于啜 茶,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况且,茶本温和,跟隐士修身养性的志趣一脉相承。 张源于1595年前后著述的《茶录》,叙及饮茶体会和心得,顾大曲在序中说: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 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这位“隐士”深山苦读,逍遥自在,若不是 以“独饮自娱”,漫长的三十年,能够坚持下来么? 南宋诗人赵师秀刻画过一个僧人,既隐于山林,又隐于茶,“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 灯”,日日以品茗礼佛为事,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此离尘出世的生活,一般人是过 不下去的。 作者以悠久厚重的中国茶文化为背景,以散文的方式勾勒了一个缤纷的茶世界,茶史、茶器无所不包,亦有一款款茶随文字呼之而出,尤其是以日记体的方式所呈现的紫砂世界,颇见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