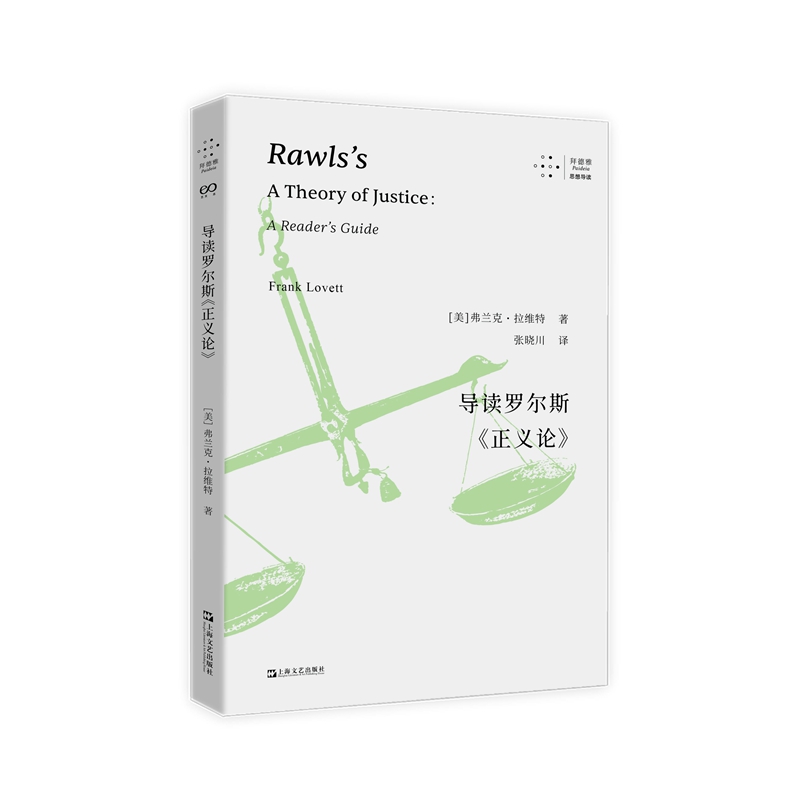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9.80
折扣购买: 导读罗尔斯《正义论》(拜德雅·思想导读)
ISBN: 9787532191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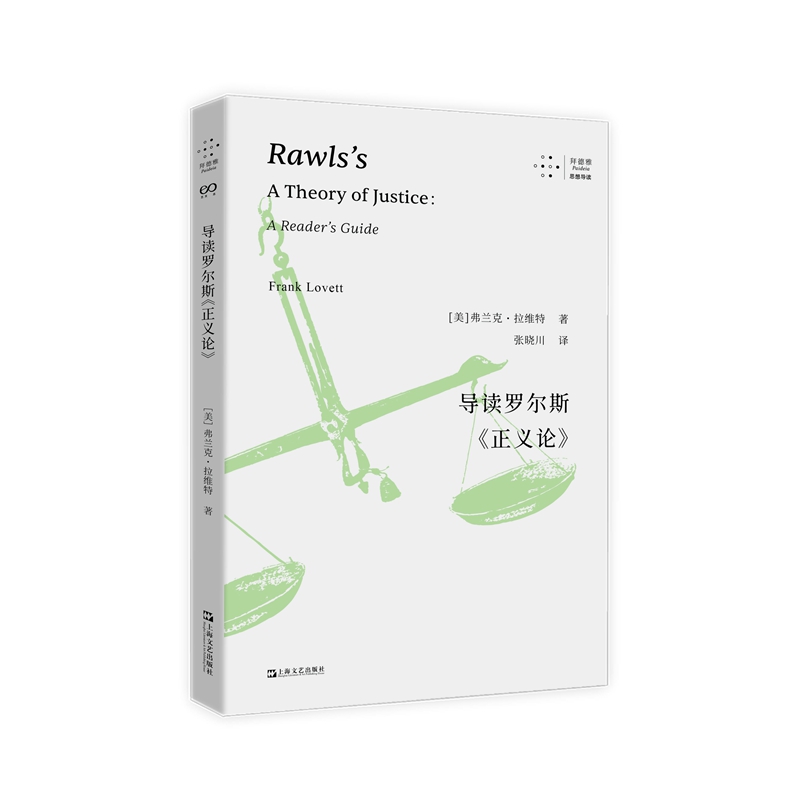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弗兰克? 拉维特(Frank Lovett),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副系主任,政治学、哲学和法学教授。他主要研究自由与宰制同正义理论、平等及法制的关系,常年开设规范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的课程。 译者简介 张晓川,哲学与翻译爱好者,译有《导读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关键概念》。
《正义论》中心思想 《正义论》这部著作篇幅长、密度大,总共近600页,读时极易迷失在细节中。因此,在上手读解文本时,对罗尔斯所要论证之点有一种整体认识会很有好处。本章意在提供这种认识,并附一份简略指南,以便读者在这本大书中寻找方向。幸好,领悟罗尔斯的论证的中心思想是比较容易的。 请回忆一下,我们曾在第1章提到,在罗尔斯最初形成其见解时,有两种道德与政治哲学理论正在较量。前一种理论,也是占优的理论,当然是效用主义。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其他一切理论看起来都远不如效用主义那样有力而精致。但同时很多人也承认,效用主义也有几项令人不安的特点,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一些。眼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另外一点。请想象,在某个社会,有一个很小的少数群体陷于凄惨的奴役状态。这些奴隶当然很不幸福,但在有这些奴隶时,其他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幸福一些,毕竟奴隶们被命令去从事社会中很多较繁重的工作。那么,当我们把多数人幸福的增进加在一起时,总和也许竟会远大于奴隶们遭受的不幸福的总和,尽管每个奴隶个体确实很不幸福。在这个社会中,效用主义看起来会赞成奴隶制。我们当然不希望计算出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这该有什么要紧吗?换句话说,奴隶制正义与否,难道取决于碰巧计算出什么结果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有强烈的道德直觉:不——多数人的幸福是否超过奴隶们的不幸福,这不该有什么要紧,因为奴役人类的做法一看就是根本错误的。 难处当然在于这不过是个直觉。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理论,即直觉主义。但是,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的那样,原来直觉主义并不真的是个理论,它不过是给我们碰巧拥有的一团杂乱无章的道德直觉起的名字而已。直觉主义无望击败效用主义,因为它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当我们的直觉不完整、不清晰或者(在最坏情况下)互相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做。罗尔斯想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理论,既像效用主义那样有力而系统,又能更好地说明我们的道德直觉——例如说明奴隶制何以具有内在错误。这样一个理论会是什么样的? 为了从整体上认识罗尔斯如何着手迎接挑战,首先有必要引入一些基础性理念。这些理念,待讨论到文本中的相关段落时,我们还会回头细讲;眼下,对它们的重要意义有一般性的把握就够了。第一个理念是社会之为“一个合作体系”(a system of cooperation)的理念。这是一种思考“何为一个社会”的方式,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考“何为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特点”的方式,对此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想象三位朋友要合伙开公司。其中一位是优秀的产品设计师,另一位有营销天赋,第三位是老到的会计。若一起工作,他们的合伙将会成功,赚很多钱,但若各自独立工作,或者互相竞争,他们就无法成功。假设他们确实同意一起工作。到了某个时候,他们总要决定新公司的利润如何划分。那么要依据什么规则划分才好?产品设计师可以争辩说,没有产品就没货可卖;她的贡献是最基本的,所以她应该拿利润的大头。营销人员可以争辩说,没有他的努力,他们就没有顾客,也就没有利润;所以他的利润份额才应该是最大的。依此类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们如果都同意某一条规则,那么这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不然就根本没法合伙,也就不会有利润可供划分;但同时,究竟应该同意哪一条规则,也许他们各自的想法会相互冲突,毕竟不同的规则有利于不同的人。因此,他们的合伙既是互利的,也是潜在分歧的源泉。 罗尔斯认为,我们可以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来考虑整个社会,即便它规模更大也更为复杂。如他所言: [……]一个社会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多少自足的联合体,这些人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都承认某些行为规则具有约束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它们而行动。我们再进一步假定这些规则指明了一个旨在推进参加者的利益的合作体系。那么,虽然一个社会是一种为了互利的合作事业,但它却通常不仅具有利益一致的特征,而且也具有利益冲突的特征。(4;修4) 例如,考虑一下不同社会中的工作是怎样得到充任的。在封建社会,工作通常按出身分派;比方说,你父亲是银匠,那你也是银匠;你父亲是农民,那你也是农民;依此类推。与此相对,在指令经济体制的社会,工作由政府计划者分派,他们要做的是对你的能力与共同体的需要进行某种评估,并据此调配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由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分派,而劳动力市场不但受供求法则制约,还受劳动法规、许可要求等规范制约。在罗尔斯心目中,这些例子都是规定着“一个合作体系”的“行为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推进参加者的利益”(比如说我们都因分工而受益),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当作“一种为了互利的合作事业”。但同时,既然某一种规则配置可能有利于某些人,另一种配置则有利于另一些人,所以社会“不仅具有利益一致的特征,也具有利益冲突的特征”。挑战在于确定哪种合作体系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罗尔斯思想的第二个基础性理念,他称之为“社会的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a society),并将其定义为“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责任,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效益之划分的方式”(7 ;修6)。为了弄明白他这是指什么,我们最好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考虑某个社会中的两个成员,安德烈娅和鲍勃。不妨假设他们是差不多同样聪明、同样有能力的个体,但安德烈娅勤劳,而鲍勃懒惰。现在,如果问我们,可以预期谁的生活整体而言会过得更好(这里的“好”取其常规含义),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大概会认为是安德烈娅。但这未必能一概而论;很多事情取决于他们碰巧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例如,想象他们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安德烈娅生而为农民,鲍勃生而为贵族。就算安德烈娅付出的努力远多于鲍勃,可她的生活,无论以何种合乎情理的尺度衡量,大概总会过得远不如鲍勃。或者想象安德烈娅生来是19世纪早期美国南方的奴隶,而鲍勃生来是种植园主人的儿子:同样,安德烈娅再努力,过得大概还是会比鲍勃差很多。这些例子表明,我们的生活过得怎样,只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个人努力。这当然不是说个人努力不算什么——安德烈娅勤劳大概会比不勤劳要成功些。要点只在于,社会的具体组织方式往往会起相当大的作用。 罗尔斯所说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大体上就是指这个:除了个人努力,还有一套社会制度与实践也系统性地影响我们可预期的生活状况,而基本结构指的就是这套社会制度与实践。这套制度和实践显而易见地包括某些事物,如政府和法律体系,但也不那么显而易见地包括另一些事物,如经济体系的组织,又如某些情况下的文化状况。举一个经济体系的例子。假设鲍勃碰巧有在棒球比赛上击出本垒打的天赋。那么,他的生活过得怎样,将部分地取决于他多么努力地培养自己的才华,但也将部分地取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如果有一个交易棒球才华的自由市场,那么他的生活状况就可能会比没有这么一个市场的情况好很多。再举一个文化状况的例子。假设安德烈娅生在一个存在深刻性别歧视的社会。就算这种一般性的性别歧视并未反映在正式颁布的法律和政策上,她的生活状况大概还是会比活在一个不那么性别歧视的社会要差。由此我们了解到,社会基本结构这一理念是极为宽泛而抽象的:任何制度和实践——不论是法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只要构成了社会成员按自己的打算尽量过好自身生活的背景条件或社会环境,都包括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 尽管这个基本结构的理念极为宽泛、抽象,但它其实为罗尔斯提供了把他与效用主义的争执收窄的依据。这是因为效用主义往往不仅仅被解读为一个有关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理论,实际上还被解读为一套完整的道德哲学。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效用主义为之提供回答的问题,也许不仅包括奴隶制是否可以接受,还包括我是否应当为了保护朋友的感受而对朋友撒谎,我的加薪是应当花在一台新车上还是应当捐给慈善机构,等等。对效用主义的较宽的解读和较窄的解读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符合效用主义创立者(边沁、穆勒等人)的初衷,都是存在争论的话题,但我们在讨论罗尔斯时可以不去管这些争论。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正义论》所针对的是较窄意义上的效用主义,即一套关于所谓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理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社会设想成一个互利的合作体系(如上文所讨论的),并且如果我们设想那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确定了合作的主要条款,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社会正义理论设想为一份说明,它说明的是哪一种可行的基本结构最好地体现了正义这一德性。用罗尔斯的话说,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7 ;修6)。从这个观点看,效用主义就是持如下观点的理论:最为正义的基本结构是倾向于使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总和最大化的基本结构,其中每个成员的幸福要平等地计入。我们可以不去管效用主义是否可以作为一份有道理的、对一般而言的道德的说明,而是更狭窄地询问它是不是对社会正义的最佳说明。在罗尔斯看来,它不是。那么他认为更好的说明是怎样的? 为了领略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再借助一个简单的示例。想象一个富有的牧场主去世了,把他的牛留给了两个儿子,但没有具体说哪些牛给哪个儿子。可是每头牛都有自己独具的特征,所以分牛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不能只是把牛分成数量相等的两组,也不能只是把所有褐色的牛分给一个兄弟,把所有黑色的牛分给另一个兄弟,诸如此类。既然兄弟二人在如何分牛的事情上起了点争执,于是他们决定咨询一位睿智的法官。法官是怎么处理的?回答很简单。法官对一个兄弟说:“把牛群分成两批,随你怎么分。”然后对另一个说:“等你兄弟把牛分好了,由你挑选哪一批是你的,哪一批是你兄弟的。”很多人一看这个方案就会觉得它公平至极。由于第一个兄弟可以认定,两批牛若有好坏之别,第二个兄弟就会挑出较好的那一批,所以他不得不把这群牛尽量划分得公平,这样无论留给他的是哪一批,他都满意。而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他所说的“正义之为公平”——本质上就基于同样的想法。 在他看来,对一个社会而言,最为正义的基本结构是你在如下情况下会选择的基本结构:你不知道你会在那个社会的合作体系中扮演什么特定角色。也就是说,你可能到头来是个有钱的业界巨头,也可能是个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要问的是,在你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给了我们一份对正义社会的说明。它是一个极其令人信服的理念,而《正义论》的全部旨趣无非是推究出这么一个基本思想的详尽细节。 不过,在一头扎进这些细节前,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罗尔斯如何融汇了上一章讨论的各个理念。他首先从洛克那里汲取了社会契约的概念,但设法摒弃了这一学说背负的历史学负担:我们无须再想象人们曾经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也无须再想象人们真的对一个特定的政府表示了同意。在罗尔斯看来,上文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假想,是一个思想实验。也请注意,社会契约的内容发生了重要转变:罗尔斯想象的社会契约不是一份事关某种政府形式的协定,而是一份事关社会基本结构的协定。罗尔斯把自然状态替换为如下想象:要求人们在他所说的一个“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中去选择基本结构。罗尔斯说,由于你对自己将会在社会中拥有的特定角色不得而知,因此你在原初位置上的选择就只能从一块“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作出。这个无知之幕的理念引入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它迫使你秉持严格不偏不倚的标准去选择基本结构。这大体上就是普遍法则公式本来要做的事情,但无知之幕做得更好。你会选择在有性别歧视的社会生活吗?当然不会,因为你不能确定你会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会选择在奴隶制社会生活吗?当然不会,因为你也可能到头来是个奴隶。基本的思维过程就是这样,不过罗尔斯的实施方式实际上抽象得多。据他想象,你要选择的不是具体制度,而是指导具体制度设计的一般性原则。他的论证是,在无知之幕后的原初位置上,你不会选择效用主义的一般性原则,而是会选择正义之为公平的原则。 ● 20世纪重磅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思想导航 《正义论》是一部必读却不易读的著作。一方面,政治哲学如今的形式和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约翰?罗尔斯造就的,任何关心社会正义问题的人,就算不同意罗尔斯的观点,也无法不严肃对待《正义论》;另一方面,这部著作篇幅长、密度大,总共近600页,读时极易迷失在细节中。《导读罗尔斯〈正义论〉》精准清晰地呈现了这部艰深巨著的论证肌理。 ○ 结构最清晰、语言最平实、内容最精简的《正义论》导读,政治学、政治哲学专业必备工具书 “引言与背景”、“主题概览”、“文本阅读”、“反响与影响”、“参考文献与进阶阅读”五个部分带你“零基础”入门《正义论》。 ● 延续拜德雅经典导读系列策划,书籍设计全面改版,更美观、更适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