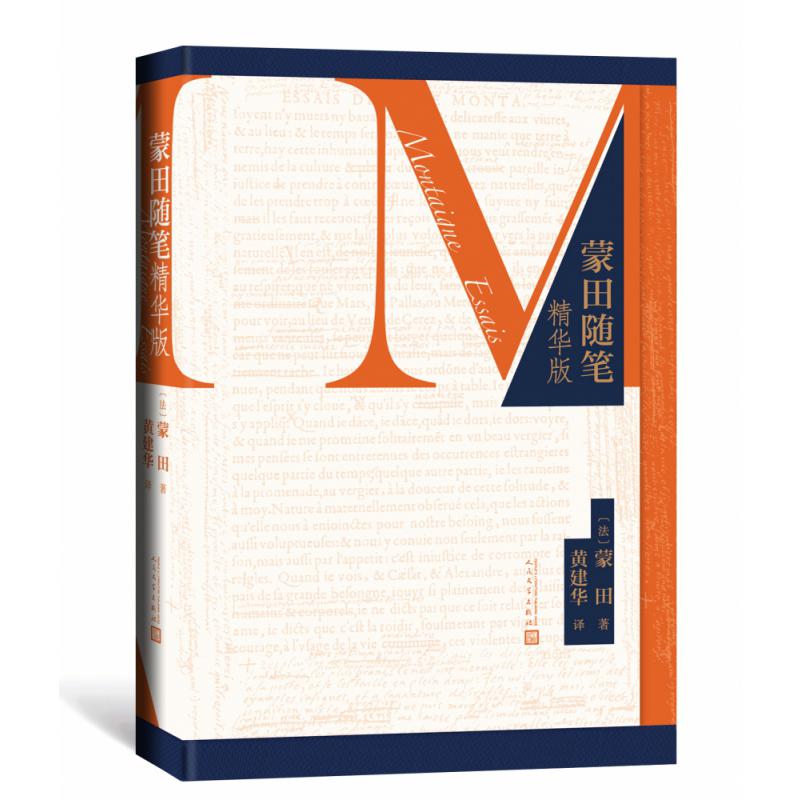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蒙田随笔(精华版)
ISBN: 9787020160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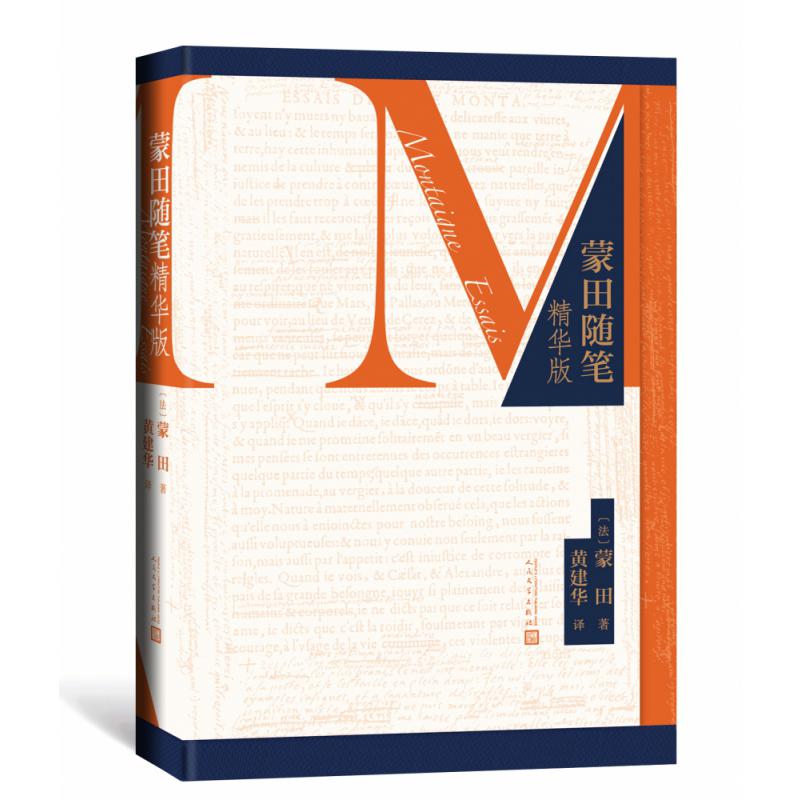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法国著名散文家、思想家,《随笔集》是他的传世之作,影响深远。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培根曾从其著作中吸取养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作家承继了他崇尚理性的体验和思想。在我国,他也引起显著的反响;他的作品不断被重译,一些篇章被收进各种文集、选集中。个别短篇早已入选为九年义务教育中学课本的教材。
第一章 不同的方式,同样的效果 我们触犯过的人,掌握了报复的手段,对我们操生杀予夺之权,这时候,软化他们心肠的方式,便是以我们的恭顺,唤起他们的同情和怜悯。然而,用相反的方法,即凭勇敢和刚毅,有时候也达到同样的效果。 威尔斯亲王爱德华1,曾长期在我们的吉耶纳2掌政,此人地位显赫,鸿运久长。他曾深受利摩日人的冒犯,便以武力攻取其城池。在屠刀下无助的民众妇孺,痛哭哀号,求饶下跪,都未能令他罢手。他继续深入城中,直至看到三名法国绅士,单枪匹马,以非凡的勇气迎击他所率的胜利之师的时候,他才停了下来。他面对如此过人的勇敢,不胜钦佩;冲天的怒火,首先受到抑制。于是,他由这三个人开始而赦免了全城居民。 伊庇鲁斯3君主斯坎德培4,曾追逐部下一名士兵,要把他杀掉。那 士兵先是低三下四,苦苦哀求,试图用一切办法令君王息怒,可无济于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横下心来,举剑去迎候君王。这一果敢的决定顿时镇住了主人的暴怒;他看到士兵下了这如此值得钦佩的决心,也就宽恕了他。那些并不了解这位君主的超凡力量与异常勇敢的人,或许会对这一事例作出别的解释。 康拉德三世皇帝1,曾包围了巴伐利亚公爵盖尔夫,对于受包围者所提出的优厚条件、委琐的曲意迎合都不屑一顾,而只允许同公爵一道被围的贵妇们徒步出城,保全其贞节,并让她们随身能带什么就把它带走。这些重情尚义的贵妇竟然想到背起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公爵本人出城。皇帝眼见她们如此高尚勇敢,竟致高兴得流下泪来;他对公爵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怨遂告消解;从此,他便仁慈地对待公爵及其臣民。 上述两种方法都极容易打动我,因为我的心地不可思议地趋向于仁爱、宽容。不过,就本人而言,我的天性更倾向于同情,而不是敬佩。然而,对于斯多葛派来说,怜悯倒不是一种美德;他们主张救助受苦难之人,而认为无须屈就他们,也不必对他们的苦痛感同身受。 …… 第二章 谈 悲 伤 …… 轻哀多言,大哀静默 的确,痛苦到了极点,其力量就会摇撼整个心灵,使其失却活动自由;正如我们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骤然得知一个坏消息,惊得落魄失魂,呆若木鸡,到后来才放声痛哭,发出哀诉,心灵似乎才得到排解,觉得较为舒缓、轻松。 痛苦终于迸发出哭声。 ——维吉尔1 斐迪南国王2在布达附近对匈牙利国王遗孀作战的年代,德国将领拉伊斯亚克看见运回了一名骑士的尸体;大家都知道这骑士在阵上的 表现出众,为他的丧生深表惋惜。那位将领像其他人一样,出于好奇心,要看看死者到底是谁;当尸首被卸下盔甲之后,他才认出,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在场的人都洒下了眼泪,唯有他,呆然地站立在众人当中,无泪,无声,眼神凝滞,一个劲地盯着儿子的尸体,到后来,悲伤过度,血脉冰凉,僵直地倒在地上。 能说出灼烧得如何的人, 他所受的就不是烈火。 ——彼特拉克1 恋人们就是这样表达无法忍受的激情的: 我啊,多么可怜! 五官全不听使唤。 莉丝碧2,我才见你, 就已经神迷意乱。 舌头麻木而不成声, 爱火将我全身燃遍。 双耳嗡鸣而失聪, 眼前黑糊糊一片。 ——卡图卢斯 因此,情感到了最激烈、最炽热的时刻,并不宜于表达我们的幽怨和感受;其时心灵受着沉重思绪的压抑,躯体则因情爱而弄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 于是,有时候就突然产生像恋人们所感受的那种不期而至的眩晕;由于激烈过甚,就在欢乐的高潮中,一阵冰冷骤然袭击全身。凡是容许品味和慢慢消受的激情都不过是一般的激情。 轻哀多言,大哀静默。 ——塞内加1 喜出望外同样也会使我们大为震惊: 她看见我走来,由特洛伊队伍簇拥着, 骤然一惊,仿佛是眼见幽灵出现; 她顿时目光凝滞,全身上下凉遍, 昏倒在地,许久许久才再张口开言。 ——维吉尔 …… 第三章 我们的意欲超越我们自身 认识自己 有人责怪世人总是追求未来事物,而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的好处,安享其成;他们认为,未来之事我们无法掌握,甚至不比过去之事更易把捉。这些人对人类最普遍的谬误,真是一语中的(如果他们敢于把我们的天性所向称为谬误的话)。我们的本性趋向于为事业的延续出力,更注重于行动而不是真知;天性引发我们产生虚妄的想法以及其他许多假象。我们从来不安于本分,总是要超越自身。担心、欲求、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令我们对目前的事物缺乏感受或重视不够,而对未来之事,甚至对身后的事物却过于热衷。 为未来而操心的人真是不幸。 ——塞内加 做自己之事,求自知之明。这一伟大格言常常被认为是出自柏拉图之手。格言的两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全部责任,而似乎每个部分又 互相包容。谁要做自己的事,就得首先认识自己的状况,了解自己宜于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把他人之事作为己事,首先就会自爱、自重,不做多余之功,不做无谓之想,也不提无用之议。 愚人达到了愿望所求,犹未知足;智者却满足于现时所有,悠然自得。 ——西塞罗1 伊壁鸠鲁2就不要智者预测未来,为未来操心。 …… 第四章 真正的对象缺乏时心灵如何将 激情转移到虚假的对象上 我们的一位绅士,得了严重的痛风症;当医生督促他完全戒吃腌肉时,他通常都风趣地回答说:他痛得厉害的时候,总想抓点什么发泄;他嚷叫着,一会儿诅咒香肠,一会儿诅咒牛舌和火腿,就感到舒服得多。 的确,正如我们举手打什么,如果打不中,落了空,我们就会觉得疼痛。同样,要想视觉舒畅,就别让视线消散在茫茫的空间,而要让它有一个目标,落在适当的距离上。 像风那样,如无浓密的森林阻拦, 其威力就会消失在茫茫的空间。 ——卢卡努斯1 同样,激动、震撼的心灵,如果抓不到什么东西,也会迷失自己。因此,应该为它提供支撑和发泄的目标。普卢塔克2谈及那些宠爱猴子和小狗的人时说道:我们的天性之爱,如果缺乏正当目标,就会另造虚浮、 浅薄的对象,而不宁愿无所寄托。我们也看到,沉湎于激情的心灵,会造出假想的、虚幻的对象以欺骗自己,甚至违背自己的信仰,也不愿意完全无所作为。 动物也是这样,它们在狂怒中会猛击那令其受伤的石器和铁器,还会因为感到疼痛而狠咬自己,以图报复: 即如潘诺尼的母熊被标枪击中, 标枪还系着细带,母熊显得更凶, 它带伤打滚,要咬枪头,狂怒不已, 追逐着那和它一道滚动的兵器。 ——卢卡努斯 当我们身遭不幸时,什么原因臆造不出来?为了有对象可发泄,无论对与不对,有什么我们不去怪罪?你不必猛扯你金发的辫子,也不必狠狠捶击你那白皙的胸脯,你那可怜的弟兄饮弹丧生与此无关,请去责怪别的方面吧。 …… 第五章 守城被围的将领是否该出来谈判 勇胜与智取 卢西乌斯·马西乌斯,古罗马的军团长,他同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作战时,想争取时间部署好部队,便放风要求谈和,国王因受麻痹而失去警惕,答应休战几天,由此给了敌人加强武装的便利和时间,自己也就走向最终的灭亡。 不过,马西乌斯的这一举动却被因循守旧的元老院的元老们指责为违背了传统。他们说,祖先打仗全凭勇敢,不靠诡计,不搞夜袭,也不佯作逃跑或出其不意反击,而只是在宣战以后,并且往往是确定了交战的时间和地点之后才开战。按照这种道德意识,他们把背叛皮洛士的医生交回给皮洛士,把背叛法利斯克人的坏老师送还给法利斯克人1。这纯属是罗马人的做法,与希腊人的机灵和布匿人2的诡诈不同,对后者来说,靠武力取胜不如用计谋光荣。 罗马人认为,欺诈只管用一时;要使敌人服输,必须让他们知道不是靠诡计和运气,而是靠公平、正规的战争中、两军对阵时的勇武。从这些谦谦君子的言语里看出,他们还没有接受下列的精彩警句: 智取或是勇胜,对敌人又有何区别? ——维吉尔 波吕比乌斯1曾说,亚加亚人憎恶在战争中使用任何形式的欺诈手段,而认为只有令敌人内心折服才算作是胜利。另一人则称说:“贤德的人士深知,唯有无损于诚信和荣誉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命运主宰者赐宝座与你还是与我? 让我们用勇气来证明吧。 ——恩尼乌斯2 被我们不屑地称为野蛮人的民族当中,有一个属于代纳特王国,他们的习俗是先宣战后开战,还要详细通报使用的手段:人员数量、军事装备、进攻和守卫的武器。这样做之后,如果敌人不退让或不妥协,他们也就有权使用最坏的狠招,而认为不会因而被指责为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和不择手段去取胜。 古代佛罗伦萨人不愿意靠突然袭击来克敌制胜,因此,在用兵布阵前一个月就不停地敲响他们所称的玛西内拉战钟,通告对方。 至于我们,倒没有这么死心眼儿,我们认为,谁取得战果,谁就享有 战功荣誉;我们继来山得1之后声言:狮子皮不够,就得用一块狐狸皮;因此出奇制胜已成为常用的兵法。我们认为,在谈判和缔约进行的时刻,将领尤应保持高度警惕。故此,当代军事家常把这么一条行为准则挂在嘴边:守城被围时,统领本人绝不应亲自出去谈判。 …… 第六章 谈判时刻危险 最近,我得知,我住处附近的米斯当镇1被我们部队攻下;那些被逐的人还有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其他人,大呼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双方正谋求和解,协议的谈判还在继续,就对他们进行突袭,击垮他们。这倒像是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2,我们的做法离这些规矩相去十万八千里。最后规约的大印未盖,别指望可以互相信任,还得十分警觉。 …… 有人说: 胜利,总是带来荣耀, 无论凭运气还是靠取巧。 ——阿里奥斯托3 但哲学家克吕西波斯4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也不大赞同。克氏认 为,那些比试谁跑得快的人,就应用尽全力去争取最快速度,而不得伸手阻拦对方,或伸腿把对手绊倒。 亚历山大更加宽怀大度;当波利佩贡建议他乘黑夜之便攻打波斯王大流士时,他回答道:“不行,取巧获胜,非吾所为。‘我宁可抱怨命运,也不愿意为自己的胜利而感到羞愧。’1” 他不屑乘奥罗德2逃遁时打他, 也不肯向他背后发暗箭袭击, 他跑到前头去与他迎面较量, 宁愿凭武力而不靠奸计克敌。 ——维吉尔 第七章 凭意图判断我们的行动 有人说,死亡令我们摆脱一切责任。我知道有些人对这话有另一番理解。 …… 我见过现时不少人,因把别人财产据为己有而良心不安,准备立下遗嘱、死后归还,求得内心宽慰。他们对这么一件急事却尽量拖延,想补救错误,愧疚感却很轻,对自己也不造成什么损失。他们所做的,丝毫不值得称道。他们应当付出自己的代价。他们偿付得愈艰难、愈辛苦,其补偿就愈恰当、愈值得肯定。悔过是要背上沉重的包袱的。 还有一些人做得更糟,他们一辈子隐藏对亲近的人的仇恨,至临终时刻才通过遗嘱表达出来;这表明他们并不顾忌自己的名誉,更不顾及自己的良知;他们激怒受冒犯的人,无益于日后的名声;他们不懂得,出于对死亡的尊重,要随死亡而消除自己的怨恨,反把它的存在延续到自己的身后。这些不公正的法官,他们已经到了不明事理之时,还要赖着来判决。 倘若我能够,我会防止自己死后去说生前未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