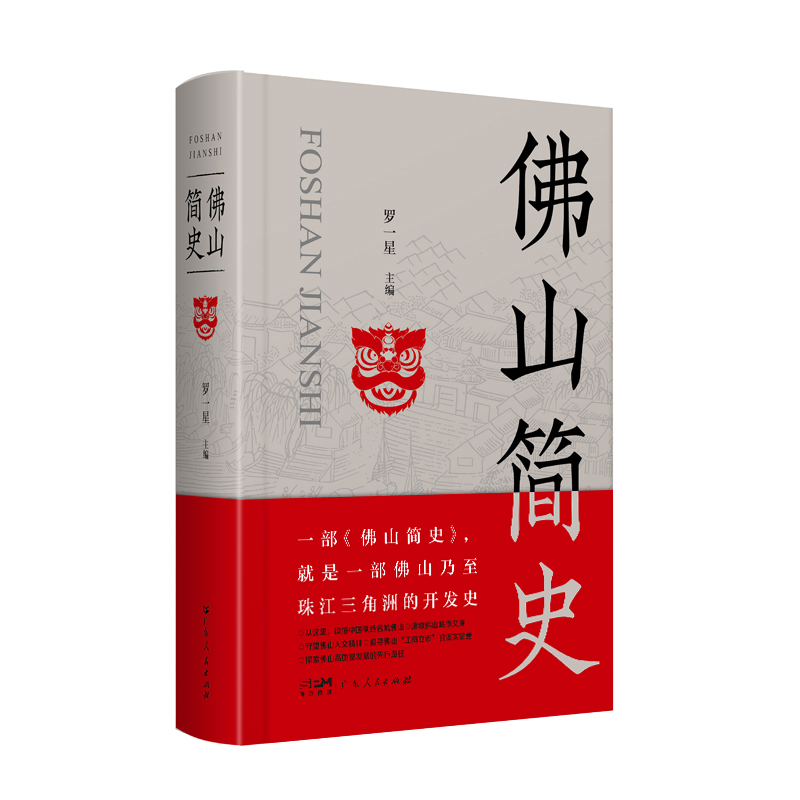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188.00
折扣价: 112.80
折扣购买: 佛山简史(精装本)
ISBN: 9787218171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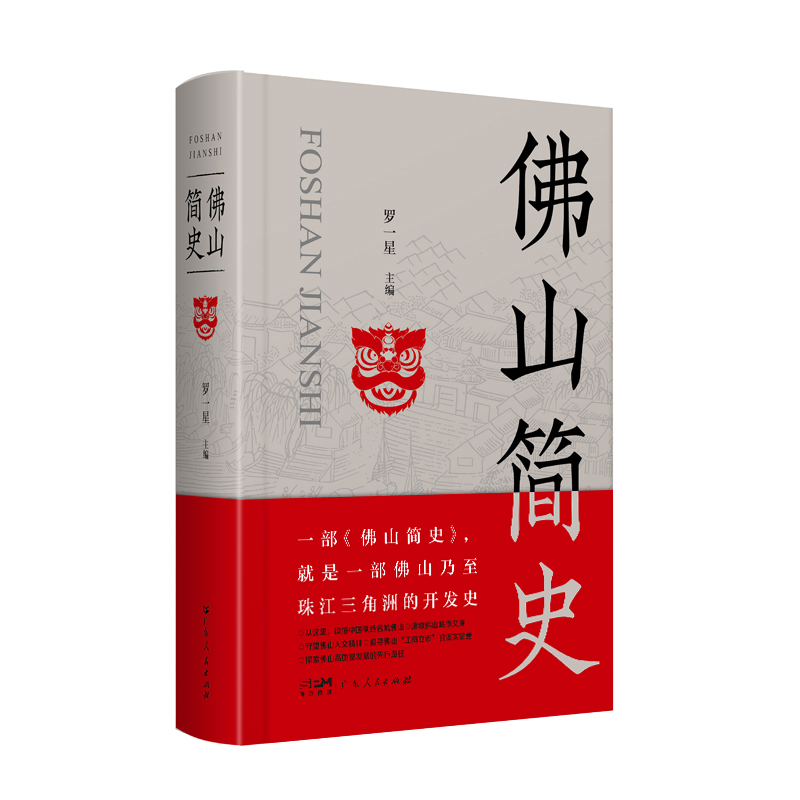
罗一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知名佛山历史专家。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任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库》主编。参与了《中国通史》和《清代全史》的编撰,参与了国家重点项目“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的研究。致力于佛山历史文化研究40年,出版研究佛山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6本,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关于佛山历史文化的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与编辑文库和丛书类历史著作多种。主要著作有《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帝国铁都:1127—1900年的佛山》《佛山北帝文化与社会》等。
一、明初佛山堡 社区基本平面分布结构是由最先形成的交通路线走向决定。在岭南地区西北东三江流域范围内,社区发展常常与最早的河流呈平行走向,以后随着人口与各项设施发展和积累,社区便沿河岸逐渐形成。而两条河流交汇之处,常常是一个社区形成的最早核心地点。这是岭南区域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特征。 明代佛山堡是个被佛山涌和新涌所包围的陆地,理论上说,四周皆可起舟泊岸。然而,更有利的水文条件是,佛山涌有许多支流伸入堡内,其中有三条最重要:一为新涌南段,新涌在茶亭处分为两支,一支向北伸入堡内, 再从栅下龙母庙出海。此为佛山旧八景“南浦客舟”所在。这支新涌南段水,在龙母庙附近又有一支伸入堡内,叫大塘涌,深入白勘头。二为西边的旗带水,从山紫村附近分支经过祖庙前,深入莺冈脚的新涌支流。“长四百六十余丈,纡回袤袅,九折而达于海。”三为北边的潘涌,系从北面的汾水伸入大墟附近的支流。这几条支流两岸,依次成为佛山社区发展的最早核心地点。 明代以前,佛山社区首先在南部栅下发展。据《岭南冼氏宗谱》记载: “明以前镇内商务萃于栅下,水通香、顺各邑,白勘为白糖商船停泊之处,俨然一都会也。”佛山“土著四大姓”鸡、田、老、布,据说就居住在栅下大塘涌一带。明初时,围绕着龙翥祠,在旗带水两岸,也形成了一个社区核心地带,这里有祭祀中心,有店铺,有九社之第一社和居民区,还有炉户在此开炉冶铁。此后,在潘涌两岸,外省与本省各地的商人开始在此建铺营生,在今公正市豆豉巷至汾水一带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嘉靖《广东通志》记载佛山堡墟市,只有“分水头”墟。又据《岭南冼氏宗谱》载:“汾水在佛山镇,去汾流古渡数十武,市肆云连,舳舻相接,亦商务中枢地也。始迁祖仕能公自本邑扶南堡卜居是地。”但当时佛山商业区划不甚明显,因河涌深入镇内,处处可起卸货物。各省商人可直接进入镇内作坊进行交易。如上述正统年间的冼灏通为锅业巨贾,各省巨商咸投其鹤园社家中贸易。又如正德、嘉靖年间的冼林佑,亦是各省客商直接到东头社其家中交易。随着镇内河涌的不断淤浅,商业点才逐渐向汾江主流北移。 在栅下、龙翥祠、汾水这三个核心地点周围,形成了它的外围区,外围区由居民住宅区、作坊区、庐墓区、田塘区所组成。明代佛山人口不多,居民区呈现为园林住宅和民居聚集区两种形态。明初一些大家巨族竞相建立园林,引流凿池,占地颇广,例如鹤园冼氏有鹤园,“家有鹤园五十亩绕池馆诸胜”。东头冼氏有东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所有几与鹤园比美”。明代佛山园林以位于锦澜铺的梁氏东溪最有名气,因为曾请到大学士丘濬到访。道光《忠义乡志》载:“东溪,在锦润辅,梁永叔筑,琼山邱文庄为作《东溪记》。”丘濬《东溪记》称“其居之东临溪水,无间寒暑,朝暮饱食,辄着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除了园林外,大多数姓氏聚族而居,在佛山堡内形成一个个以水隔离的民居聚集群落。 作坊区分布较广,佛山冶铁炉一般傍涌而建,大炉房有自己的码头。由于佛山堡内河涌较多,故炉房所在星罗棋布。20世纪70年代,佛山挖防空洞、搞基建时,发现地下数米处均有大量铸冶后废弃的泥模、铁渣等物。其分布地点沿今祖庙—莺冈—普君墟—经堂古寺一线以南至涌边的广阔地区, 成片状分布。 庐墓区多分布在明以前迁入姓氏的聚居地周围,如金鱼堂陈氏始祖墓, 就在旗带水附近宝鸭墩处。鹤园陈氏与隔塘霍氏祖先庐墓亦在两氏族居住地之间。 田塘区则大量存在于各聚居点周围。明以前,佛山田园广阔,置地极易。如纲华陈氏陈宣义,从元至正年间到明洪武初年,二十年间“置有田园共八顷零”。东头冼氏六世祖在明初时能使“家业益隆,田连阡陌,富甲一镇”。又据乾隆《佛山忠义乡志》载:“乡田皆两熟,谷美亦甲他处。但习农者寡,获时多倩(请)外乡人。”乾隆时尚且如此,明代乡田当亦更多。即使在栅下核心地点周围,亦有不少农田,据《栅下区氏族谱》记载,平政桥外有“良田二十四顷四十二亩”。此外,在堡内处处可见桑地与鱼塘。例如,在金鱼堂始祖庐墓宝鸭墩周围,就有谭氏桑地、梁氏桑地、李氏鱼塘、区氏鱼塘等。 明初佛山堡空间结构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有栅下、祖庙和汾水三个核心地点。这三个核心地点都具有商业中心的功能。而祖庙区则还具有祭祀中心的功能。它们是佛山城市的最初胚体。二是外围区由民居区、作坊区、庐墓区和田塘区组成,保持着农村的基本面貌。 这就是佛山堡在明初刚刚向都市化起步迈进的基本空间结构,是农村—城市续谱的“始祖”阶段,因此保留着较多村庄风貌。 二、1449年佛山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珠江三角洲爆发了黄萧养之乱。它对佛山社会的全面冲击及佛山乡民的积极反应,造成了深远历史影响,其结果对佛山都市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黄萧养是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人。“貌极陋,眇一目”,早先因“盗贼”罪被广东官府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在狱外同伴接应下,黄萧养率领同狱者集体越狱。逃出城外纠合同党以及无业流民、江海渔疍,“旬月至万人”。黄萧养自立为“东阳王”,并大授官衔,有所谓“安乡伯”“东平侯”“四海侯”者。他们四处劫掠村落, 刨挖各氏族祖坟获取财宝,胁迫村民入伙,“弗从辄杀”。如石头村霍氏四世祖霍厚一率其叔祖兄弟“奔七星冈入峒, 转徙佛山”,而四世祖霍厚德未出逃,被黄萧养所部“挥刀断髻”。不到几个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秩序大乱。各类边缘群体如盗寇、渔疍以及流氓纷纷加入,到处打家劫舍,残害良民。 恰恰在此时,明朝廷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出征。八月至大同闻前线战败决定回师,退至土木堡时被也先率军包围,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66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举国震惊。这给了黄萧养一个纵其所欲的天赐良机。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黄萧养分水陆两路进攻广州,白鹅潭上一时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水疍船只。然而久攻广州不下。黄萧养“又闻富户多聚于佛山,欲掠之”。八月遂分兵进攻佛山。 佛山堡民高度重视可能被劫掠的危险。早先黄萧养声言欲攻佛山时,佛山父老即赴祖庙叩问北帝神,以卜来否。“神谓贼必来,宜早为备。”当时佛山父老中有“二十二老”首倡大义,号召全堡坚决抵抗。他们是梁广(世居梨巷)、梁懋善(世居黄勘)、霍伯仓(世居隔塘)、梁厚积(世居澳口)、霍佛儿(世居祖堂边)、伦逸森(世居巷心)、梁浚浩(世居水蓼头)、冼灏通(世居鹤园)、梁存庆(世居晚市)、何焘凯(世居栅下)、冼胜禄(世居白勘)、梁敬亲(世居石狮里)、梁裔坚(世居冈头)、伦逸安(世居巷心)、谭熙(世居六村)、梁裔诚(世居冈头)、梁颛(世居冈头)、梁彝頫(世居冈头)、冼光(世居东头)、何文鉴(世居栅下)、霍宗礼(世居山紫村)、陈靖(世居旧早市),其中的梁广当时已74岁,是“二十二老”中的年长者,他秉性严厉,处事公平,乡里对其历来信服。而当时的冶铁大户冼灏通被推举为乡长,其余人个个皆是家资饶裕的“大家巨室”。他们各罄家财,甚至拆自己的大屋提供木梁,率领佛山八图子弟,树木栅,浚沟堑,储兵械,一夜之间就做好准备。正所谓同仇敌忾,备战“一夕而具”。佛山向无城墙,无险可凭。但四面环水,可竖立木栅。于是佛山乡民沿涌建栅,以栅为城,“周十许里”皆为木墙水城。h 佛山堡民创造了战时铺区防卫制度,把佛山全境划分为35铺,分区联防。“沿栅设铺,凡三十有五。每铺立长一人,统三百余众。”5铺共万余 名子弟兵。临战前所有父老子弟聚于祖庙前刑牲歃血,举行誓师大会。是以“军声大振,士气百倍”。不久,黄萧养有几百艘舟船迫至,而邻近村堡之从乱者亦“皆视佛山为奇货”,破之则大获其财。于是四面环而攻之,昼夜不停。 为了保卫佛山堡内数万生命以及明初以来佛山社会积累的财富,面对强敌,“二十二老” 誓死抵抗,他们各展其能,有的铸铳,有的筹款,有的御战,有的筹划,奇谋迭出,屡战屡胜。佛山本是冶铁重镇,自明初以来就集中了不少冶铁工场,此时这些冶铁大户和工场发挥了主要作用。如冼灏通,“用大铳,实以火药,石弹大如碗,辄击毙之。数开门挑战,战辄胜”。其次子冼靖,“率子弟为兵(军器),树栅液铁以拒以战”。所谓“为兵”和“液铁”,就是融化铁水铸造兵器。其季子冼易,拔剑击杀谕降使者李某。又如霍伯仓,率从弟霍佛儿(“二十二老”之一),从侄霍礼翘,胞弟霍伯球、霍伯厚,“同捐资缮兵甲,以武备用,夤夜撤屋为栅,浚田为涌,与贼血战,杀其伪千户彭文俊等数名,焚获甚众。贼怒,势猖獗,攻益急,公等用飞枪巨铳摧破贼锋”。再如梁浚浩,令少年趁夜色假扮成年武士,昼夜不停地鸣金击鼓巡游村中。黄贼不知虚实,以为佛山时时处处都已严防紧守,“俱不敢攻”。由此争取了宝贵的坚守时间。这个少年假扮成年武士的故事,实乃佛山秋色之滥觞。再如冼胜禄与冼光(“二十二老”之一)共事,“以筹饷为己任,于是万众一心,乡人恃以无恐。坚守六阅月,杀贼数千,公赞画之力居多”。还有梁裔坚,家资颇饶, 好任侠,乐施与,“适黄寇作难,悉以家资供乡兵食,协弟裔诚、彝顺、颛纠合乡众,并力御贼”。其弟梁颛禀性鲠直,状貌雄伟,臂力过人,“年十八,值黄寇乱,率乡忠义士悉力备御。及战,持丈二红刃刺贼先锋,大呼陷阵,众从之,贼遂溃”。 在“二十二老”的“破家财以资军食,出奇计以陷强敌,并身先乡民, 不避锋镝”的感召下,佛山全堡上下团结一心,“凡士农商贾有识力者,靡不听其驱锋冒刃而罔后我”。 祖庙在抗击黄萧养的6个月里,一直是佛山乡民的军事指挥部和精神中枢。当其时,除了佛山人的坚决行动力因素之外,北帝神的精神凝聚力因素也在起作用,这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容忽视的。在6个月的坚守中,佛山人不仅凭借其精良冶铁技术制造出足能战胜黄萧养的武器;而且凭借对真武神的信仰, 鼓起了乡民必胜信心和勇气。从心理层面上说,正是基于对外来侵略的恐惧, 加强了佛山堡民对神明的依赖。从社会层面上说,在群体面临生存威胁时,佛山“二十二老”借助神明,整合群体的大权,并运用强力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也正是在外来力量威胁下,佛山乡民接受了与神明俱在的强力权力结构,接受了当众处决内奸的结果,而没有提出任何不满和挑战;也接受了佛山全堡划分为35铺的防务布局,这为战后佛山社区的重新整合奠定了社会基础。 景泰元年(1450)二月,明王朝派都督同知董兴率江西、两广军前来镇压黄萧养。大洲决战,黄萧养大败,被杀万余人,黄萧养本人也中箭死。佛山之围“一夕散之”。官军至佛山,推冼靖为“乡义”,总协官兵讨伐黄萧养余部。冼靖甄别“良莠”,除主谋者外胁从者均不究问,周围乡村“存活者百数千人”。 佛山之战,佛山堡民歼敌“二千余名”,击杀黄萧养部将彭文俊、梁升、李观奴,生擒张嘉积等。但本身也遭到严重损失,如霍仲儒等就在战斗时中炮身亡;以“二十二老”为首的富家大室也罄尽资财。然而,正是由于佛山堡的坚守,佛山堡成为广州城的奥援,分散了黄萧养的兵力,争取了明官军的反攻时间。佛山人民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捍卫了佛山社会自明初以来积累的大量财产,保护了千家万户的妇女儿童,为明代保持在岭南地区的统治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部《佛山简史》,就是一部佛山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史 ?从这里,读懂中国制造名城佛山 ? 赓续佛山城市文脉 ? 守望佛山人文精神 ? 追寻佛山“制造业立市”的坚实足迹 ? 探索佛山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