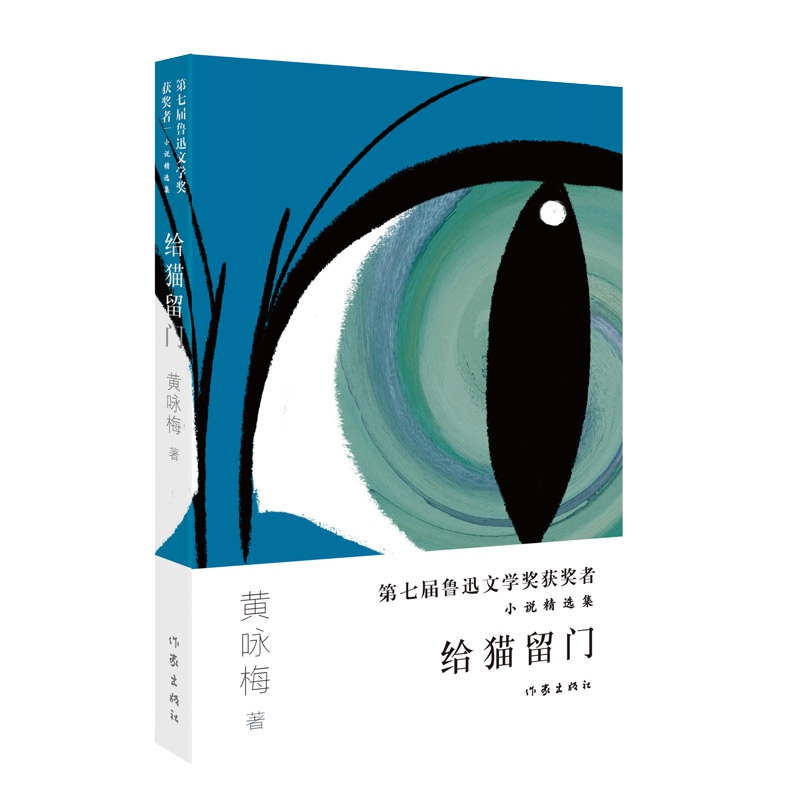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0.50
折扣购买: 给猫留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
ISBN: 9787521202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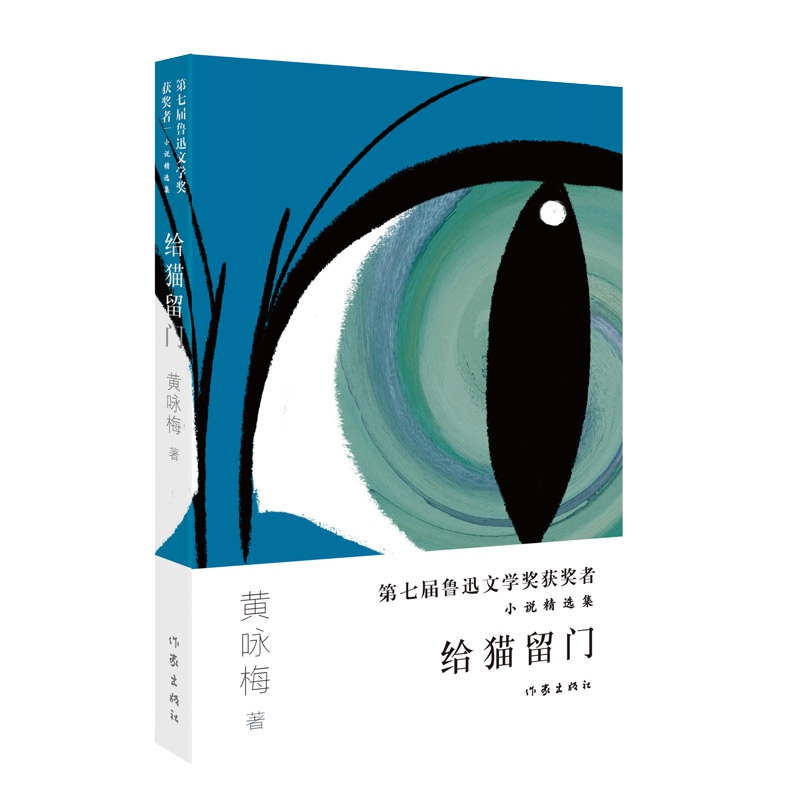
黄咏梅,女,70后作家。出生于广西梧州,现居杭州。在《人民文学》《花城》《钟山》《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小说,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出版小说《一本正经》《隐身登录》《少爷威威》《走甜》等。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父亲的后视镜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嗦,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嗦”,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还时常超速,把人撇在后视镜都看不见的拐弯处。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父亲领着它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父亲的车开得并不快,他说,开得再快,也快不过前方那团云,一眼是这样,再下一眼,就跑样了,所以,着急啥呢?父亲不着急。父亲在路上跑的时候,感觉不到时光飞速,每次回家看看日历,摸摸脑袋,哎呀,这个月又穷啦?后来,我从物理课上学到了绝对运动定理,父亲在跑,时间在跑,父亲在路上的时间等于静止。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母亲经常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道你们父亲在路上会遇到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移动电话,全靠父亲从某个途中加油站,拨个电话回家报平安,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深夜。后来我才弄明白,母亲最害怕父亲在路上遇到人。仔细想想,父亲每次出车,不仅自己穿得整洁,还把大卡车也擦洗得清爽,的确像一个出门约会的男人。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事实上,父亲四十岁那年,他跟他的卡车的确开出过轨道。这事情无须隐瞒,在我们这条红石板街,只要住过些年头的人,都不会忘记父亲那次出轨。那个下雪的深夜,他们在梦里被一阵接一阵的汽车长鸣惊醒了,叫声既像一个人在发疯,又像是拉响的警报,听说有好几个人从床上蹦下地,出门打算要往防空洞逃了,后来发现竟然是一辆卡车,停在我们红石板街中央,在我们家楼下那片空地,瞪着大大的远光灯,厉声尖叫着。雪仿佛是被它从天上叫下来的,簌簌发抖着跌落地面。人们看着这不明来路的庞然大物,竟然不敢张口开骂,只是探出头去,像看到一只受了伤、不断哀号的野兽。 卡车不知道叫了多久,忽然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同时远光灯也熄灭了,人们才看见,我父亲那辆卡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到了近前。他们先是沉默着,车头顶着车头。后来,父亲的卡车发动起来了,发出嗡嗡的叹息声。父亲一点一点地逼近,那辆卡车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后退,一直退出了我们红石板街,在大转盘掉了个头,朝城北开出去了。父亲的卡车安静地跟在后边,打着亮亮的远光灯,照亮了前边的道路。一前一后,他们开到国道上去了。 被灯光照亮过的雪,是有记忆的,结冰时就把光锁在了里边。两辆卡车留下的车痕,有时重叠,有时分开,每一段都特别深、特别亮,我母亲踩在车痕上,来来回回地走。天亮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如同他每次跑完长途回家一样,用热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把大背头梳得亮亮的,然后倒到床上,睡了一个长长的觉。 人们再也没见到过那辆尖叫的卡车,他们总是不无遗憾地说,可惜那晚灯光太刺眼了,看不清车上那个四川婆。“四川婆”漂亮的吧?我母亲也常这样问父亲,父亲从来没正面回应过,在他看来,这问题就是公路上设的一个路障,他手握方向盘,绕了过去。 “不要总是老生常谈嘛,我们是新社会的人。我跟新中国同龄。”父亲理直气壮地越过这路障。 “新社会的人,就要做这样的荒唐事?”母亲眼眶就红了。 “好啦好啦,都过去了,已经开过十八道弯了,都过去了不是吗?”父亲就这么哄着母亲。 我们都没有见过“四川婆”,她是父亲远方的情人。 母亲生前也有一个情人,他总是在远方。父亲跑长途,远的地方,一趟七八上十天的,母亲就把父亲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垫在枕头上,把手伸进袖口里,这样,她就躺在父亲的胸口上了,并跟父亲握着手。等到父亲出车回来,很奇怪的,那个远方的情人就消失了。她总是动不动就埋怨父亲,那种温柔的思念一扫而空。通常是吃过饭,把我们打发去做作业了,她就开始对着桌上的空碟、脏碗,责备起父亲来。归根结底,她是怨父亲不顾家庭,一个人跑到外边潇洒,留下她一个人在家拖儿带女。父亲也不逃避,安静地坐在母亲身边,用火柴将香烟点着后,花一点时间,用食指和拇指将火柴烧黑的地方捻掉,火柴变成了一根牙签,在父亲牙缝间进进出出。母亲那些唠叨在父亲耳畔进进出出,父亲像剔牙一样将它们剔了出来。 偶尔,父亲也不会绕开这些“路障”,会向母亲申辩。“你以为一个人在外边跑有多潇洒?我不累?你自己想想看吧。”母亲沉默一下,心里认输了,嘴巴还是要犟的:“再累也没我累,我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孩子,你一个人在外头,吃饱穿暖,全家不饿的……” “我哪里是一个人了?我后边不是拖着一条大尾巴?”我母亲光联想到父亲坐在驾驶室疾驰的风光模样,她忘记了父亲身后那一车重重的货物。母亲无语了。父亲站起身来,拍着母亲的肩膀,柔声说:“我哪里是一个人?我背后拉着一台拖拉机呢。”母亲彻底沉默了,肩膀慢慢地松懈下来。 父亲常说,他的身后拉着台拖拉机,母亲是车头,哥哥是左轮,我是右轮。 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可是,父亲却为我们的求知欲付出过沉重代价。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你们知道,后视镜里看到的东西,比老王伯伯的风筝还飞得远,又远又小。是的,隔壁老王伯伯经常从印刷厂里拿回些彩纸,扎各种各样的纸风筝,星期天带上他们家三个女儿到运河边放,我们也会跟去。运河边空旷,北风南风全都不缺,风筝遇到风就会失控,线一松就往天空蹿,很快就远成一个点了。既然父亲在路上看到的风景仅仅是那样的一个个点,父亲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她最多坐过父亲的车到十里外的郊区农场买红茶菌。母亲恐吓我们说,别老缠着爸爸和他的卡车,要是爸爸饭碗丢了,我们这台拖拉机就报废了,到那个时候,拆掉你们这两只轮子,卖钱去。我们就再不钻进父亲的驾驶室闹了。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映照着一个劳动者的路,也映照着时代的变迁。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平凡的一生,如凝练精警的诗篇,时有超拔壮阔的气象。其中贯彻的深长祝福,体现着宽厚有情的小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