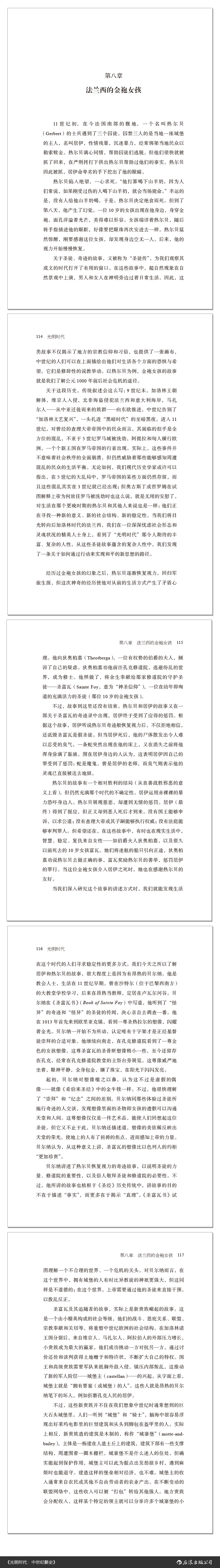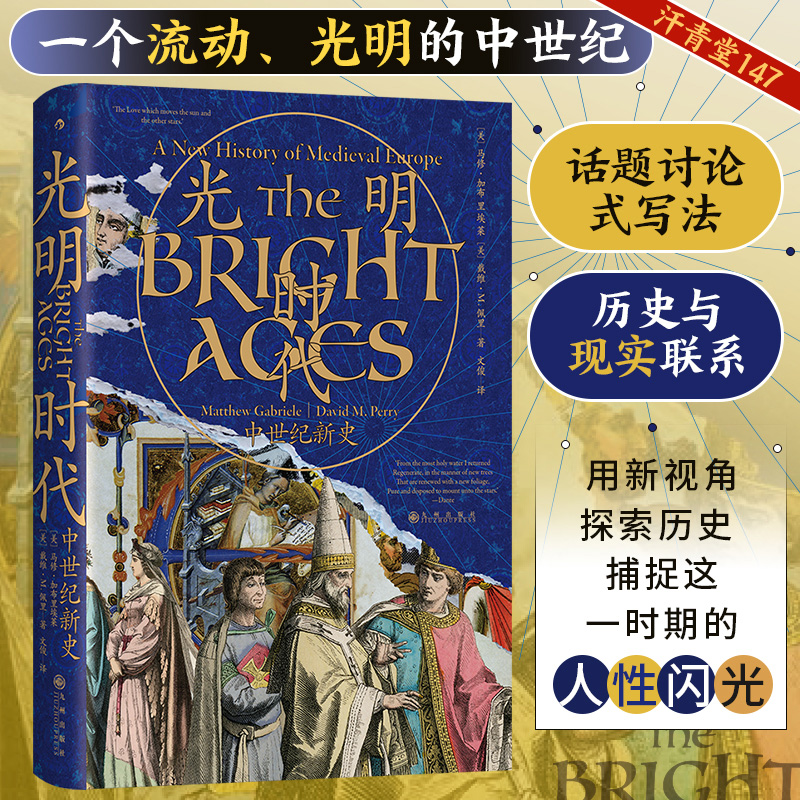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76.00
折扣价: 47.20
折扣购买: 汗青堂147·光明时代:中世纪新史
ISBN: 9787522532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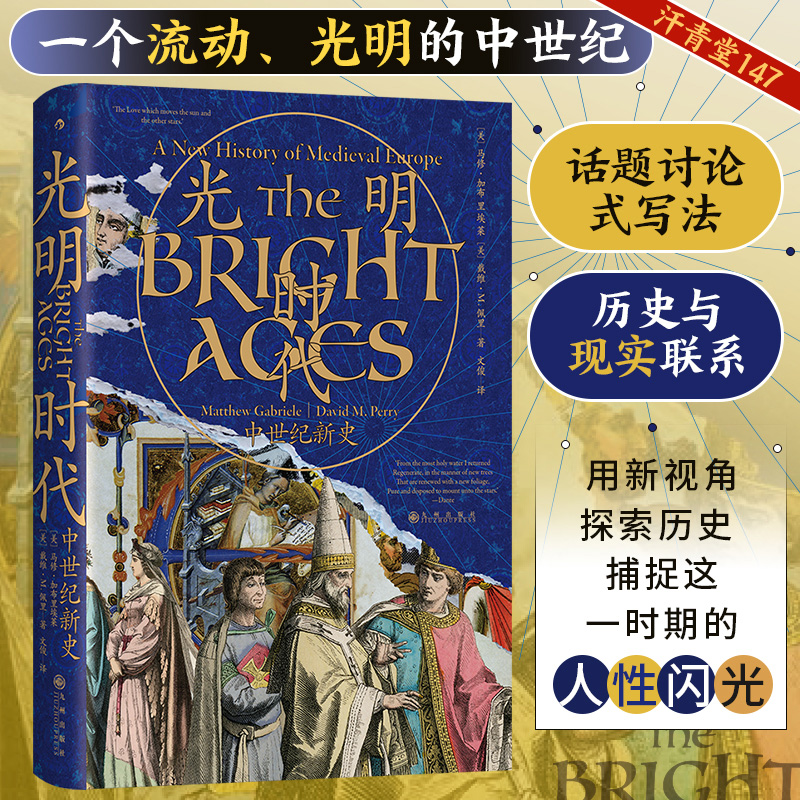
马修·加布里埃莱,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宗教文化系系主任,著有《记忆帝国: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前的查理大帝、法兰克人和耶路撒冷的传说》一书,以及有关中世纪欧洲和中世纪记忆的多篇文章。 戴维·M. 佩里,记者、中世纪史学者,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务副主任,曾在多米尼加大学任中世纪史教授,关注历史、教育、残疾人权利等话题,研究方向为威尼斯、十字军、地中海世界。
第八章 法兰西的金袍女孩 11世纪初,在今法国南部的腹地,一个名叫热尔贝(Gerbert)的士兵遇到了三个囚徒。囚禁三人的是当地一座城堡的主人,名叫居伊,性情残暴,沉迷暴力,经常绑架当地民众以勒索赎金。热尔贝满心同情,帮助囚徒们逃脱,但他们很快就被抓了回来,在严刑拷打下供出热尔贝帮助过他们的事实。热尔贝因此被抓,居伊命卑劣的手下挖出了他的眼睛。 热尔贝陷入绝望,一心求死。“他打算喝下山羊奶,因为人们常说,如果刚受过伤的人喝下山羊奶,就会当场毙命。”幸运的是,没有人给他山羊奶喝。于是,热尔贝决定绝食而死。但到了第八天,他产生了幻觉。一位10岁的女孩出现在他身边,身穿金袍,面孔洋溢着光芒,美得难以形容。女孩端详着热尔贝,随后将手指插进他的眼眶,好像要把眼珠再次安进去一样。热尔贝猛然惊醒,刚要感谢这位女孩,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后来,他的视力开始慢慢恢复。 关于圣徒、奇迹的故事,又被称为“圣徒传”,为我们观察其成文的时代打开了有用的窗口。在这些故事中,超自然现象在自然景观中上演,男人和女人在神明旁边过着日常生活。因此,这类故事不仅揭示了地方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也提供了一张画布,中世纪的人们可以在上面描绘出他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恐惧与希望。它们是修辞性的说教举动。以热尔贝为例,金袍女孩的故事就是我们了解公元1000年前后社会危机的途径。 关于这段历史,传统叙述会这么写:9世纪末,加洛林王朝解体,维京人入侵,北非海盗侵犯法兰西和意大利海岸,马扎尔人—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族群—向东欧推进,中世纪告别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一头扎进“黑暗时代”的至暗黑夜。进入11世纪,对曾经的查理大帝帝国中的民众而言,其面临的似乎是全方位的混乱,不亚于5世纪罗马城被洗劫,阿提拉和匈人横行欧洲,一个个新王国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出现。实际上,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但仍然威胁着那些能够感知周遭混乱的民众的生活平衡。无论如何,我们现代历史学家或许可以指出,在5世纪的大乱局中,罗马帝国的某些方面仍然存留,而且这些混乱其实在3世纪就已经出现;但奥古斯丁或哲罗姆在试图解释上帝为何放任罗马被洗劫时也这么说,就是无用的安慰了。对生活在那个更晚时期的热尔贝和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意义、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稳定性。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后加洛林时代的法兰西,我们在一位深深忧虑社会形态和灵魂状况的精英人士身上,看到了“光明时代”那令人期待的丰富、复杂的人性。从这些圣徒故事蕴含的复杂人性中,我们发现了一条关于如何通过行动来实现和平的新思想的路径。 经历过金袍女孩的幻象之后,热尔贝逐渐恢复视力,回归军旅生涯,但这次神奇的经历使他对从前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矛盾心理。他向狄奥柏嘉(Theotberga),一位有权势的伯爵的夫人,倾诉了自己的疑虑。狄奥柏嘉劝他前往孔克修道院,逃避纷乱的世界,成为修士。他照做了,将余生奉献给那家修道院的守护圣徒—圣富瓦(Sainte Foy,意为“神圣信仰”),一位在幼年即殉道的充满活力的圣徒(那位10岁的金袍女孩)。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热尔贝和居伊的故事又在一部关于圣富瓦的奇迹录中出现,居伊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根据这个故事,居伊听说热尔贝奇迹般恢复视力后,不仅拒绝相信,还诋毁圣富瓦是假圣徒。但当居伊死后,他的尸体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他的床上,又在消失之前将他浑身涂满了黏液。围在居伊身边的人认为,这表明居伊因自己的罪受到了惩罚:蛇是魔鬼,曾是居伊的老师,而臭气则表示他的灵魂已直接被送去地狱。 热尔贝的故事有一个相对胜利的结局(从良善战胜邪恶的意义上看),但仍然充满那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居伊运用赤裸裸的暴力恐吓身边人。热尔贝展现慈悲,却遭到无情的惩罚。居伊(最终)得到了报应,但正义却到恶人死后才到来。没有国王能够申诉,以求公道;没有查理大帝或其子嗣能够执行权威;没有法庭能够审判罪人。但希望还在,在这些故事中,有时也在现实生活中,智慧、稳定、复仇来自女性—如伯爵夫人狄奥柏嘉,以及很久以前死去的10岁女孩富瓦。她们将迷航的船只引向正途,狄奥柏嘉劝说热尔贝去做正确的事,富瓦奖励热尔贝的善举,惩罚居伊的罪行。当这位金袍女孩介入居伊之死时,她也在感谢热尔贝的友好。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时,我们就能发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寻求稳定性的更多方式。我们今天之所以了解居伊和热尔贝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昂热的贝尔纳。他是教会人士,生活在11世纪早期,曾在沙特尔(位于巴黎西南方)的大教堂学校学习,后来在昂热当教师,定居在卢瓦尔河谷。贝尔纳在《圣富瓦书》(Book of Sainte Foy)中写道,他听到了“怪异”的奇迹和“怪异”的圣徒的传闻,决心亲自去调查一番。他在1013年首先来到欧里亚克镇,看到一尊圣热拉尔的塑像,闪耀着金光。贝尔纳一开始不为所动,认定唯有十字架才是正经基督徒崇拜的合适对象。他继续向南走,在孔克修道院看到了一尊金色的女孩塑像。这尊圣富瓦的圣骨匣塑像稍小一些,至今还留存在孔克,经常在孔克修道院教堂的主祭台旁展览。这尊像威严地坐着,眼神平静,全身包金,镶了珠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起初,贝尔纳对塑像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虚假的偶像—就像《希伯来圣经》中的金牛犊一样。不过,他很快理解了“崇拜”和“纪念”之间的差别。贝尔纳同那些体验过圣徒所施行奇迹的人交谈,发现塑像里面的圣物即女孩的遗骸可以沟通天堂和人间。这尊塑像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能使人们回想起这位圣徒。但它又不止于此,贝尔纳还描述道,塑像的美依稀反映出天堂的荣光,使地上的人有了祈祷的焦点,进而感知上帝的力量。贝尔纳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讲,圣富瓦的塑像比以色列人的约柜“更加珍贵”。 贝尔纳讲述了热尔贝恢复视力的奇迹故事,以说明圣徒的力量、修道院的重要性,以及俗人敬拜圣徒和修道院的必要性。不过,他所讲的故事也植根于《圣经》历史传统中,讲故事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事实”,而更多在于揭示“真理”。《圣富瓦书》试图理解一个不合理的世界、一个危机的关头。对贝尔纳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拥有城堡的人有时比异教徒的神祇更强大,但这同样是不道德的;在这个世界,上帝需要通过他的圣徒来直接干预,以拨乱反正。 圣富瓦及其追随者的故事,实际上是新贵族崛起的故事。这是一个由小精英构成的社会等级,他们的战斗、恩庇关系、联盟、宗教奉献和关切等,将重塑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在加洛林诸王国分裂后,来自维京人、马扎尔人、阿拉伯人的外部压力增长,小贵族成为最大的赢家。他们成功挑动一方对抗另一方,通过讨价还价和谈判获得土地赠予和特许状,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国王和高级贵族需要军队来抵御外敌入侵,镇压内部叛乱,这推动了新的军人阶层—城堡主(castellan)—的兴起。从字面上看,城堡主就是“拥有要塞(或城堡)的人”。这些人就是昂热的贝尔纳笔下的坏人,例如折磨孔克人民的居伊。 不过,这些新贵族并不住在我们想象中世纪时通常想到的巨大石头城堡里。人们一听到“城堡”和“骑士”,脑海中很容易浮现出好莱坞电影里的巨型建筑和从头到脚包在盔甲里的人。实际上相反,新贵族造的建筑是木制的,称作“城寨堡”(motte-and-bailey),主体是一栋建在人造土丘上的建筑,建筑下部有一些支撑结构,周遭围着一圈木栅栏。城寨堡不是什么迷人的住处,但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城堡主可以此为据点出发劫掠乡村,遇到麻烦时也能退守。建造这样的堡垒相对经济,也不难。城堡主的收入通常来自农民或其他不自由劳动者的农业产出,在不断变动的联盟网络中,这些收入可以被“打包”转给其他强人。地方贵族会分配收入,这样某个特定的领主就可以分享许多个城寨堡的小份财富,这其实是在小范围内再现了查理大帝在一个世纪前通过分封来安抚贵族的做法。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安排与其说培养了贵族的独立性,不如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破坏性冲突。建造这种城寨堡并不需要王室或高级贵族的授权,任何有意愿、有资源的个人都可以做到。在缺乏国王和大贵族权威的法兰西,城寨堡到处出现。 这种原始城堡快速扩张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我们可以在《圣富瓦书》中看到其迹象。孔克地区周边遍布独立的城堡主,有时候,他们彼此结成松散的联盟,或依附于更高级的贵族,但通常情况下是独立的,每个人都以扩张自肥为第一要务。比方说,贝尔纳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城堡主雷农想袭击孔克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并抢走他的马。不过雷农的下场很糟糕:当他冲向这位修士时,却被自己的马摔下马背,折断了脖子。这个故事证明,圣富瓦有能力保护她的子民。此外,圣富瓦还保卫自己的土地不受贵族彭斯的侵犯。彭斯想要侵占一部分被许给修道院的土地,当他正在图谋干更多坏事时,他被一道闪电击中,当即毙命。这样的例子不仅存在于《圣富瓦书》中,在整个欧洲的其他文献记载中也比比皆是,只不过有时少了一些满身黏液的蛇和重新长出的眼球罢了。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中充斥着关于不间断的战争、对教会的洗劫、普遍混乱的嘈杂声。没有国王和皇帝能够维持和平。对这些文献的作者来说,中心和边缘地带几乎都完全不稳定,西欧大块地区分裂成许许多多块权力碎片,各碎片之间的争斗不算激烈,却总不停歇。没有人会在根本上对另一个人负责,似乎至少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力量就是正义。公正只有通过剑锋才能执行。街坊四邻的恶霸流氓耀武扬威。 但若再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作者也展示出,恶霸并非无人反抗。除了居伊、雷农和彭斯,还有保护修道院和教堂的城堡主,小贵族们也主动填补了王室法庭缺位所造成的司法空白。贝尔纳讲述了修士吉蒙的故事,这位吉蒙原本是城堡主,加入孔克修道院后仍保留着战斗装备,要是从前的同袍胆敢冒犯圣徒的权利,他就冲过去与之斗争。这种修道和战斗相混合的生活方式,在11世纪并非闻所未闻,但还不算常见。在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叙事中,绝大部分宣布告别军旅生涯的战士都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还记得 7 世纪末不列颠克罗兰的圣古斯拉克,他放弃了战斗,“皈依”—用他自己而非我们的话来讲—修道生活而非皈依基督教(因为他本来就是基督徒),因为他担心自己过去的暴行会损害灵魂的不朽。更著名的例子要数图尔的圣马丁—他是好几代人的模范,他的坟墓后来成为广受欢迎的朝圣地—他在4世纪宣布退出罗马帝国行伍,表达了成为隐修士的愿望:“我是基督的战士;于我,战斗即非法。” 到1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多(Odo),曾写过欧里亚克地区的贵族热拉尔的故事。这位贵族的生活方式尤其值得称赞。他保护受困者,避免犯罪,过着贞洁的生活,乐意听从修士、神父、主教的意见。但他仍会率领军队同破坏和平者作战,不过他只用剑脊战斗,从来不让对手流一滴血。有一次,热拉尔去见主教,要求加入某个修道院。主教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允许他像修士一样秘密剃发。据说,热拉尔此后再也没有碰剑。 ◎新视角:光明的中世纪 对“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认知,学界已经有不少反思批判,而本书则努力展现中世纪“光明”的一面。 那么,“光明时代”的光明体现在何处?作者认为,中世纪延续了罗马文明,欧洲并未堕入黑暗。中世纪也并不停滞封闭,而是不同族群和地域交流、流动的时代。欧洲人与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乃至突厥人、蒙古人之间,都有复杂的交流碰撞。而常常被忽视的女性,在中世纪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话题讨论式写法,历史故事丰富 两位作者采取了话题讨论的开放式写法,从拉韦纳的礼拜堂的星空、查理大帝收到的巴格达大象、法兰西的玛丽的骑士故事、思想家迈蒙尼德的旅程、黑死病的传播等生动的实例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时期的文化、思想、社会状况,捕捉了这一时期的人性闪光。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作者颇有洞见地指出,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中世纪叙事,实际上是为现代西方的霸权地位做辩护。这种狭隘的历史叙事应该被突破。中世纪的历史应包括阿拉伯人、突厥人、犹太人等族群的故事以及女性的传奇,应该是一段流动的、有人性之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