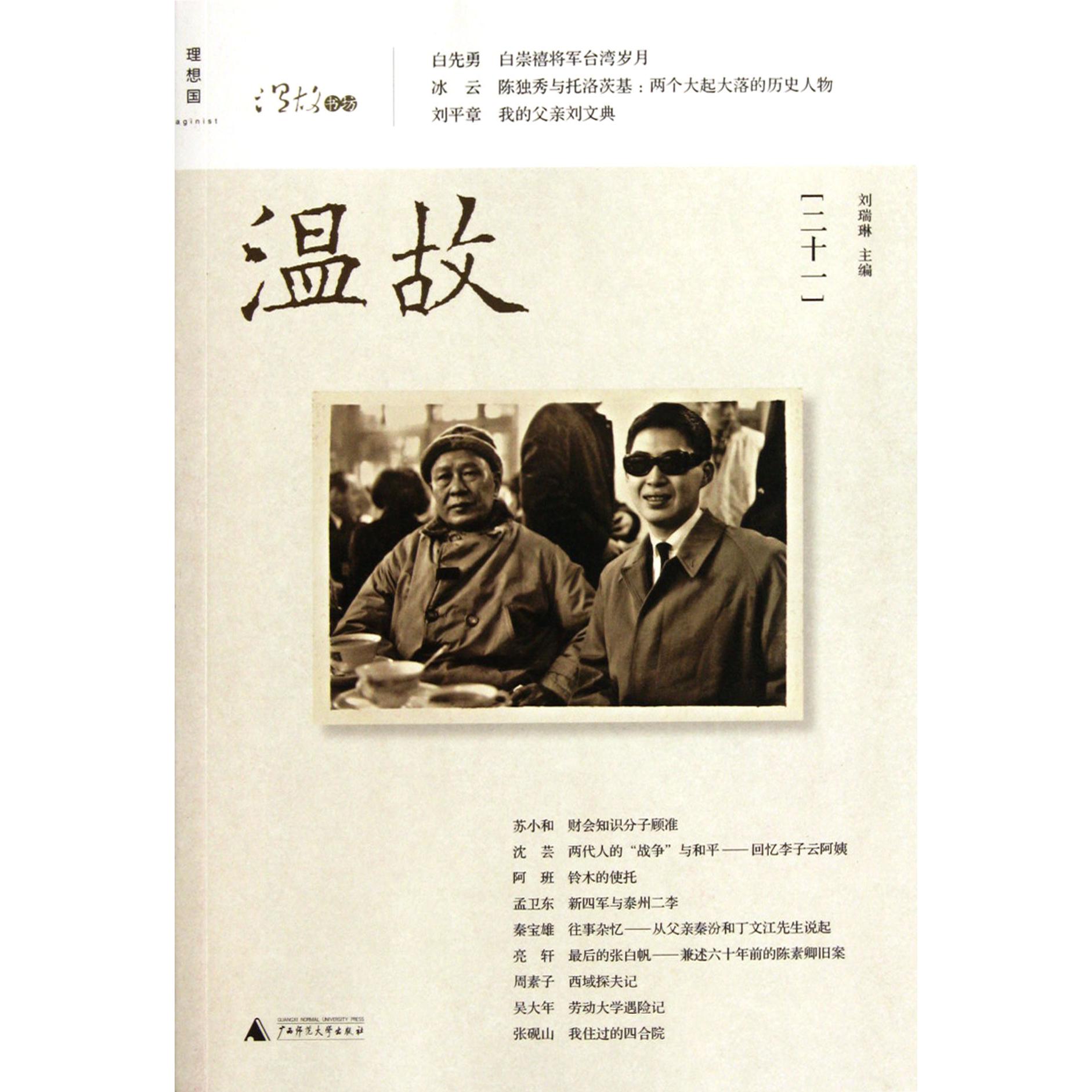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18.00
折扣购买: 温故(21)
ISBN: 9787549508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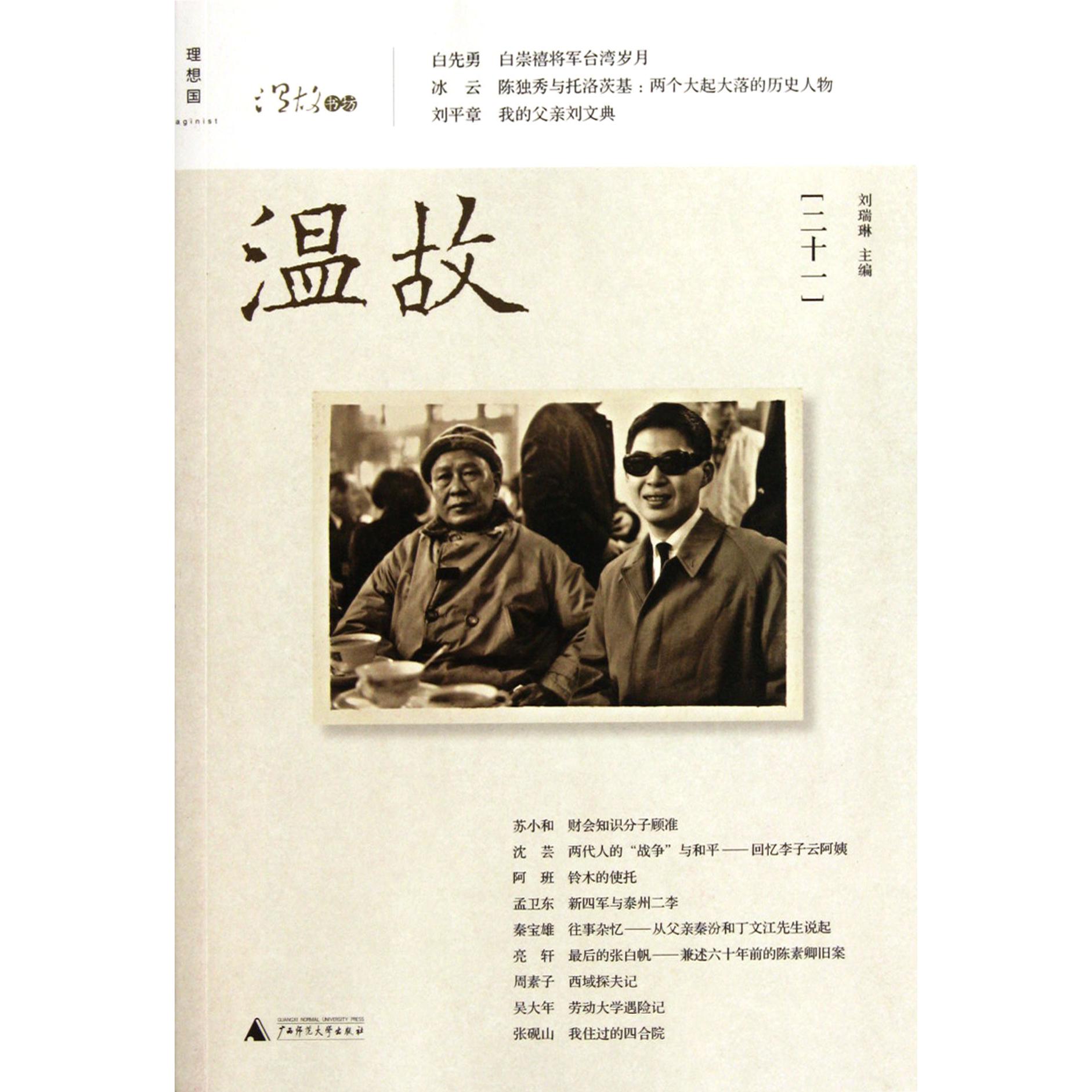
作为历史人物,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生平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现象:在他 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他们是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们的每一项重大作为都会明显地改变历史面貌,并且 不断赢得世人的阵阵喝彩;然而,,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他们却变成了无 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活得越长久,活动越多,受到的打击就越多,他们在一 般世人心目中也就越被描绘到反面。 叙述陈独秀的生平,提及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因 为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国托派组织的精神导师,而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最知名 的领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后半生命运产生 了极深刻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托洛茨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 20年代末,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陈独秀再次燃烧起了革命激情,并且 惊喜地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勇往直前。与此同时, 托洛茨基也认识到了这个在中国名声显赫的革命家站在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 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自此以后,共同的遭遇和事业让两人在感情上都对彼此 保存着真诚的尊崇和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惺惺相惜的特殊情谊——尽管他们 并没有过深的个人交往,甚至终生都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报刊和断断续续 的通信得到对方的确切消息和政治动态。 如果说在20年代末直到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关注陈独秀的政治动态和 个人状况,更多的还是看中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治经验,希望他在整顿、发展 中国托派事业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从30年代后半期起,随 着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渐行渐远,他对陈独秀的关注,则更 多的是出于一种对老朋友的私人性质的关心(自然也包含着对他在思想上能 与自己趋于一致,并且发挥政治作用的期待,但这种政治上的用心此刻已经 明显退居次要位置了)。 至于陈独秀,自1929年笃信托洛茨基主义后,就严格按照托洛茨基的指 示,殚尽心虑地奔波于中国托派的统一和发展事业。他也始终对托洛茨基保 持着尊重的态度,即使对他的某些政见无法赞同,也从未对他出言不逊。 1932年被捕入狱后,他仍与中国托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最初一段时 间仍保存着参与政治的浓厚热情,而他对托派事业及托洛茨基的关注之情也 未曾稍减。 对于经历过从“时代骄子”沦落为“国民公敌”的反差极大的人生历程 的陈独秀来说,他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遭人白眼、被人误解欺辱的个中滋 味,因此,当他看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遭遇种种刁难的新闻后,愤愤不平 ,1934年,他满带情绪地给托派国际局写了一封信: 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 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 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 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 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 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 这封信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关注和无限同情,尽管他的信对改善托洛 茨基的境遇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但对于身处逆境的托派来说,发自心坎的 支持和理解才是最为重要的。“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这句斯宾诺 莎的格言不仅为托洛茨基所欣赏,也是托派成员自勉及相互勉励的人生戒条 。 在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愤慨和对托洛茨基的无限同情之外,这封信中透露 出的另一个信息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当时苏联性质及斯大林的态度,陈独秀 逐渐与托洛茨基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强调的是斯大林等人执行的政策违背了十月革 命精神和列宁的遗教,因此,他将斯大林与托派的斗争归为两条政治路线的 斗争,并致力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路线(自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及共产国 际的恢复,致力于“救护十月革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旧承认苏联 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的感情还是站在这个国家及其施行的政治制 度一边的。 但这封信表明,随着对苏联所作所为的愤慨、绝望和深刻思考,陈独秀 已经开始质疑苏联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在苏联,斯 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 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他还提出,“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 能改良的那种幻想”。。他的新观点,不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就是与 托洛茨基仍将苏联定性为“工人国家”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相比于陈独秀 ,苏联毕竟是托洛茨基和列宁亲手缔造和捍卫的,他的感情自然要深厚、复 杂得多,因此,即便面对种种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经过二十年的 发展,“官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 量统治着民众”时,他仍坚持这个“工人国家”具有双重性质,他只承认苏 联共产党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这个国家也堕落为带有“极权主义的官僚主 义性质”,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国家还存在可以挽救的积极方面。甚 至到了1939年,托洛茨基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一文中仍以比喻的方式 说道:“打个比方:一位修理工检查汽车。开车的强盗于糟糕的路面飙车多 时,以逃过警察追捕,结果把车折腾得七零八落(车厢撞烂轮胎变形、发动 机毛病丛生)。显然,工人师傅有理由骂一声:‘这哪儿是车,分明一堆垃 圾!’类似的呵斥表达了工人师傅对司机的愤慨,但与科学分析无关。P20-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