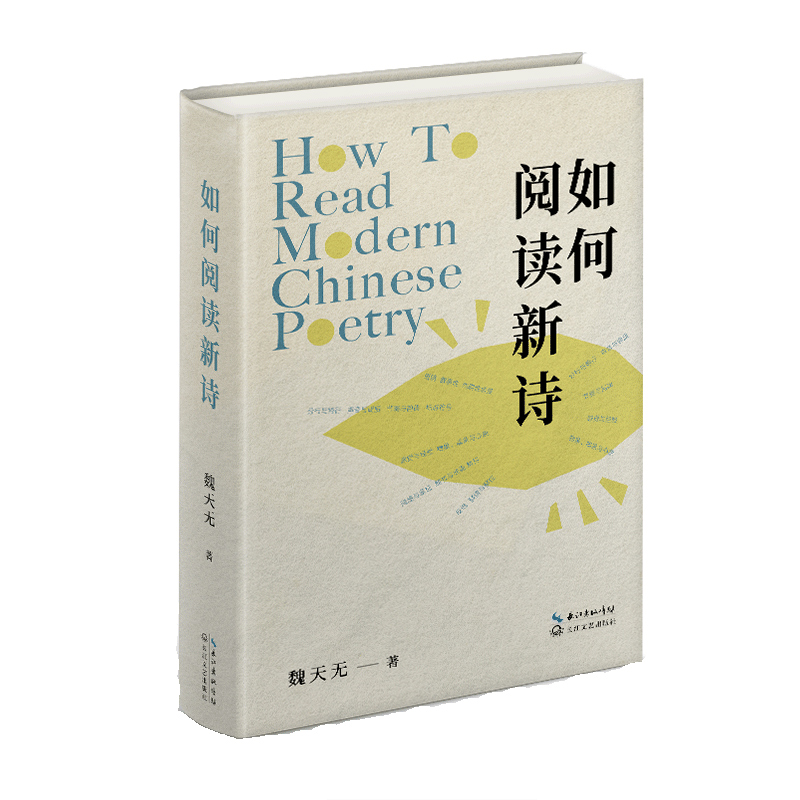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60
折扣购买: 如何阅读新诗
ISBN: 9787570232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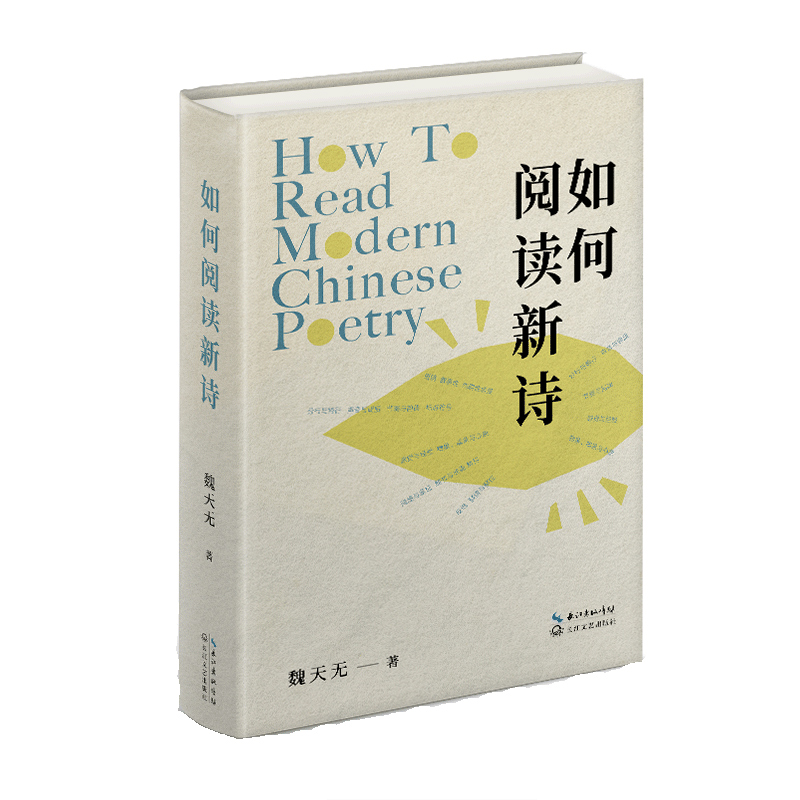
魏天无,1967年3月出生于湖北荆门,祖籍河北饶阳。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为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学术著作《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等五部(含合著),评论集《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等两部(含合著),随笔集《高过头顶的句子》。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学、现代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
结语:诗歌走向何方 结语中问这个问题,似乎问错了对象:应该去问写诗的人,不应该来问读诗的人。但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意识,让诗歌日益远离了我们,我们也就一次次失去了从诗中获得情感的满足、生活的智慧、经验的增值的机会;同时也让写作者越来越看不清诗与读者的真实关系,以致丧失了对于诗的更睿智、机敏的理解。 什么时代都不缺少号称“为未来写作”的人,尤其是所谓“先锋派”,但名与利的诱惑总是让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同时,对诗人群体和诗歌现状的不满、咒骂,在今日发达的网络上随时可见,但从不见这些人,对自己作为读者是否应当在其中承担一点责任,做出反思:错误总在对方,真理永远在我。这种缺乏反讽的态度无助于新诗的发展,除了赚取一点文章的点击量,只会固化双方对彼此的成见乃至厌倦。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新诗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假设确乎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有人肯定不同意),可以这样来回答:因为没有出现伟大的读者。 当然,像海德格尔之于荷尔德林、T.S.艾略特之于约翰·邓恩、W.H.奥登之于约翰·布罗茨基这样的伟大读者与伟大诗人的典范,实在太罕见;惺惺相惜、抱团取暖别说是在诗人与读者之间,就是在诗人之间,也似乎是个神话。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诗人与读者共处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单个诗人的写作可以完全不考虑读者,但中国新诗不可能在摒弃读者的情况下,去想象一个未来。如果没有成熟、稳定,具有一定规模的“诗歌读者”的出现,新诗若想再登高峰只能是一种可爱的幻觉。法国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诠释学家之一的保罗·利科认为,文本所要表达的比作者写作时意欲表达的重要得多,作者的意向只能成为文本意义所投射出的一种维度,“与对话的处境不同——在那里面对面由话语本身处境规定着——文字话语引起了一个读者群体,这个群体潜在地延伸到任何一个会阅读的人”。也就是说,诗人写诗并将之公开,就将面临不确定的读者群体及其七嘴八舌,这是他无从拒绝也无权阻止的;拒绝与阻止只是“表演”而已。而读者若只是盯着那些末流甚或不入流的文本,说三道四,只能说这个人的嗜好有异于常人,惊世哗众。 诗不会灭亡,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位诗歌读者。诗不会败坏在一个或一群诗人之手,而将毁灭于诗人与读者之间信任的消失。 现代诗人有一万个理由说明现代诗的复杂、艰深、晦涩,不是他存心为之,有意刁难读者。对此,作为伟大读者之一的,美国当代学者、翻译理论家、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也有了解之同情。他说,像兰波、马拉美等诗人要起到作用,“新的私人语言背后必须有天才的压力;仅仅才能,一种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是办不到的。……现代诗人利用语词作为私人记号,普通的读者要进入其中变得日益困难”。但即便艰深、晦涩如T.S.艾略特这样的伟大诗人,也倡导重视口语,注重从日常语言中获取诗的音乐性,更不用说那些把目光投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诗人,他们把日常语言作为诗的语言宝库。从读者一面来说,每个时代伟大、杰出的诗人总是极少数,平庸的诗人遍地皆是;伟大的、理想的或“超级”的读者总是屈指可数,缺少自知之明的读者摩肩接踵——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把自己从后者中超拔出去,向前者一步步靠拢。正因为我们这些读诗的人和诗人都是宇宙间孤僻、高傲、有尊严的生灵,声气相通,才需要彼此倾诉与倾听—— 我曾是宇宙深处的一团孤僻 我写诗,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孤僻 我做到了 更好地保持厌倦 我听着雨声,一滴,一滴,一滴 我害怕雨点不再飘落 潮湿不能使我成为诗人 但能使我无助——是你吗 我听见它说 “是我”(王天武《雨》) 孤僻的诗人写下/敲下的每一个字词,都像是一滴一滴的雨点,滋润着自己也飘零到他人干燥焦渴的心田。倘若真诚的诗人从诗中探身来问:“是你吗?”他应当听得见一声应允:“是我。” 本书各节所谈问题,只是笔者认为的、进入新诗需要了解的基本常识。一方面,还有更多、更具体的知识点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并不是说只要掌握、理解了这些知识,就可以无障碍地走进新诗世界。源自西方浪漫主义文论和美学的“有机整体”观念,仍然是我们阅读、解释文学文本时先验的假设,无须再去证明。从这一观念出发,任何对一首诗的条分缕析的“肢解”,都是不少诗人、也是相当多的读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这种做法只是权宜之计,但却是必需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说到如何读诗,前人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在会心中会意。陆机《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则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现代学者徐复观认为,文学欣赏乃是“追体验”的过程,“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说得上欣赏”。顾随谈及阅读体会时说: 读诗必须以心眼见……如读老杜之《对雪》:“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亦须心眼见,虽夏日读之亦觉见雪,始真懂此诗。用心眼见,亦可说用诗眼见。作者不能使人见是作者之责,写得能见而读者不能见是读者对不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