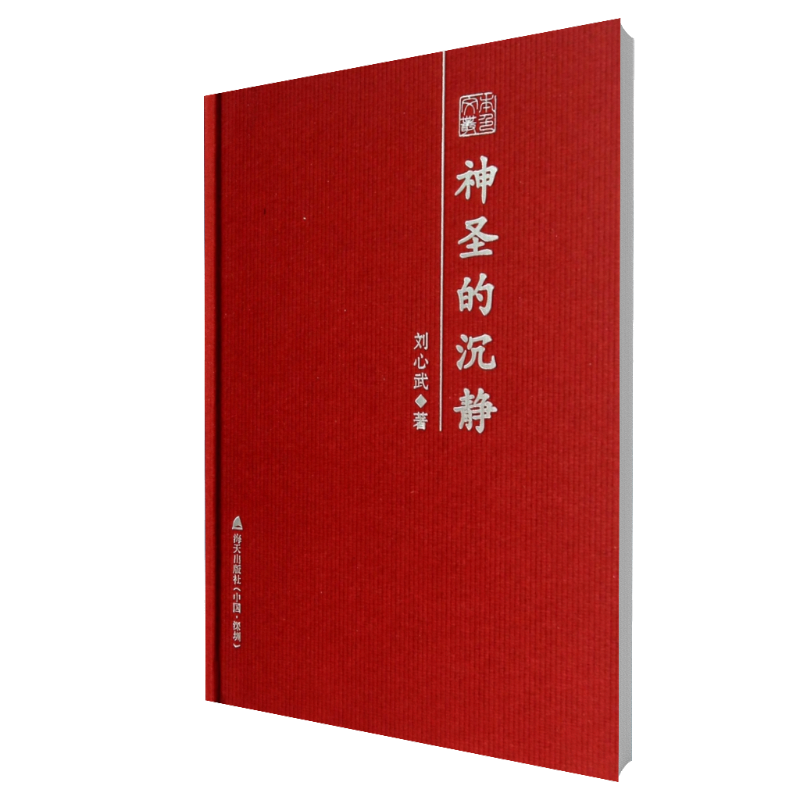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18.60
折扣购买: 神圣的沉静(精)/本色文丛
ISBN: 9787550710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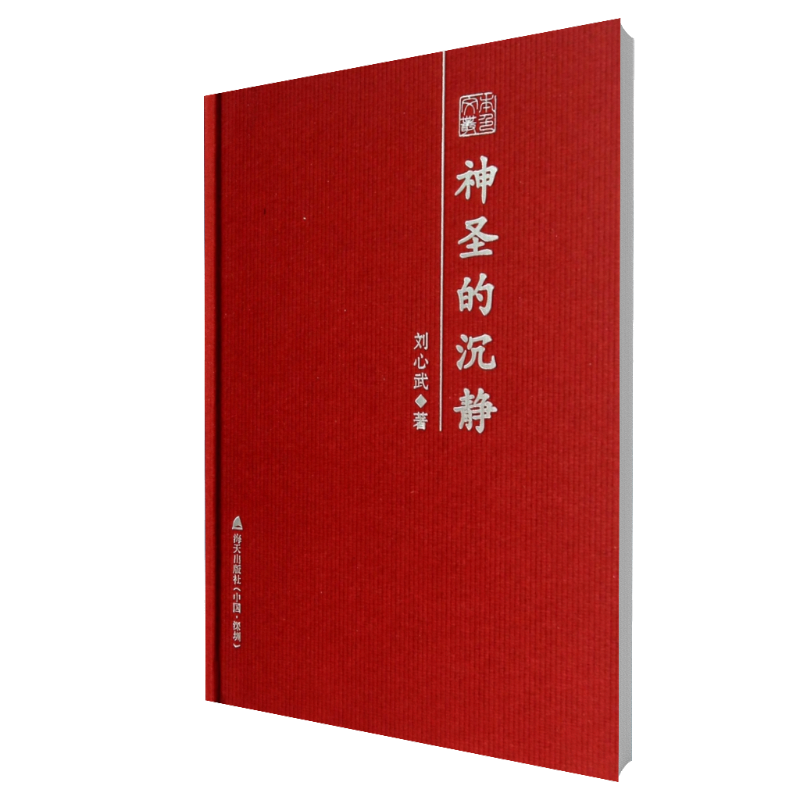
刘心武,1942年生,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代表作《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19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同名书出版后,发行数百万册。其作品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是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之一。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 锐的 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 在世 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 曾向其 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 办50周 年的报庆活动。其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 相家。 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 出版过 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 外若干 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 但要提 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就正在接待一 对普通 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而他们的预约 ,却是 在近3年前——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便来登记过的 。1988年 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 ,还给 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5年内还精确到月。至少到目 前为止, 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 后心旌 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 己都意 识不到,放飞的手远去了,母亲,你是被笼罩在母亲 的强烈 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多 么大的 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 (所谓 “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 资源, 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 了粤 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 包括外 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 此他对 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 他确是 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 许我并 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做出重要的 抉择 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 自禁地 迈出步去。 二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 也仅是 “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 书写的 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 似嫉妒 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 极也能 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 另一个 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 去者地 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 姊,他 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并未特别注 重享受 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 一个 “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 都育婴 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 轰炸重 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 我兄姊 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 抗战胜 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雾重庆在我 童年的 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 时代真 切而深刻的记忆,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 ,我的8 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他 去农村 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 ,但除 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 姐姐们 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 ,平时 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 的哺 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 正有得 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 的,如 家具,跟邻居们比,实在是毋乃太粗陋;但在吃上, 那可就 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 她能独 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 世面、 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 地轮番 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 圆、肉 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 扣肉、 米粉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 ,绝对 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10年里,天天所吃的,都 是母亲 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 川话, 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 ,晚上 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 在厨房 里外不惮其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 ,老早 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 得惯 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设想过“将来”。 生活也 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 腊肉豆 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 两样 “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 我属于 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 不给我 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 不得给 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粽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 食,她 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 个人只 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 ,似乎 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 ,吃零 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 所意会 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