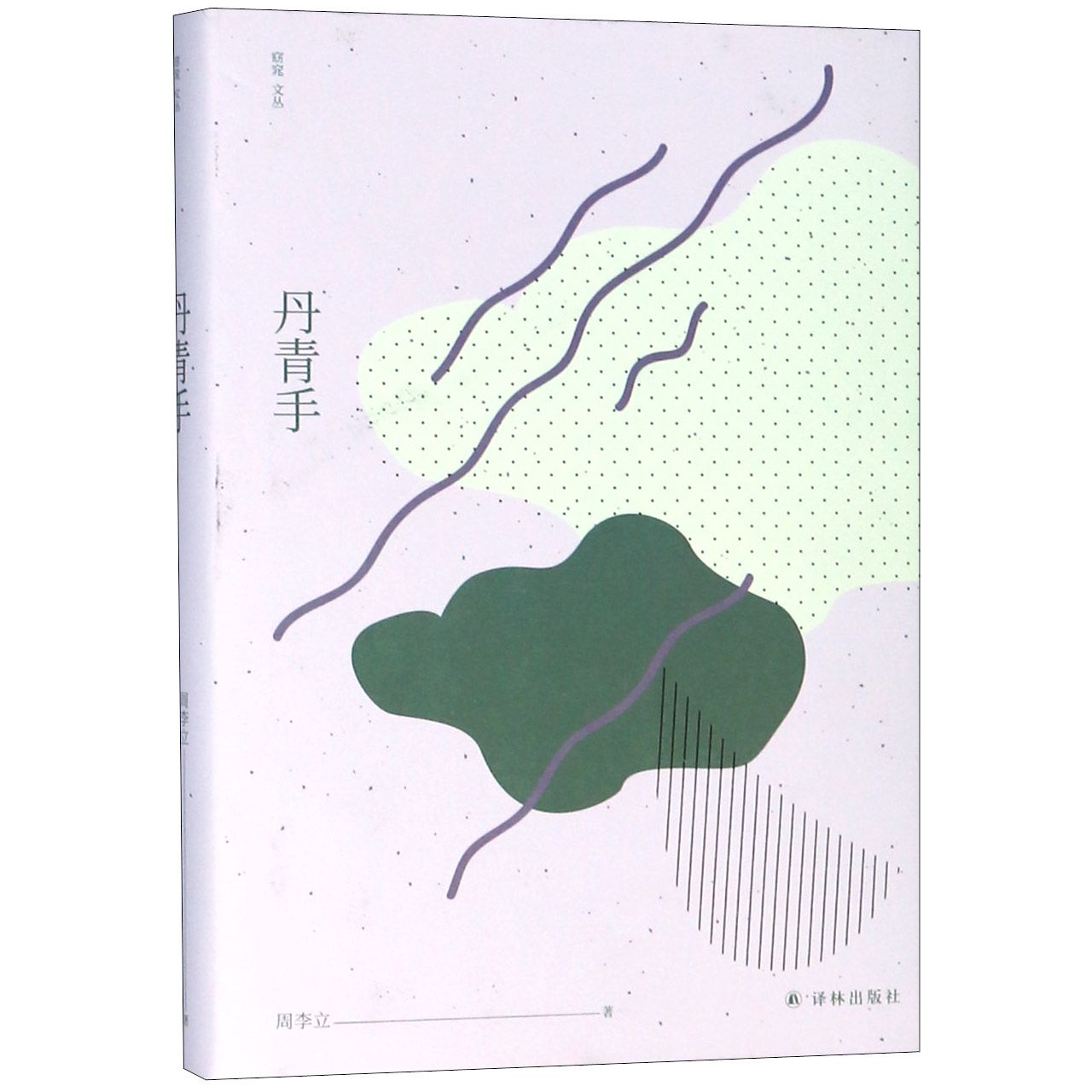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90
折扣购买: 窈窕文丛:丹青手
ISBN: 9787544773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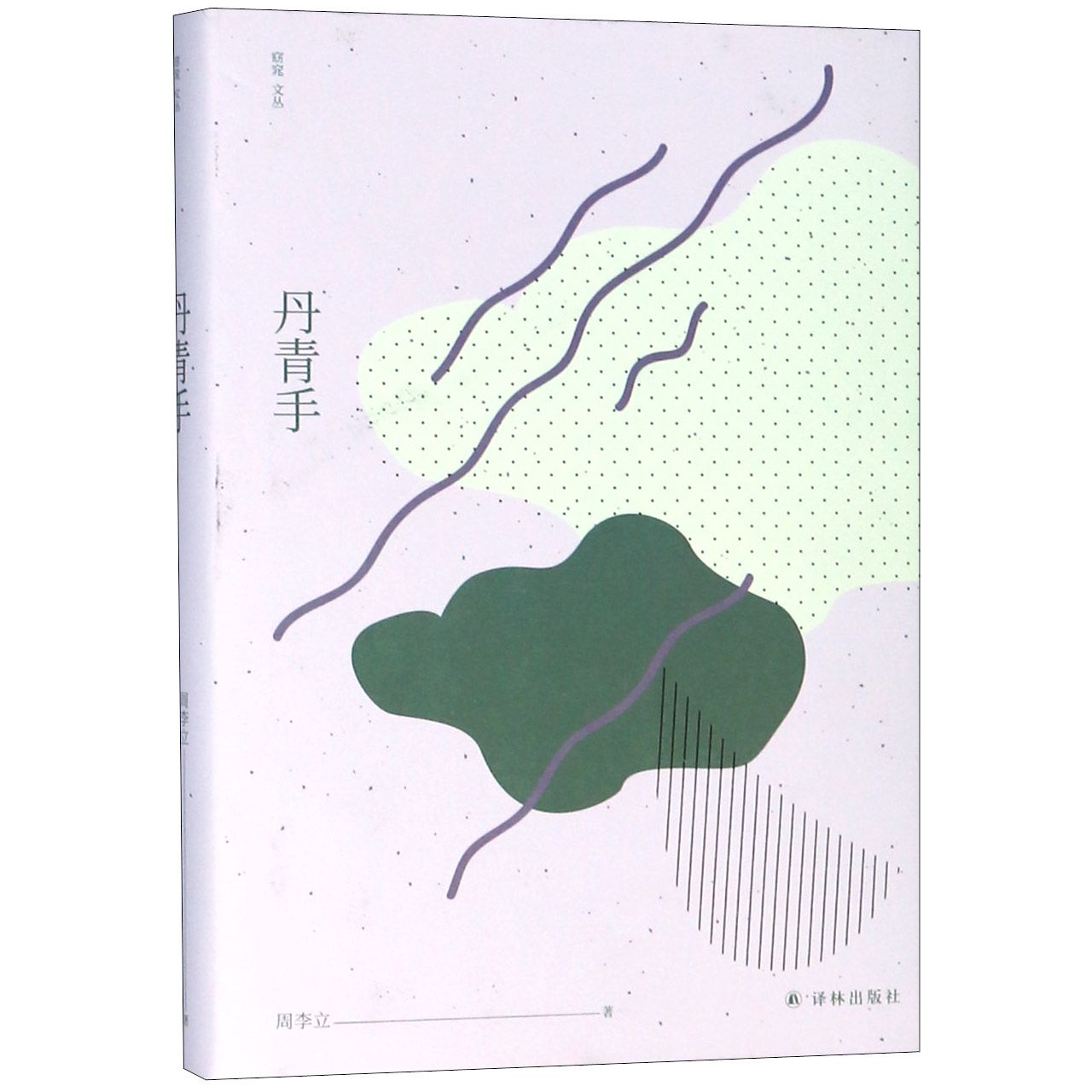
周李立,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八道门》《透视》《欢喜腾》。获17届百花文学奖、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一等奖、《朔方》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设 防 一 二〇〇三年春天认识吴勇。为什么是二〇〇三年春天?此后每到春天,乔远都这样问自己。那是特别时期,因为“非典”。口罩和**的味道成为人们熟悉的东西。北京城空空荡荡,像老妇的**。乔远**次来到艺术区,过程稍显艰难。因为那时他任教的高校已经开始实施管控政策,进出校门都如偷渡客翻越国境。校门口的棕红色电动门终*关闭,一个月没有打开过,除了小汤山医院的救护车开进来拉走需隔离的学生那次。校门传达室改为临时进出通道,装有自动检测体温的装置,很像机场安检通道,但又复杂些,因为进出校门都需要通过校办复杂的审批程序。 吴勇那一年已经是年与时空画廊的老板。乔远后来知道吴勇是山西人,面慈、手软,就像大同石窟里的佛头。画家乔远画国画,尤喜人物,曾去大同石窟造访过那些佛头。乔远看见吴勇一张可以做模特用来画佛像的脸,印象深刻。 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在艺术区*西边。应天开车带乔远来艺术区,他们把车停在艺术区外的公路边上。应天说他不担心违章停车,因为现在没人管这些了。 年与时空画廊占用的是一幢公寓楼的一楼和二楼,共两层——也许是后来打通的,中间接上楼梯。公寓楼紧邻艺术区外的公路。这条公路通往首都机场,然后,“通往世界”——应天这样解释。他总是喜欢这样夸张。他也许该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乔远时常这么想。 画廊的一层,是大厅,可以明显看出改建的痕迹。原来的墙体都拆掉了,连成一间宽阔的、像样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显眼的作品——是一些*蛋、装在金属制的镂空立方体里。六个金属立方体错落着,层叠上去,每一个都半米见方,像坏掉的一堆魔方。*蛋都是真的,乔远走近查看过。他想起*蛋的保质期,“非典”让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吴勇问,说实话,还不错,是吧? 乔远不太明确他指的是什么。但他笑着答,不错。 乔远这天是翻了学校西门的矮墙,从集中营里溜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真正不错的事。学生们那时开始都管校园叫“集中营”,两千多名青春期男女,在集中营里已经待满一个月,又停课了,终*无所事事,谁都难免想要逃逸。毕竟在*坪上晒太阳或者打羽毛球,这些事情,很快会让人厌倦。于是有人开辟了这条出校的秘密通道——矮墙本来也不高,沿着墙根又垒了些砖头,个子不高的女生也能轻松踩着砖头翻墙进出。校方似乎也知道这条通道,因为那些砖头一度被清理过,但不久又有新的砖头出现。学生们心照不宣,谁也不问是谁做了好事。墙外面的北京城,其实也不过是一座大一些的集中营,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只是乔远翻墙出校,可不是为了像大学生们一样,只为看场电影或者吃顿没味道的麻辣烫。 乔远是被应天叫出来的。乔远的大学同学应天,早住在艺术区,这天打来电话说要解救乔远,去艺术区转转。 应天说,都这样了,还不出来。 这天下午,应天说他已经把车开到西门那处矮墙外了,他已经看见了三三两两的学生翻过矮墙出来。而且那些翻墙的动作熟练、轻巧,“就像做*一样”,应天在电话里说。 后来,乔远也翻了墙。他觉得这感觉很好,像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跨站在矮墙上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很久都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应天开车带乔远来到了艺术区。艺术区在北京城的另外一边。穿越城区的三环路,在乔远看来格外空旷陌生,就像另一座新兴城市的开发区。只不过两个月之前,这还是北京城*拥堵、*繁华的一条路。 那年春天北京的天空,也蓝得离奇的虚伪,酷似丙烯颜料里乔远*不喜欢的那种蓝。乔远打开车窗,摘下口罩,因为应天并没有戴口罩,乔远也不愿让自己显出胆怯。 乔远来到艺术区的**站,就到了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画廊老板吴勇一一应天这么介绍的——说,他在策划一个活动,叫“蓝天不设防”。吴勇找来应天,是为商量这件事。应天又叫来乔远,因为应天总是会在遇上麻烦事的时候叫上乔远。应天向吴勇介绍,说乔远是画家,画写意人物的。但应天没说乔远在城西的高校当老师。乔远心照不宣,于是也没有解释。他们都觉得在艺术区,画家的身份,其实*合适。 “随便看看”,吴勇说。他穿小方格子的衬衣,在衬衣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盒KENT香烟,透过薄薄的衬衫布,香烟盒清晰可见,于是他左边的胸脯就鼓了出来。那是心脏还是肺的位置呢,乔远不确定。 乔远在艺术区见到的**个人是吴勇,这难免造成不太合适的印象。其实艺术家们从来都不会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放东西——他们根本也不会穿衬衣这种东西。 吴勇带着乔远、应天去了画廊的二楼。二楼装有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抽象表现主义的画。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室内热得待不住,只有一楼装了空调。他们只看了一眼,又下楼。吴勇说去外面抽支烟。 “都差不多了,跟亦庄那边也说好了,到时候直接去就行。”吴勇跟应天谈着活动的事。他们似乎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远听不明白,但他也没问。 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楼里,乔远已经独自打发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四月“非典”疫情公开、学校实行紧急封闭措施的时候开始。这一个月的*子过得很漫长,每天的娱乐,不过是看看新闻通报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的人数,就像股民每天守着看大盘指数。只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大盘的指数都只是在涨,没有跌。到后来,连新闻里的数字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那毕竟太抽象。有些东西变成数字之后,便显不出什么意义。乔远开始进人一段沉闷的自闭里。没人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想跟什么人联系;学校的网络时好时坏,上网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些画画的东西,毛笔、砚台、宣纸、颜料,都搁置在宿舍一个角落里,发出干燥后的粉尘气息,谁还有心思画画呢;教研的论文,一直在电脑某个文件夹里,没被打开过,自然也毫无进展。乔远每天的活动,是晚饭后在校园内闲逛,看学生们如何花样百出地打发时间,谈恋爱或者发呆,本质上是一回事。有时会碰到认识的学生,他只是远远地点头,连微笑也省略了,反正大家都戴着口罩。他*久有一个星期没有开口说话,沉默到错觉自己会因此顿悟而成为艺术大师。可是他知道,其实自己始终也没能真正平静下来,内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很狂躁,他安静不下来——反正,他一点也不想这样过*子了。所以,应天打来电话的时候,乔远几乎立刻答应了一一是的,去艺术区看看,翻墙出去。 乔远认识的画廊老板从来不多,他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商人,商人总是穿衬衣,是会在胸前的口袋放东西的另一种人。那大概很不一样。乔远一直自认是学院派。学院派艺术,依赖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的核心是论文成果、教学成绩以及叫好不叫座的赔钱展览。可是,这种逻辑乔远也没能掌握。他当了三年高校的艺术课老师,一直教的是公共选修课,当然没人在乎,所以连副教授也没能评上。这大概很能说明些什么。应天一直在劝他辞职,大概也是意识到乔远在高校的*子难免捉襟见肘,还不如辞了痛快。 乔远慢慢听明白他们的活动内容。他们打算在亦庄开发区的空旷地带,放飞三百只风筝,名为“蓝天不设防”。风筝是在潍坊定做的,潍坊有家风筝厂自愿赞助他们三百只风筝,因为这毕竟是“公益活动”。“抗击‘非典’,团结人心”,电视里都是这么说的。三百只风筝不算什么、微不足道,尤其是比起因此获得的名声来说。 乔远没有问“风筝”和“非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默默听他们说话,各种细节,邀请多少人,还有宣传,*好能多去些人,什么人都行,反正所有人现在都没事干——机关不上班了,学校停课了,商场也没生意了,连公交车都空载了,闲人多的是……说实话,没问题的,因为在户外,亦庄那边很开阔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开阔,还可以戴口罩,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我们做过申请,跟有关方面打过招呼的……三百只风筝可能不够,潍坊那边愿意再提供些……但那不是关键,关键是里面有几只定做的,很大……你猜不出来,那是什么风筝,打死你也猜不出来,这可是出彩的部分呢……是孔子、佛祖、耶稣……上新闻的时候,得说说这个……可能还有别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都是些神仙……说实话,现在不正是该神仙们出场的时候了吗……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意义是你们艺术家的事,说实话,我是商人,我不*“意义”的心……什么,那可不行,你*好再想点什么意义来……我不知道……我得打几个电话了,再叫一些人,*好有名气的,这几个电话得我来打,说实话,我有这面子…… 阳光亮得刺眼,在艺术区空旷的柏油路面上,炙烤出一些气体状的东西。乔远觉得,透过这些气体看眼前的一切,都有种变形的感觉,好像时空穿越,总之是那种非现实的映象。他的心思,并不在吴勇的活动上。他从来也不关心那些被认为是哗众取*的行为艺术,尤其在这样的时候。 两周前,乔远的一个学生被带走,去了隔离医院。跟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宿舍以及左右相邻共八个宿舍的学生。他们还不知道隔离是怎么回事,在上车的时候仍然快乐得像是去春游。有女生朝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喊宇航员叔叔。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后来,有不好的消息在校内网上流传,说起他们的隔离,医院那里早已是人满为患。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无法**分开,*多的时候六个人一间房。再后来,这些消息也没有了,因为那家隔离医院断网了。乔远开始收到一些陌生号码群发的手机短信,都是本校被隔离的学生发出的,收到短信的人又自发扩散这些信息。那些短信,让乔远一点点虚弱下去。此前,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虚弱得很,就像乔远一样。 这样的时候,吴勇想做一个抗击“非典”的活动。乔远顾不上他们,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总是想着如果明天感染了“非典”,**其实做什么也没用。 但也许,他们和乔远又不一样。乔远住在城西的高校,三条地铁在学校大门外交会,那里是“非典”的重灾区;艺术区在城东,疫情没那么严重。北京这么大,乔远与吴勇,曾经是天平两端遥遥相望的砝码,难得遇见。但现在,乔远来艺术区了,见到了画商吴勇,天平就倾斜了,乔远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失控。 吴勇并不知道这些。城西是高校区,距离这里毕竟太远了。吴勇拍了拍乔远的后背,并就势把手停在乔远的肩上。 乔远从柏油路上那团诡异的气体里,回过神来。他感*到吴勇粗短的胳膊上发烫的温度,禁不住一哆嗦。乔远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身体接触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现在,这都是**的事了。 但乔远的反应,也许不是太礼貌,反正,吴勇迅速收回了手,几乎不着痕迹。吴勇的眼睛,躲在反光的眼镜片后面,乔远暂时看不明白他的神情。乔远宁愿相信,吴勇只是为表示友好而已,搭着肩膀,就像哥们儿一样。乔远想要道歉,为自己刚刚那么惊讶的反应。但他又不知道怎么道歉,因为吴勇把这些动作都做得那么自然,没有刻意的亲密,也没有故意去掩饰难堪一一因为他是商人,乔远只能这样想。 吴勇走开了,他“有几个电话要打”。 应天抽完烟,招呼乔远进画廊。他们漫无目的转了两圈,一张一张看着墙上的画,还有画旁边那些小标签上的署名。有的署名旁边,贴着小小的红色圆形贴纸,像古代仕女额头的美人痣,代表这些画已经售出了。 “其实也不是,”应天神秘地说,“有时候还没卖的画,也贴上这个小东西,显得**。”乔远听过这样的事,艺术市场总是需要各种运作、炒作、营销和策划。这都是画商们的本事。 应天说,你也拿几张画来摆上,摆上又不花钱。 乔远答应着,心里并不喜欢应天的说法。乔远只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卖过几幅画,是他的毕业作品,那时他喜欢抽象表现主义——在当代艺术领域,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抽象表现主义。但那些画从毕业展览上撤下来的时候,乔远很难过。他为此很长时间都看不起自己,也因此认定自己无法靠画画生活了——不过卖了几幅画,竟像卖了器官般痛苦。但这些事,是不是做多了就习惯了呢?在年与时空画廊,乔远这样想着。就像女人**,次数多了就没事了,只要是为了生活一一这总是一个堂皇的借口。 乔远说起吴勇的活动,问应天那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 应天似乎很有兴致,他认为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后海已经火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非典’,三里屯不能去了,人们要到户外,户外是什么地方,就是后海,也是艺术区啊。”应天看这件事的角度,似乎跟吴勇不一样,跟乔远想象中也不一样。艺术区有些偏远,交通并不那么方便。早期,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学校搬迁、装修,在这里租了厂房,做雕塑,也画画,因为房租便宜。应天也是那时到艺术区的,他被学校开除了,他睡了三年的乔远上铺的那张*位不再属于他,他需要找一处便宜房子。 “到时你来就是了,反正没事。”应天说。 吴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进到画廊来了。他指给他们看那些红色小标签,说行情不错,“尤其是红色题材的,你们知道的,说实话,就是红色题材。”吴勇来回解释,*像是在遮掩什么东西。 吴勇又问乔远画什么题材。乔远说水墨。 “什么内容的?”吴勇认真地问,眼镜片后闪过倏忽而逝的光。 乔远觉得很难回答。人物,或者山水,这该是吴勇的理解。其实乔远*喜欢那些形式主义的实验,但那可能会引发吴勇*多的疑问。 “什么都画一点。”于是乔远含混地说。 “哦,哪天可以去你的工作室看看吧?”吴勇说。 乔远没有工作室。他都在教师宿舍里画画。乔远看了看应天,应天已经替乔远答应下来了:“没问题,哪天我们一起去看看。” 乔远有些疑惑,但应天用眼神制止了他。乔远觉得应天的眼神里有些别的东西,大概在他们谈论的事情之外,但他不确定那是什么。 吴勇说他每天都在画廊里,要乔远没事的时候就过来看看,吴勇住在这幢公寓的九层,“租一、二楼,送第九层。”他补充 道。乔远每天都没事,但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再来这里了,进出校门都得翻墙一一这事儿并不那么容易。 “说实话,多走动走动,是吧?”吴勇点燃一支烟,这次他没有到外面去。“非典”让所有人都对户外和户内间的差别敏感起来,乔远也想抽烟,他犹豫着要不要到门外去,并且已经挪到了玻璃大门处,透过大门进人大厅的阳光,像一束追光灯,让他感到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每个动作都很*瞩目。 但应天也说外面太晒,他们开始在大厅抽烟。吴勇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金属的小雕塑,一条美人鱼,上身**,下身的鱼尾甩进一圈起伏的波浪。乔远看见他们把烟头在那些金属波浪里拧灭。 “*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许久,应天开口说道。 “什么是什么?”吴勇问,他刚刚在说这里的房租为什么便宜,因为马上会被拆掉,“市**想把这里改成高新科技园区。” 但应天说的是别的事情,关于吴勇的行为艺术,“蓝天不设防,*重要的,是活动的*后,要让所有人都摘掉口罩。” “摘口罩,摘口罩……”吴勇嘀咕着,突然把手里的美人鱼重重撂在展台上,“对,就是摘口罩,这就是我想要的,”他之前坐在展台上,两条不长的腿悬在白色展台边上,像没有骨头一样甩来甩去,但现在他猛地跳下来,大概很激动,“牛逼啊,就要这个,摘口罩。口罩?说实话,这玩意儿管用吗?”他从裤兜里竟真的掏出来一只白得耀眼的口罩。而乔远还以为艺术区没有人戴口罩。 “管用吗?谁知道呢,这些人……说什么都管用,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会信的,说不管用,他们也信。”应天一边说,一边绕着那堆金属格子里的*蛋转圈、手舞足蹈着。烟灰于是落在地板上,又被他踩上去,留下一些散淡的痕迹。 乔远也在美人鱼身下的波浪里拧灭烟头,然后又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了,于是又点燃一支烟,他很长时间没有抽过这么多烟了,也许应天也是,吴勇也是。 但乔远并不像他们那样激动,他想起自己的裤兜里,也有一只刚刚摘下的口罩。口罩其实并不让人舒服,就像面具。乔远的家乡,就有一种傩戏,人们戴着花花绿绿的面具跳舞,竟然倍增勇气。乔远小时候很喜欢看这种傩戏,都在县**前的广场上。七岁时,他窜到跳傩戏的队伍里,又被父亲揪出来。那天县**的**台上坐着省里管文化工作的头头们,傩戏是专门为他们演的。傩戏队伍早已失散,所以临时又凑了一些人,反正戴着面具、穿上戏服,谁也认不出来谁。但乔远还是在那些临时演员的队伍里,看见了自己的小学老师,他太熟悉那个讲台上的背影。乔远冲进队伍,是希望找那个老师。被揪出表演队伍的男孩乔远,注意力只好落在那些古怪的面具上。是那些面具,让他们变得不一样了。你看,连老师都能四仰八叉地跳舞,就像只青蛙。 “说实话,我没戴过口罩,你看我每天把口罩装裤兜里,但是我从来没戴过。我得说话,还得抽烟,说实话,戴上这东西,我喘不上气。”吴勇举着烟头的手在空中挥来挥去,他好像也忘记要把烟灰弹进那只有美人鱼的烟灰缸里。 “嘿,北京城西,你知道吗?他们都得戴口罩,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子……”应天用手蒙住嘴,像要呕吐的样子,只留出 一双眼睛,假装惊恐地看来看去。 “哈,哥们儿,你说得太对了,”吴勇说,“说实话,蓝天不设防,是个好主意,说实话,我们得庆贺一下。”他一连讲了两个“说实话”。 乔远觉得自己已经被他们看穿,因为他每天戴口罩,跟谁都不来往,像他们嘲笑的那种胆小鬼。 阳光越发倾斜,刺人封闭的玻璃门。室内有空调低沉的轰鸣声,很让人昏昏欲睡。烟雾在这间阔大的画廊里也逐渐明显起来。太阳底下,那些烟雾飘动的情状,如同玻璃上的水迹一般明显。它们在闭幕的空间里,缓慢升腾,并终于凝结成如同抽象表现主义油画上的图案,也像乔远小时候见过的傩戏面具上的花纹。 应天拿过吴勇那只口罩,后来他又从一张展台的后面打开柜子。那是一个极隐蔽的柜子。应天从里面掏出一些东西,是丙烯颜料。他很高兴,说:“我他妈就是天才,你看,我一找,就找到了颜料。”他挤了一点水红色的颜料,在口罩上,用手指快速抹了两下,又单手举起口罩,像举着一条脏掉的白**:“看,画点什么东西,怎么样?” “说实话,你真他妈恶心。”吴勇却是笑着说的。 “乔远,你来画!”应天叫道。乔远几乎没见过应天画画,应天大学肄业,认为画画是一种“灵感偷袭躯体”的事情,而他始终没被灵感偷袭过,所以他没法画画。 乔远在那只口罩上又抹了些蓝色的丙烯颜料一一他*不喜欢的那种虚假的蓝色一一他回忆起傩戏面具,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在口罩上画画,然后让所有人摘下这些面具。 应天继续在他偶然发现的那个隐蔽的里翻找,他竟然找出些别的东西,是大半瓶透明的纯粹伏特加。 “哦,现在喝酒,你不觉得太早了吗? ”吴勇斜着眼睛看外面,但已经看得不是太清晰了,烟雾像是让阳光变重了一般。 “吴勇,你还藏了什么好东西,我们不是要庆贺一下吗?都拿出来!我们来庆贺一下。”应天并不客气,反正他贡献出了摘口罩的好点子。 “嘿,都被你小子找出来了,哪有什么好东西。”吴勇看着天花板上一个什么地方出神。 乔远在自己那只口罩上,也画了些东西。他想画一个耶稣,但吴勇没看出来,吴勇说那是星巴克的商标。“不,我们不要星巴克,我们已经有赞助了,潍坊风筝厂。”他说。 乔远戴上那只画有耶稣基督的口罩,耶稣不是他的信仰,但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这样的时候,信仰有用吗?他们还打算把耶稣的风筝,放到天上去呢,和孔子风筝一起。 两只口罩都画好了,那只被应天弄上颜料的口罩,被乔远改造成了傩戏面具的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叫它,钟馗,也许。” 乔远这样告诉他们。 应天并不介意这只口罩上是否真的是钟馗,反正他戴上了它。而乔远自已戴上了那只耶稣口罩。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大笑起来。但口罩让笑声听起来,有些诡异。 吴勇也希望加人他们,他竟然又掏出一只口罩,也许他的裤兜里还装着*多的口罩,但是他说过,他从来也不戴它们的。 他们把酒瓶传来传去,直接喝掉那半瓶伏特加。 乔远在吴勇的口罩上,画的是一个佛头。他擅长画佛头,慈眉善目、让人想流眼泪的那种。后来吴勇就一直戴着那只佛头口罩。乔远闻到口罩上丙烯颜料的味道,但他觉得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他们抽了太多的烟,又喝了伏特加,对味道可以不在意了。 喷头开始喷水之前,有过警报,但他们都没在意。那警报声不大,就像微波炉完成工作后嘀嘀嘀的提示音。 “还有微波炉?”乔远记得应天这样疑惑地说。“什么微波炉?”吴勇问。口罩让他们的说话声都含混起来。“还有微波炉,我想热个*腿吃,天啊,太他妈想吃个*腿了!”应天说着酒话。 这时水就下来了。天花板上那个小巧的黑色挂钩一样的东西,就在装有*蛋的金属装置的正上方。刚才那微波炉一样的嘀嘀声,就是那个小东西发出来的。但他们忽略了它,所以它开始喷水了。水雾并不大,像春天里雾状的雨。 “靠,什么鬼? ”应天被吓得弹开,他摸着自已的头发骂道,他的头发已经湿了,一些水珠在上面闪闪发亮。应天刚才一直倚靠着那些金属格子,现在,水雾垂直笼罩住他。 他们并未**明白眼前的状况,但天花板四角的地方也开始喷水了,像那种随着节奏喷水的音乐喷泉。 “啊,是烟雾探测器!”吴勇话音刚落,警报声又响起来一一这次的声音*大,像很多台微波炉同时完成了工作,一起发出嘀嘀声。 “怎么关掉它?”乔远也被水淋湿了。水雾越来越大,春雨继而转为微雨、中雨。乔远看见应天和吴勇,他们在水雾里走来走去,像是要找到什么东西。 “我们不该在这里抽烟的。”吴勇很无奈地说,看样子他并不知道怎么关掉这个。 “你该说的,这里有个喷泉!靠,真**,居然有个喷泉。”应天很不满。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但又忍不住笑起来。吴勇已经扯下了口罩,在警报声和喷水的声音里,他大声冲应天喊着:“我他妈怎么知道这里有个这玩意儿,烟雾探测器,没人说过这个……” 应天也扯下口罩,那只钟馗已经变形了,在应天嘴上留下一些红色的颜料,像嘴里在出血,又像一处夸张的**。应天用口罩干净的一面擦嘴,但没什么用。“丙烯颜料是擦不掉的。”乔远说。 “你们都有,哈哈!”应天突然大笑起来,乔远看见吴勇的嘴上,也留下一圈黑色的痕迹,那曾经是一个画在口罩上的佛头,现在模糊地印在了吴勇的嘴上。乔远于是也知道了,自己嘴上也有颜料。三个男人似乎反而不在意了。他们看着对方脸上嘴上那些深深浅浅的脏兮兮的颜色,看着对方头发上衣服上不断凝聚起来的水珠,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不被设防的烟雾探测器喷射出的人造雨,看着朦胧的落地玻璃门以及门外凛冽的大白天光,竟就这样松弛下来。 乔远想起大学时候,应天还没有被迫退学,他们夜晚在宿舍楼的水房里洗袜子——这是他们都不屑一顾的麻烦事,于是*后会洗成一场惊天动地的水仗。七八个男生在水房里互相用盆泼水——那些年的夏天,他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洗澡。但现在并不是夏天,只是一个古怪的五月,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束的五月,永远过不去的五月。 应天碰倒了一个装有*蛋的镂空金属格子,*蛋砸碎了一些,黄色的、透明的液体,黏在地板上。“我去,你想干吗?”吴勇说着,听上去他并没有生气。吴勇正扯着乔远的衣服,大笑着 想把自己脸上的颜料在乔远的衣服上擦干净。乔远躲着他,骂着:“你有病吧。”吴勇止住笑,说:“嘿,哥们儿,你那么紧张干吗?我又没病,我不会传染给你的,你别紧张。” 乔远突然蹲下来,想起了那些孩子,被带去隔离的孩子。他从昨天开始,就没再收到陌生的手机号群发的消息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会活着回来。学校里有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说校长已经决定把孩子们带回来,在校医院准备拆除的那幢小楼里隔离。但没人能确定这消息的真假,因为人命关天的事情,谁也承担不起。乔远希望他们回来,哪怕两周的隔离期还有整整五天,才会真的过去一一他仔细算过。 “哥们儿,你怎么了?起来嗨啊!”吴勇在水雾里东倒西歪地指着乔远。他不明白这些事,乔远想。 “它会自己停掉吗?”乔远问。但他们其实都不确定,烟雾探测器这种东西,*后是不是会自动关掉。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它从来没喷过水,抽烟也没喷过,今儿怎么回事?”吴勇说着,一边取下满是水痕的眼镜,露出真实的眼神。乔远**次看清他的眼神,一种忽明忽暗的光,像那种诡异的、总是会坏掉的*光灯启辉器。“可能这东西坏掉了,靠,我得找他们去……”吴勇又说。 “嘿,你们干吗呢?谁能这么好玩呢,多好玩啊。”应天喊着,他在跳《雨中曲》,他还有这一手。乔远也站了起来,加入应天,开始跳舞。他不太会跳这个,但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起小时候跳傩戏的老师。重要的是,他们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在会喷水的**房间里被淋得透湿,而他们竟然都没有想要暂时离开这里,到外面去。其实很多人都离开了,那些得“非典”死掉的人成为新闻里的数字,还有那些离开北京的人——他们也许会把病毒带到*多的地方。他们三人,都没离开,尽管他们**可以逃到门外,但他们还是让这些不知来路的、凉丝丝的水冲刷自己。 它突然停掉了。不再有水喷出来,嘀嘀声也没有了。 应天看着天花板上那些小小的黑色的挂钩一样的东西,好像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但乔远知道,这是一场意外的降水,就像这年春天意外发生的疫情一样,它总是会停止的,在某一个不被注意的时刻。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似乎为目睹了对方那场狼狈又失控的表演而难为情——也许这才是需要他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去对付的局面。 一切都安静了,碎掉的*蛋在地板上又被鞋踩过了,*蛋液于是到处都是,像是无法回避的证据或记忆。 “噢……”应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一下坐在湿淋淋的地板上,像是刚完成一场筋疲力尽的比赛。 “我们太需要这种放松了。”乔远也坐了下来,但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这样想。艺术区,这样的地方,也许本就比高校让人放松。他想起自己此刻,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到底是来自那场降水,还是来自这混乱的艺术区。只有在这样的行将被拆除然后建成高新科技园区的地方,才没有自动体温检测装置,进出没人找你要复杂的审批手续,也没有需要翻越的院墙,你也才会遇到这样的怪事一一坏掉的烟雾探测器。 “可不是吗,所以吴勇,你那个放风筝的活动,会管用的。”应天总是比他们反应*快些,现在,他马上可以一本正经地谈论他们的正事了。 “我想也是的,说实话,我不怕,”吴勇说,“他们让我别在这儿开画廊,说会被拆掉的,但是我不怕;他们也让我别搞这么大的活动,说眼下人多的地方都没人去了,但是我也不怕。我是下煤井挖过煤的人,我还怕什么?” “你还借过高利贷,也放过高利贷,结过婚,也离过婚,被人害过,也坑过人,打过架,也被打过。你那些光荣事迹,我都知道。”应天说。 他们真的已经不在意了——那些光荣的却终将成为笑谈的事,乔远想。人们总是会彼此原谅的,尤其在这些特别的*子里。 乔远承诺道:“我一定得去你那个放风筝的活动,就算翻墙也要去。”他很珍惜这样的时刻和经历,他知道这并不经常发生。 “翻墙?”吴勇不明白。 “是的,学校已经**了,我是翻墙出来的。”乔远说。 应天似乎意识到什么,他急忙说:“没事儿,他们学校,没大事儿。” “哪个学校?”吴勇认真起来。 乔远告诉了他。 “真的?你真的在那个学校?”吴勇似乎紧张起来,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手机上也有水。他在屏幕上来回抹,一边呢喃着:“上周有学生被隔离的那个?” “其中一个,是我的学生……希望他没事,我想。”乔远不知道这件事已经传到了艺术区,但这也不奇怪,所有的手机报都会传送高校区的病情,与隔离和疑似人数的那些数字一起。 “你不早说?你不是画家吗?”吴勇站起来,他从地上捡起纯粹伏特加的空瓶子,大概他想起了他们三人,刚才轮流对着瓶口喝酒。他又去摸衬衫上口袋里的烟,但烟也已经湿了。 “你也没问啊,我是画画……”乔远突然明白过来,吴勇在害怕什么,就像刚刚他对吴勇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臂感到不自在一样。 “算了,算了,没事,没事……”吴勇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推开玻璃门,一股沸腾过的暑气扑面而来。地上的水迹漫延到门外的台阶上。吴勇回头,对他们说:“我得去找找他们,来检查一下烟雾探测器。” “他怕你传染给他,所以我刚才没告诉他,你在高校区住。”吴勇走后,应天满不在乎地说。 “我以为,他不怕这个呢。”乔远并不觉得自已被吴勇突然的警惕伤害了,他明白,眼下人人都在自保,都在设防一只是一种本能,没必要被责怪。 “他?他怕死了。”应天说。 “他随身带了两个口罩。”乔远又想起来,吴勇可是要做一个“蓝天不设防”的活动的。 “哈哈,口罩,是,两个口罩一一他还给这里装了烟雾探测器。”应天说。 乔远问,真是他装的? “不知道,但怎么不可能呢?是吧。”应天说,“不过,我们没他那种经历,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他在煤井里被埋过一次,惜命得很……” 吴勇没再回画廊来,他去找修烟雾探测器的人了,但谁来为烟雾探测器负责呢?没人知道这个。也许那根本就没坏,只是他们自已做错了,不应该在有烟雾探测器的地方抽烟。他们都得为自已负责。 应天和乔远离开艺术区的时候,将玻璃门随手关上了。之前,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打扫一片狼藉的画廊。清理工作难度*大的部分,是那些碎掉的*蛋,黏腻的蛋液里掺进了烟灰,如同这世界上所有那些不堪忍*的肮脏面目。 “我们要做这些吗?”应天问。 “不知道。”乔远说。但如果就这么走掉,他还是感到过意不去。 “别往心里去,”在回学校的路上,应天开着车,这样说,“其实他这人,很多时候是不错的。这次活动,阻力还挺大的。” “我知道。”乔远说。他的确知道,所有人都没错,但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承*这些。这些隔离的*子,简直让人疯掉了。“你说,后天他那个‘蓝天不设防’,我还要去吗?”乔远担心自己会再次让吴勇难堪。 “哦,‘蓝天不设防’?你去不去,这,可能还真是个问题。”应天紧皱起眉头说,“你刚说你会去的。” “你刚说,什么阻力还很大?”乔远问。 “大型集会啊,现在,你知道的,特殊时期,到处都很紧张。” “应该是,但是,他说已经没问题了。”乔远说。 “是没什么问题了,他活动能力还可以。只是为做事,不为别的,所以,我们还是去吧,这也是我们的活动呢!”应天答道。 “我们?” “嗯,策划人里也有我,吴勇说的,摘口罩的主意是我想出来的。”应天骄傲地说着。 车速越来越快,三环路空旷无人,像没有尽头一般延伸。三环路是条环线,如果应天一直这样开下去,他们只会耗光汽油,也根本到不了尽头——尽头是不存在的。 不过,他们也终究没有在三环路上一圈圈地重复,而是小心地找到了那个恰到好处的出口。乔远已经能远远看见那紧闭的棕红色校门。他想起翻墙而出的那一刻,他曾以为自己终于逃离了戒备森严的校园,可以不必再回来了。可事实上,并没有。但那短暂的不设防的瞬间,也足以让乔远记住这**——二〇〇三年春天,画家乔远认识了年与时空画廊的老板吴勇。 * 八零九零后一批青年作家群体愈发*到关注,他们已成长为*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窈窕文丛”精选八位风格鲜明、颇具潜力的年轻女作家集中亮相:孙频、周李立、朱个、阿微木依萝、池上、庞羽、余静如、祁媛。 * 她们的写作多从自我经验出发,从生活细节出发,源自天性和本真的思考,呈现出新一代独特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
